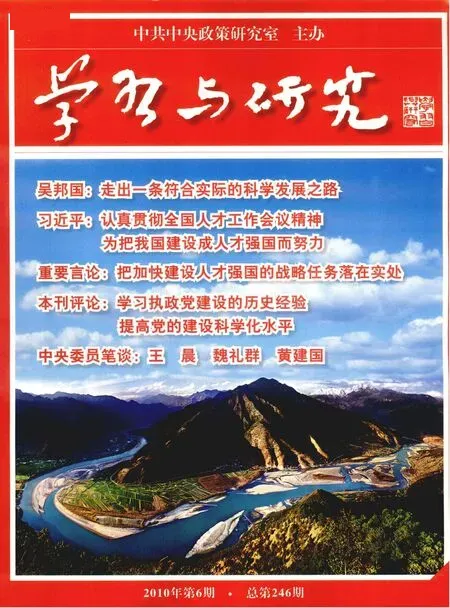方孝孺汉史典籍研究探微
2010-02-15朱志先
朱志先
方孝孺汉史典籍研究探微
朱志先
(咸宁学院人文学院,湖北咸宁437005)
方孝孺一生治学广博,对历代典籍皆有考究,尤其是对汉代典籍剖析甚多,从实学的角度质疑《史记》所载,从治世角度论析《盐铁论》、《申鉴》,从反对苛政的角度批判《政论》。在研究汉史典籍的基础上,方孝孺又从为君之道和为臣之法方面论述汉史的借鉴功能。
方孝孺;汉史;典籍;研究
方孝孺(1357-1420年),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遜志,人称正学先生,浙江宁海人,洪武进士,建文朝官至翰林院学士、侍讲学士、《太祖实录》修撰总裁。他幼受庭训,得伊洛之学,为宋濂入室弟子,对其师非常景仰,称“吾太史公远宗孔、孟,以为学高视雄,通而有余,其著书、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于四方,而信于当时,传于蛮夷之国而诵于缙绅。当世虽未有发明之者,亦无害其不朽也”①。方孝孺师从宋濂,是“婺学”之传人,其学术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程朱之学发挥到极致,但其并非是一味死守模拟儒家之经典,如其所言“取乎古而师之者,以其合乎情当乎理也”②。
方孝孺治学自幼颇有见解,人称之为“小韩子”,又追随宋濂求学多年,遍交有学问之人,当世之文真正使其“喜愜无所遗恨者不数人,岂仆识见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鲜臻其极故也”③。可见,方氏为学要求极高,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当世之作不盲从,即便对历史典籍,也持有怀疑态度,他曾言“书之名真而实伪者多矣,何从而信之哉?”④并提出其辨别史实真伪的方法,“味其辞以望其世之先后,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质诸道以索其旨之浅深,而真伪无所匿矣。”⑤依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方氏对有关两汉历史记载的书籍,如《史记》、《盐铁论》、《申鉴》、《政论》进行合理的解剖,下面依次论析方氏对两汉典籍的解析。
一、质疑《史记》之所载
太史公在自序中言“不韦迁蜀,世传《吕览》”⑥。方孝孺对此提出质疑:
吕不韦为秦相时,使其宾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为不韦徙蜀乃作《吕览》,夫不韦以见疑去国,岁余即饮鸩死,何有宾客,何暇著书哉?史又称不韦书成,悬之咸阳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辄与之。不韦已徙蜀,安得悬书于咸阳?由此而言,必为相时所著,太史公之言误也。⑦
方孝孺认为《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为相国时所作,而不是迁蜀而为,因为吕不韦“见疑去国”,不久自尽,无暇召集门人著书。另外,吕不韦已迁蜀,不可能悬书于咸阳,可见太史公之言必误。
方孝孺极力遵奉纯儒之道,以弘扬正学为目标⑧,将理学的纲常贯穿于汉史研究之中,对《史记》有周武王以暴伐纣提出质疑。他认为“司马迁之为《史记》,其志以作《春秋》自拟”,就不能“背经而信传,好立异而诬圣人,其他微者未足论。若武王与纣之事,见于书最详,而迁非乱之尤甚”,甚至“迁乃谓武王至纣死所,三射之躬,斩其首悬于太白之旗,又斩其二嬖妾悬于小白之旗,此皆战国薄夫之妄言,齐东野人之语,非武王之事,迁信而取之,谬也。……苟信迁之言,是使后世强臣凌上者,葅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祸君臣之大义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为好奇信怪者之戒。”通过上面方孝孺的分析,他认为《史记》之弊在于记载史实杂乱,背经信传而诬圣人,且以武王伐纣之事为例进行批驳,指出司马迁有过为二:其一,不能为尊者讳,详叙武王伐纣之过程;其二,好奇信怪,不能依实记载。实际上反映了方孝孺为尊者讳的思想。
另外,方孝孺对《史记》中关于周亚夫的记载,写有《條侯传论》,先指出为史者代天子立言,应该秉笔直书,行大公之道,这样才能使天子的赏罚信义于天下。接着分析西汉初年,辅相大臣多出于屠贩刀笔之流,熟于世故,善于避祸趋变,而能坚守臣节之士,汉高至文景期间,也不过仅王陵、周亚夫数人而已,周亚夫尤为突出。但在汉景帝时,周亚夫反对封皇后之兄窦信及匈奴降王为侯,汉景帝以它事为借口将其下狱致死。方氏对此事大为愤慨,论道:“封无功者以乱先帝之法,纳外国之叛臣以启为臣不忠之心,此诚宰相之所宜争也,亚夫争之岂为过哉?”而“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亚夫不从其心,固有杀亚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无以屈其说,故忍而未发。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诛之,遂卒寘之于死”。因此,据周亚夫所为“确乎有大臣之风,景帝罪之者,私恨也。”⑩方氏指出汉景帝致忠义之臣于不忍是源于私恨,但司马迁之所为更让其难以接受。方氏认为“为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马迁反诋之为守节不逊”,而以“亚夫之心,岂以穷困为戚者哉?迁不称其能守官,而诋其不逊,不闵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穷。史氏之论若此,何以信于后世?”因此,他归结为“迁善纪事,而不知统善,陈辞而不能断,有良史之才,而不达君子之道,《亚夫传》之类也。”对《史记》中所评周亚夫“守节不逊”,前人已有解析,而方氏从臣子应忠心事君,不能避义趋利的立场出发,认为司马迁之论“不达君子之道”。
方孝孺之论析充满着儒家正统伦理之味,和其尊崇儒家正学,以及明初的社会氛围是密不可分的。尽管方氏对《史记》所载史实有所发疑,但对司马迁的文笔还是倍加赞叹:“三代之隆斯文,显然惟太史公……春秋之辞,楚汉之雄,韦编竹书,金匮石室,千载遗亡,公手纪述,扫刮晦蒙,揭兹日月,上翼典谟,下昭大法……卓哉英贤,允矣良史,何人无知,巷伯是拟,公去千年,斯文湮没,纷纷鄙夫,敢继公笔”。
二、从治世角度论析《盐铁论》、《申鉴》
桓宽的《盐铁论》,后世多考究其文辞之优美,方孝孺对《盐铁论》亦倍感兴趣,曾作《读汉〈盐铁论〉》一篇,涉及以下三点内容:第一,论述了《盐铁论》产生的背景是在汉武帝四出征伐,税费横增,导致天下疲弊。汉昭帝即位后欲纠其弊,才出现这一篇问答之词;第二,从经世的角度,分析汉文帝与汉武帝执政的差别。他指出文帝时没有盐铁之征,府库充溢,而武帝继之,虽然赋税横政,却是“反愈困乏”,其因在于节俭与靡费之差异;第三,从“人君苟不节俭,虽积金齐泰华,蓄货拟江海,不至于乱未见其厌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乱矣,而文景之泽犹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缓急,从而稍稍罢其害者,故一变而弭元元之愤,不然汉岂可冀哉”,归结道《盐铁论》一书“于道德功利之际,论之当矣,不特文辞足法而已也。”方孝孺还对《申鉴》有一定的研究,他是有感于明初“学者牿于旧闻,不复知有学术,窃窃诩诩,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为,或才高而沉溺不返”。而《申鉴》是荀悦在东汉末年,面对衰世,无所可为的情况下,作《申鉴》五篇以抒己见,提出“致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方孝孺在明初读书人不讲“道术”、“学术”,即不讲经世之学的状况下,研习荀悦的《申鉴》,感到遇见知己。因此,他特著《读荀悦〈申鉴〉》一文,指出《申鉴》论述“治乱兴亡之理详矣”,因为荀悦耳闻目睹了东汉的败落之象。“故其言愈有征据,从而行之可以为治,而自汉以来,鲜有言之者,纵或言之,特以其文辞而已,著书之不足恃如是哉!”方氏经历明初政局的变革,迫切希望有治世之道,实现自己应为“有用之儒”的理想,所以他对《申鉴》的理解,并不是注目于其文辞,而在于《申鉴》中的为政之道。如他所言:“余读其书,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
方孝孺对崔寔《政论》的研究,是建构于明初统治的弊端之一在于严苛。而崔寔《政论》则主张重视赏罚、明著法术,施行“霸政”。因而,方孝孺对《政论》嗤之以鼻,认为其是“邪说”,并且引经据典,论说历来纵横之辨,为“矫当时之失,不求古今之变,而轻于持论,非知道者也”,最后对《政论》展开剖析,他认为“宣帝,汉室基乱之主,苛以为明,忍以为断,督责以为能。当斯世也,斯民兢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爱,于是高惠文景之泽竭矣,譬犹服金石恣声色之人,其外虽若未衰,而其中之虗坏已甚。至于元帝继之,稍失其术,则汉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轻信而不知道,敢为异论,而不顾其无稽,至诬文帝以严致平,何惑妄之甚哉!”甚至称《政论》“鄙哉!愚儒好高之论也……所闻者卑,而所习者陋,无怪其为此言也。……而其论至于与韩无异于乎,其所从来远矣,岂特寔之罪哉?”方孝孺在批驳《政论》中指出其弊在于,其一,汉宣帝非贤,应为基乱之主;其二,汉文帝恭俭忠厚,非以严治世;其三,汉桓帝时,没有明君之治,不应施以严刑峻法。方氏以此称崔寔不明世事,类为“愚儒”。其实崔寔
三、从反对苛政的角度批判《政论》
之论,是建构于汉末帝王比较柔弱,权归外戚、宦寺,希望帝王通过严整法纪,挽救世运于不衰,尽管其对汉文帝、汉宣帝之政,分析不是很到位,但《政论》作为一个政策的借鉴,还是有可取之处。方孝孺对东汉世事的分析比较贴切,不过其出发点是建立于明初的现实,朱元璋施行严刑酷法,肆意戮杀功臣。因此,他在辅佐建文帝时,便希望扭转时弊,施行仁政。在此前提下,方氏自然带着偏驳之见,来论析崔寔的《政论》,其心情可以理解,但史实毕竟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
方氏对《史记》、《盐铁论》、《申鉴》、《政论》的论析,不是无源之鱼,无本之木,是源于其对儒家正学的崇拜,及其贵疑的精神,如其所言“不善学之人,不能有疑,谓古皆是,曲为之辞;过乎智者,疑端百出,诋呵前古,摭其遗失,学匪疑不明,而疑恶乎凿,疑而能辨,斯为善学,勿以古皆然”。方孝孺一方面尊崇儒学,另一方面对汉史持怀疑态度,“表现出极力突出历史道德判断意义的色彩,但又多少存在一些调和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矛盾的思想和学术倾向”。
四、“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关注汉史的借鉴功能
生于明初,方孝孺亲历朱元璋之治,目阅其师宋濂和所崇拜的王祎之命运,痛感朱元璋为政,弊端较多,因此,其“志在于驾轶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然圣人之道,与时偕行”。鉴于朱元璋依汉制来治理天下,方氏在研究汉代历史时,便时时考虑到明初的现实,借以比照汉代的历史境域,希望借鉴历史“与时偕行”,从而达到“会其通而不泥于一志”。
方氏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述两汉历史:
第一,为君之道。
朱元璋在位初期,吸取元代在天下大乱之际,而宗室势力过弱,终致崩溃,因此主张模仿汉代实行分封之治,却导致几个塞王坐大。方孝孺认为这是帝王考虑问题不够长远,依此论道:
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各惩其所繇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备之外……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
方氏通过分析汉高帝借鉴秦亡之教训,大肆分封同姓宗亲,导致“七国之变”,光武帝惩汉哀、平之败乱,而不用三公,最终出现外戚、宦寺专权,皆是“各惩其所繇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备之外”,因此希望帝王不能仅以权制、法术来治理天下,应该“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方孝孺在辅佐建文帝时,便建议施行削藩和仁政,可以说灵活地把汉代历史与明初的现实结合起来。
方孝孺作为儒家正学之弘扬者,其心中所想即“治国、平天下”,达到三代之治,因此他希望为帝王者,能善纳下言。他认为汉高帝之所以能成大业,在于其善用属下之言,并以娄敬的迁都之说为例进行分析:“夫敬徙谪之虏,布衣之人,山东之贱夫耳,语其辨不若陈陆语,其智不若张、萧,无夙昔之故,左右之荐,卒然脱挽辂而入见,若涉无人之廷”。方氏认为娄敬不过一山村野夫,言辞、智虑亦没有过人之处,但汉高帝听到其迁都之言,即采纳之,因为汉高帝坚信娄敬之策能为子孙谋福。虽汉高帝“椎朴质厚,于学无所知,然其听言任人,与知道者无异”,所以“高帝之才,非能远过于人也,智非能虑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也”。方孝孺认为帝王应为天下计,不仅要有宽阔的胸怀,而且要有远见卓识,这样才能使国家鸿运长久。
第二,为臣之法。
方孝孺针对西汉初年,曹参继萧何为相,尽采其法而不变,出现汉世之大治一事,认为是为臣者善于立法、守法和不乱法,并且这三者各有差异,立法者应以仁义之道为准则,守法者应领会立法者的意图,这样才能达到不乱法。进而分析道:“何之立法,参之善守法,后世莫及也。当秦之亡,其患不在乎无法,而患乎法之过严,不患乎法废而不举,而患乎自乱其法。故萧何既损益一代之典,曹参继之,即泊然无所复为。参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为者也,特恐变更,而或至于乱,不如固守之为万全尔”。方氏认为萧何与曹参使立法、守法和不乱法这三个环节,得以完美的衔接,这样才出现曹参无为而治的局面。另外,方氏还把萧何与曹参进行换位思考,指出“何智谋虽过于参而不学,故干戈甫定而役民大治宫室,其意务媚于主,而无抚民之心。参苟居何之任,必不为此,以何代参,则何亦不能如参之明于国体,而无所变更也”,甚而认为“汉苟无何,则参之才足以立法,苟无参而他有才者继之,则汉之法乱矣。”方氏前文讲萧何吸取秦之苛政,损益一代之典,而参继之,后文又以萧何大修宫室媚主而责之,这都无可厚非。但依此认为萧何与曹参如果换位,则必致汉乱,此说过于主观论断,因在方氏头脑中充满着理想的仁义之政,再加上“今之世承大乱之后乎,然先王之道所以利民,而上无所利能为之,以渐可不扰而复也,稍揆其当损益者,而疏略之民,可不甚病也。”所以他对大兴土木的劳民之策,颇为反感,在此情况下进行换位思考,才会出现曹参非萧何可比的局面。
另外,方孝孺鉴于战国初期,纵横之士颇多,导致生民流于变诈。虽然秦代吸取其教训,但焚书坑儒及施行严苛之律令,旋经二世而亡。于是汉代实行宽大之政,终致四百年之基业。他指出明初之世,因“元之俗贪鄙暴戾,故今宜用礼义为质,而行周之制……夫示之以礼义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礼义;御史出行郡县,不以搏击人责之,而责之以礼义。化民之事,守令者考核之。”方氏认为应吸取秦汉的经验教训,为臣子的应施行宽大之政,修以礼义之法,这样才能逐渐改变元朝留下的恶俗。
方孝孺对两汉历史的论析,是建立于经世治世的目的之上,而且也和他崇高的理想人格是分不开的。方孝孺为弘扬正学,不愿仰人鼻息于权威之下,因此他对汉代的汲长孺非常崇拜,其“《憨窝记》曰:汉汲长孺、吴张子布辈,皆负气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当时,视人君之尊,不为之动,遇事辄面争其短无所忌,此皆流俗所谓憨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为重。狐鼠之盜瞷,其进退以为恭肆,彼岂用区区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惮之,以其节之足尚也。”方孝孺不仅敬仰汉代汲长孺为正义而生,不畏权威的做法,其自己也是以此效法。在明成祖让其拟诏以示天下时,方孝孺以明成祖得位不正,不愿苟息于其朝,将笔投掷于地,大骂明成祖,最终被处死。
注释:
①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九,《与苏先生二首》,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下引版本同),第12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②《礼记注疏》卷六,《考证条》,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第1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③《逊志斋集》卷十一,《与郭士渊论文》,第352页。
④朱彝尊:《经义考》卷七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下引版本同),第678册,第28页。
⑤《经义考》,第28页。
⑥《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按《史记正义》,《吕览》即《吕氏春秋》。刘知几对吕不韦迁蜀,作《吕览》一事,论道“案吕氏之修撰也,广招俊客,比迹春、陵,共集异闻,拟书《荀》、《孟》,思刊一字,购一千金,则当时宣布,为日久矣,岂以迁蜀之后,方始传乎?且必以身既流移,书方见重,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而辄引以自喻,岂其伦乎?”其因归于太史公“识有不该,思之未审”。(《史通通释》卷十六,《杂说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6年版,第461页)
⑦《经义考》,第556页。
⑧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中称方孝孺“既而时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也。”
⑨《逊志斋集》卷四,《武王诛纣》,第124页。
⑩《逊志斋集》卷五,《條侯传论》,第150页。
(责任编辑 梁一群)
B248
A
1008-4479(2010)06-0104-05
2010-09-10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一五”规划资助课题“明人汉史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153。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9q147
朱志先(1976-),男,咸宁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化史与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