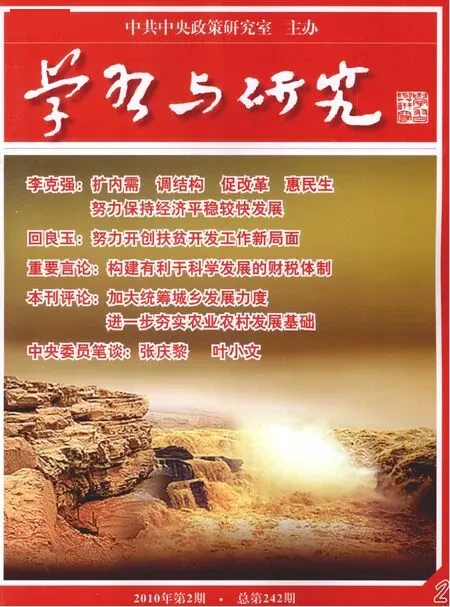生产力发展视角下的五四运动研究
2010-02-15黄亚玲
黄亚玲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生产力发展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的主线。“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须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彭明曾精辟地指出,作为历史科学的整体来看,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思想是历史的灵魂。[2]因此,当我们在分析任何一种政治现象或思想文化运动时,应当首先把握其“骨骼”,即这一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研究五四运动也应当如此。
五四运动包含着两个内容: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既是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是指1915-1920年这一时期的新文化思想运动。它既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又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本文正是从五四运动所包含两个内容进行研究,一方面从生产力发展的视角来探讨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发展的起源,另一方面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
一、生产力发展与五四爱国运动
对于五四爱国运动来说,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状是这场运动爆发的原因、背景之一。当时生产力发展极其落后,激起了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广大人民要求推翻旧军阀统治的愿望;生产力发展也促使中国的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强大起来,足以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生产力发展也使民族资本发展壮大,使民族资产阶级有相当的力量与北洋军阀政府对抗,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力量之一。与此同时,五四爱国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五四爱国运动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
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在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并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各派军阀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中,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政府,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北京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截止1919年5月,各派军阀公开或秘密举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银元8亿元以上。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船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捐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国家则通过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的政治性贷款,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3]总之,这一时期,北洋政府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加上军阀战争造成的破坏,都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也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正是五四爱国运动在经济层面的爆发根源。
2.五四爱国运动前后的工人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产生在19世纪中叶的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民族资本企业中。甲午战前中国工人阶级就已产生,大约有10万产业工人。甲午战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帝国主义在中国企业的进一步扩张,工人阶级队伍也迅速成长壮大。1913年,近代产业工人达60-70万,五四运动前更增到200万人左右。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数目,约计1,000万左右。[4]掌握着先进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成为一支新兴的产业大军。
五四运动期间,日益成为近代一支重要社会力量的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虽然工人的罢工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更加壮大,不仅表现在人数的增加上,而且表现在力量的集中上。从地区看,由于中国工业发展的殖民地性,近代工业多集中于沿海少数大城市。上海、天津、武汉、青岛、广州五个城市工人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0%,其中,上海一地就占25%。1924年,上海计有产业工人29万,相当于当时居民人口160万人的六分之一。1927年,全国有近代纺织工人23万,上海就集中了9万,占37%。从部门看,工人集中最多的是纺织、矿山、铁路、航运等业。1920年日资的本溪煤矿有48,000人,抚顺煤矿40,000人,开滦煤矿也近20,000人。在纺织业中,外资纱厂有的多到6,000-7,000人,中国纱厂也有5,000-6,000人的。在铁路部门,1927年,京汉、京浦、京绥三线各有工人20,000人,京奉、陇海、南满三线亦超过10,000人。1919年民族资本工厂335家中,工人在500人以上的有144家,1,000人以上的有29家。[5]工人阶级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为后期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五四运动前后的民族资本经济
中国的民族资本经济是在外国侵略势力与本国封建主义经济共同压迫的夹缝中艰难产生与生存的,自身比较弱小的民族资本主义,在有限的市场空间中,难以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在竞争中获胜。在政治领域中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力与政治地位,进而凭借政治力量来推进自身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的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是艰难曲折的。
五四运动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曾因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时,有过“短暂的春天”。 这一时期,民族工业无论从设厂数目、投资规模看,还是从增长速度方面看,都是其产生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从1913年到1920年,民族产业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54%。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促进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
五四运动时,各地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一战后卷土重来的威胁。五四学生运动提出了抵制日本货,劝用国货的口号,对工商业者来说是有利的。北京的商会立即表示赞助学生的行动,接着,天津、上海和全国许多城市的商会也纷纷响应。同时,不断高涨的反帝爱国革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着外国资本对华的侵略,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较好的机会,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商品,尤其以日本为最。当时日本输华的商品主要为棉纱,再加上日商在华投资设厂,从而对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形成巨大压力。但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成效显著。日纱输华数量,1918年为746000担,1919年下降为 531000担。日纱在1918年占中国棉纱进口总量的66%,在1919年只占38%。[6]
五四运动后,就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未因一战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立即就陷入萧条破产的境地,而是继续发展的。据北洋政府农商部不完全的统计,全国资本较大的厂矿公司,1914年共计146家,资本总额4,100万元。1922年,厂矿公司增加到了379家,资本总额16,000万元。公司增加了1.5倍,资本增长了近3倍,平均资本由28万元增至43万元。这说明了厂矿数和投资规模都比以前增加和扩大。据估计1933年全国工厂数已在2,000家以上,资本额达4亿元。[7]
资料表明,就工厂数目而论,棉纺织业、丝纺织行业、卷烟工业、面粉铬镍钢业等四大行业,1919年共有工厂102家,到1927年增为315家,即1919-1927年8年中,就增加213家;1927年后工厂的数量有一定下降,但棉纺织业的设备和产量仍不断增加。所以说,1919至1927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继续发展的,1927年后发展速度放慢,但较之一次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发展速度仍较快。可见,五四爱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生产力发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20世纪的旧中国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学技术的不发达。这两大问题互为因果,共同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解决这两大问题提出了新思维、新方法。一是马列主义的传播,为中国指出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是“赛先生”——科学的提出,科学救国思想的深入发展,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它们都为当时及此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1.生产力发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促进了思想解放,猛烈地冲击和荡涤着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历史的比较和实践的选择,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并不只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对于中国的发展受益最大的,是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跨越了生产关系的“卡夫丁峡谷”,实现了社会制度的突破,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缺少的条件。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内部逐渐发生分化。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其中有三场论争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场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它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一场是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它实际上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以及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还有一场是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它实际上无产阶级要不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论争。经过这三场论争,一批进步青年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人们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明确了“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中国要迅速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命运,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就必须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生产力要充分而彻底地发展,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从根本上推翻旧有的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然后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时,在随后的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从旧中国的国情出发,最能有效地推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并不是在较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应当是充分反映现代社会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近代中国要想建立充分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必须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进行变革,尤其要对由帝国主义入侵而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结构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这样,就需要把原本要在生产力比较发达基础上才可能发生的彻底的社会革命提前进行,以保证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2.生产力发展与“赛先生”的提出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社会的科技意识有了真正的提高。1915年创刊的《科学》杂志曾经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栎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8]这两句话充分概括了科学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东西方文明空前剧烈地碰撞和融合时,思想解放更加深刻与广泛,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认知与理解较之以前更全面更深刻。
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着科学的伟大精神。以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先进知识分子,以求实态度宣传新科学新思想,激励人们冲破旧的思想樊篱,寻求科学救国的道路。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为科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9]他提出要从客观事物中寻求其规律,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包括在科学之中。他还突出强调了科学的重要性,把其与民主并重。“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再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9],“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9]“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它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论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10]胡适则提出了“科学”的怀疑精神与探索方式,使“实验主义”以工具理性的方式进入救国实践。当然,科学的方法并不限于实验主义,辩证法的唯物论也有同样的重要。所以还有一部分新文化运动者,提倡辩证法的唯物论。可以说,五四新文化时期,人们对于科学的关注,既包括科学技术本身,也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赛恩斯”——科学——的重要,不是只限于机器的一方面;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比其他一切的科学的结果更为有价值。所以介绍科学的方法,是新文化运动者的责任。[11]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科学救国思想达到了高潮阶段。对科学重要性的强调使整个社会的科学氛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科学的普及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促进了现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了充分的准备。不可否认,“科学救国”思想一定的局限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科学救国”并不能根本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而且,时人所理解的科学与当下的科学有一定的差距,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促进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由此可见,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科学救国”的艰途,实为难得。当然,更为难能可贵的,五四时期“赛先生”提出并颇受社会重视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乎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多少具体的科学知识,而在于提出了新思维、新方法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综合以上的分析,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思想文化层面,从生产力发展的视角来考察五四运动也是必要的。在生产力发展的视角下可以看出,生产力发展之于五四爱国运动来说,其作用是显性的,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状况是导致爱国运动爆发的经济根源,而五四爱国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于生产力发展来说,其作用则是隐性的,却又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还是科学技术认识的提升,都是社会生产力得以快速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2.
[2]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2).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23-24.
[4][5]凌耀伦、熊甫、裴倜.中国近代经济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361,362.
[6]荣家企业史料: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64-65.
[7]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M].上海:三联书店1961:21.
[8]科学[J].发刊词,1915年:1.
[9]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J].1914:1.
[10]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J].第6卷第1号.
[11]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况[M].黄山:黄山书社,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