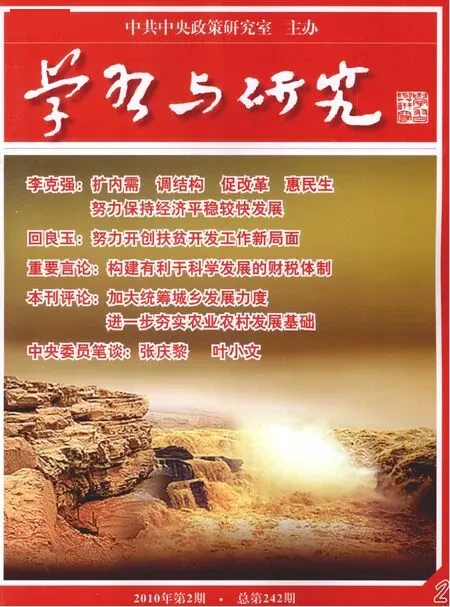“说天话”:知识分子担当责任的独特方式
2010-02-15孙美堂
孙美堂
“说天话”:知识分子担当责任的独特方式
孙美堂
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责任的独特方式是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传统是否存在某些误区?
西方知识分子以为学、求知为使命,知识则以达到普遍性和确定性为目标。为了达到普遍性与确定性,西方思想家习惯以纯概念为对象进行逻辑推演,并对知识大厦的基础进行反思。这种演绎和反思看似远离现实,仿佛上帝在远远地冷观人类,但其社会效应是革命性的。例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推论方式,简直像说天话,与人间无关!但这几句“天话”却导致思想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因为它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把西方以神为中心的宇宙秩序和价值框架给颠覆了!说“天话”的习惯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很普遍。康德问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谢林设定哲学基石是“一”、“绝对”、“上帝”,黑格尔确立“绝对说不出什么”的绝对精神,都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但西方社会完成自己的启蒙和现代化,离不开这些“天话”。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缺少为科学而科学的热情,缺少讲“天话”的学术单纯,他们不以自己为纯知识的生产者,而是维护纲纪、匡扶社稷、忧国忧民的儒生;他们大多把“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作为目的,为学、求知只是一种手段。为学、求知又归结为悟道、明德、修身;要把握的那个“道”,没有任何确定性,神妙无穷。道家谓“道”“唯恍唯忽”,“玄之又玄”;兵家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医术讲“加减临时在变通”;和尚讲“破执”,都是要打破确定性。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化境”。“化境”唯有中国文化才有,它是把确定性消解到至极才有的奇妙境界。你要“穷神知化”,“与天地合其德”,就不是敲定知识的普遍性和确定性,恰恰相反,是要消解这种普遍性和确定性。
中国文化不分“此岸”和“彼岸”,终极和绝对不在具体和相对之外而是在它之中。所谓“道不离器”,“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砍柴挑水无不是道”……总之,形而上与形而下须臾不离。这种思维方式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因为彼岸的东西自己掌控不了,此岸的东西则可以从心所欲。故明德、悟道就不是向外追寻,而是向内开拓,发明本心。这种“反求诸己”的“内在超越路径”也与确立普遍性和确定性相悖。
今天,下意识地拒斥知识与价值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常常以“阶级性”、“具体历史性”为由),仍然是中国知识界的特点。人们习惯下判断、得结论,却很少有人对判断和结论的前提进行批判。很多话语,看似振振有词,实际含混不清,经不起推敲分析。人们仍然对纯粹知识没有兴趣,心思过多聚焦在出谋划策,设计“救世良方”。这种没有学术根基的“招儿”,对文明发展没有实质性意义。
诚然,知识和思想终究是社会现实的表达,终究要为社会服务。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上是对的。但是,如果学以致用就是从政做官、经商下海、做工种地;如果“知识分子”桂冠唯一的优势是,我有个教授、专家、博士的头衔,在市面上比别人混得更好,那就没有起到知识分子应该起并且只有他才能起的作用,没有把知识、学术的独特功能发挥出来。我不反对有些知识分子去“经世致用”,但那不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般模式,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本行,有自己担当社会责任的独特方式,这种方式是社会必需而其他群体又不可能胜任的。显然,这只能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坐而论道,为科学而科学,批判知识的前提与基础,敲定知识、价值的普遍性与确定性,以概念辨析、理性建构、逻辑演绎、数量运算等纯知识的方式来更新人们的视野,以“说天话”的方式来建构新的理念,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常态。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