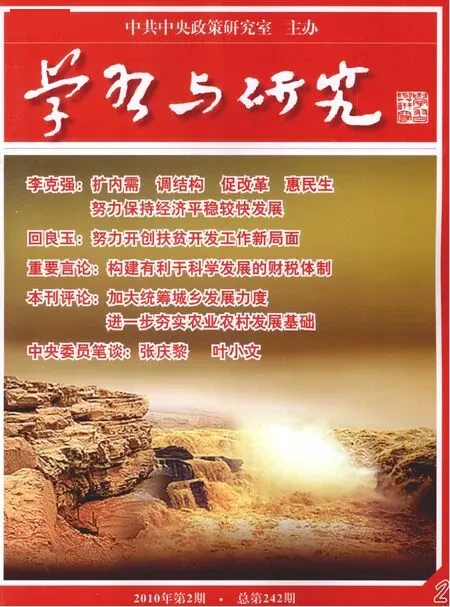严格区分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
2010-02-15陈勇勤
陈勇勤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严格区分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
陈勇勤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是两个不同的经济现象,需要严格区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包含的一个环节,是市场经济下需求无计划性和供给无计划性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已成为自然规律。金融危机纯属人为造成,它来自货币、股票、衍生金融工具以及相关经济现象。经济周期不可能消除,只能设法缓解。因此,经济危机总会出现,只不过有时间持续长短、结果影响大小的区别。金融危机完全可以消除,关键在于要有一系列有效的制度。
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多因素分析;自然规律;人为造成
一、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是两个不同的经济现象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有明确的说明,它是经济周期必然的一个阶段,或者说经济周期循环中必然存在的一个环节。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1]。工业周期也就是商业周期、经济周期。经济活动归结到一点就是交换,甚至可以说,无交换也就无所谓经济。交换联接着供给和需求,或者说,供求的交点即交换。工业代表供给,商业代表需求,也代表交换。因此,工业周期、商业周期和经济周期为同义。
马克思给金融危机的说法是货币危机。不过马克思区分了两种货币危机,一种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它属于经济周期的一个环节;另一种货币危机是“单独产生”的,“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2]。显然,后一种货币危机就是金融危机,但前一种货币危机不属于金融危机。需要注意,金融危机是金融部门爆发危机,而金融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所谓危机实际上是说融通方面出现严重问题。金融危机的出现可以和经济周期无关,但金融危机本身必然会影响经济周期。
二、经济周期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经济周期是经济活动在前行轨迹上规律性出现的波动现象。“时间之箭”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前行是永恒的,前行必然形成轨迹,这条轨迹不可能走出直线,只要表现为曲线,那就是波动。波动必然有峰顶和谷底,所以经济活动有周期也是必然的。“经济下滑和上扬的短期交替就是所谓商业周期”[3]。在人们普遍认同这一点之后,讨论便集中到波长问题上。于是又产生出短波假说、中波假说和长波假说。
循环表明一种规律,周期则表明循环中不断重复的那个峰顶—谷底结构。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衰退,爆发危机?于是又讨论经济波动原因。第一种观点认为,来自内在因素。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过剩。第二种观点认为,来自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比如某种投入品突然价格暴涨、自然灾害等。第三种观点认为,来自货币政策。这还涉及所谓不恰当的政府干预。第四种观点认为,根源来自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但内在因素加大了波动的长期化。
不同观点集中到一起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这就是,时间、地点不同,波动原因必然不同。在上述四种观点中,暂且排除外在因素,避开随机性,可不考虑第二种观点;政策决定货币发行量,如果货币的发行量有一定依据,那么它就涉及金融问题,可不考虑第三种观点。由此可见,可以主要考虑内在因素。
回到经济活动的原点——需求和供给。其中,需求的无计划性是必然的,不可能出现有计划的需求;而市场经济下供给必然也是无计划的,向利润高的行业投资相当于一种本能①。因此,供给大于或小于需求都有可能出现,而供给等于需求只能是理论上的一种假设。在无计划状态下,产品过剩无非就是供给大于需求。当某个社会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后,也就不再出现需求大于供给,于是供给大于需求也就有可能出现,造成产品过剩。
商业周期显然把产品过剩当作转折点,但倍受关注的是它所导致的其他现象。
马克思主要看到了失业。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所说,“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持续的和慢性的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4]。概括说就是:产品过剩→失业→饥寒交迫的失业者起来推翻政府。
J.M.凯恩斯(Keynes)同样注意到就业,不过他主要看到了需求,并强调是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是个谬论,“以此为基础的一种理论显然是不能胜任对付失业和经济循环问题的”[5]②。他把“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周期的时间顺序和期限长短的有规则性”和“危机现象”,说经济周期“是以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变动为诱因”,进而指出:投资量的变动要和消费倾向的变动相抵消,否则就会造成就业量的变动;危机不是起因于对货币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的利息率的上升,而是起因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很难,不是简单的金融当局直接介入就可以奏效,因为这个恢复决定于无法控制的信心恢复(涉及“投资市场心理的深远的变化”);资本边际效率恢复的影响因素还和耐久性资产、存货、周转资本等有关[6]。
凯恩斯曾把《通论》的思路作了如下提示:(1)预期→投资决策和生产决策→产量和就业量的实际水平→收入→消费和投资(储蓄)→产品供求均衡;(2)利息率→货币供求均衡→货币数量→流动资源供给;(3)商品供求→总价格水平;(4)利息率+信心→投资引诱→特定供求关系(利息率+信心)→产量和就业、收入、总价格水平的均衡水平[7]。这里给出了,预期决定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投资决定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产量和就业决定收入,商品供求决定价格,特定供求关系决定产量和就业、收入、价格的均衡水平,投资决定于预期、收入、利息率、信心。由《通论》思路我们可以整理出三组关系式:
a、预期型投资(预期)→产量和就业量的实际水平→收入→消费(消费品消费)和投资(投资品消费)→商品供求关系→总价格水平
b、引诱型投资(利息率、信心)→特定供求关系(利息率+信心)→产量、就业、收入、价格的均衡水平
c、利息率→货币供求均衡→货币数量→流动资源供给
从中我们看出,a组的最终落点是价格,去掉供求环节后的b组等同去掉供求、消费和投资等环节后的a组,c组的货币环节与a、b两组的价格环节有一定的关系。总体上说,《通论》最后讨论的正是“价格论”,价格是商品和货币的交换比例,但价格的直接影响因素不是货币数量,而是商品供求[8]。如果说供求的交点有产量和就业量,那么,价格既是商品买卖的交点,也是劳动和收入的交点。价格通过物价影响购买量从而影响产量,价格通过物价影响工资从而影响就业量。对于价格的两面性,凯恩斯没有很好地研究。
凯恩斯之后,M.弗里德曼(Friedman)看到了货币政策,认为货币供应量的无规则变化导致经济波动。R.E.卢卡斯(Lucas)看到了理性预期,认为存在货币的商业周期。F.E.基德兰德(Kydland)和E.C.普雷斯科特(Prescott)看到了真实商业周期,认为生产率的变化导致经济波动。N.G.曼昆(Mankiw)看到了不完全竞争。
在商业周期的模型中,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产量、投资、消费和劳动工时[9]。产量和劳动工时就是产量和就业,消费和投资就是收入,就业涉及工资和劳动工时。这反映出,商业周期离不开产量、就业、收入三个要素。20世纪70年代的商业周期模型至少还注意到货币导致的价格波动[10],后来的商业周期模型就很少考虑价格了。
P.克鲁格曼说,“市场价格会向着一个使供给数量等于需求数量的水平运动。但是这个均衡价格却不一定会使买方或者卖方满意”[11]。实际上凯恩斯之后的供给学派也有其理论说服力,并非“萨伊定律”的简单翻版。他们坚信供给决定需求,只不过供给出了问题,即生产过剩是劣质品过剩,市场充塞旧商品,缺少新产品,这时政府干预刺激需求,反倒造成恶性循环,加剧经济危机[12]。卢卡斯、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都认同供给学派这方面的观点,并把拉弗曲线反映的税收凸现出来。税收无疑会影响收入,从而有了最优税收与负福利收益的关联[13],很像供给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契合。于是又都回归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说的西方经济学的伦理学传统[14]。意味着用符合伦理的税收来熨平经济波动。
经济变化涉及很多“影响变化的相关因素”[15],其中包括文化因素。这正是我多年来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金融危机
金融部门的物质要素是金融资产,主要包括贷款、债券、股票和银行存款等四种。金融市场是人们用储蓄购买金融资产的投资场所[16]。金融危机就是包含在金融市场的波动当中,反映了波动的走坏趋势。
金融危机一定和金融资产有关。债券相当于特殊存款,而贷款、银行存款都以货币表现出来。因此,金融资产实际上可以集中在货币和股票上。这时,银行在货币体系中起着主要作用,证券交易所在股票体系中起着主要作用。可见一旦发生金融危机,最坏的结果,要么表现为银行挤兑—银行破产,要么表现为狂抛股票—股市暴跌—券商破产。前者的原因在货币失信,后者的原因在泡沫破灭。
货币本身是一种信用。信用指遵守承诺。经济上的借贷行为自古被称作信用,显然包含了遵守承诺的意思。请注意,实物(如珠宝等)法定(公认)的货币是真正货币,其中特别是纯金币和纯银币。非纯金、非纯银的金属币,都应当看作面值币。纸币(钞票、银行券)是典型的面值币。从货币的主要三个职能来看,撇开价值尺度、交换媒介(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不谈,储藏手段指“在一定时间内作为购买力的保存手段”,而且这一点是“必要的”,或者说“储藏手段的作用是必需的”,这关键就在于“随时间推移能保持购买力”[17]。对此我认为,更重要的应当是保值,不能保值的货币也就没有储藏的价值。所以,保值实际上应当看作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的结合。保值作用的次序为:实物货币→金属面值币→纸币。贬值作用的次序则相反,即:纸币→金属面值币→实物货币。
货币发行超量,股市泡沫破灭,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泡沫破灭,最终祸水都汇聚到货币身上,显示出贬值。这必然也就丧失了货币本身的信用。银行破产给金融危机作了交代,金融部门成了骗子。金融部门在制造货币、股票、衍生金融工具等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一系列“促销”行为,骗的是信用,最终也尝到了失信的苦果。但金融危机给民众的伤害更大,毕竟货币等信用工具等同财富[18],贬值等于相应的财富无形中消失了。
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未来毁灭人类的,将是金融部门。用金融部门之水能载经济之舟、也能覆经济之舟来形容,大概并不为过。金融部门一旦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的,“载舟”作用将越来越弱化,而“覆舟”作用将越来越强化,最终经济完全覆没了。
有效的制度,对金融部门是至关重要的。
四、经济周期问题能否解决
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市场经济下需求的无计划性和供给的无计划性都是必然存在。
凯恩斯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是严格以总产量为基点。这相当于总产量具有两面显示,一面以购买显示总需求,另一面以销售显示总供给。正因为总产量本身就是总供给,接下来就是有效需求恒等于总产量,否则也就无所谓有效需求,也明白了为什么凯恩斯说“总需求函数,这个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忽略的概念”[19]。在总需求为有效需求的前提下,有效需求等同总需求。总产量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交点,就业量也在此点,所以就业量对应总产量。
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意味着既没有求大于供,也没有供大于求。我们发现,虽然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是假设产量由预期决定[20],但实际上是将总产量看作既定③。在这一前提下,才有就业、收入相应地去和产量达到均衡状态。可见又要收入对应有效需求。就是说,总产量→总就业量→收入→有效需求反映出有效需求的实现,收入→有效需求→总产量→总供给反映出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实现。
凯恩斯的收入概念只针对企业主,指的是利润。企业主收入可分解为补充成本、消费和储蓄三个部分,包括补充成本就叫毛利润,减去补充成本就叫净利润[21]。凯恩斯又给出一种表述,有效需求是与总就业量相对应的总收入[22]。这似乎是说,有效需求只和劳动者工资有关,而和企业主利润无关。如果总就业量对应“利润最大化的就业水平”[23],那么这一点与“有效需求和企业主利润无关”这一点又怎么来联系呢?总之,无法解除我们的疑问,有效需求为什么不涉及企业主收入。凯恩斯给了一个推导:收入=消费+投资,储蓄=收入-消费,储蓄=投资[24]。但这仅仅是说消费在推导中被消元,并不能证明收入中不存在消费这个分解部分了。
再看凯恩斯给出的一个表述,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每一个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有效需求的水平将有一个与之相应的总就业量,而且这个有效需求按照一定的比例分解为消费和投资”[25]。这似乎是说,有效需求对应总工资(总就业量的价格计量),总工资又可分解为消费和储蓄。由此得出,消费品已经供求相等,储蓄转化的投资使投资品得以供求相等。撇开消费品不谈,如果说投资品产量由预期决定,那么怎样估算出工资储蓄使供求相等的这部分产量占总产量的多大比重,因为这之后才能决定投资品总产量。
由于总产量概念存在模糊不清之处,所以有了克鲁格曼的再三强调,“准确地说,总产出是指经济在给定时期内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的生产量——通常是一年内。其中不包括作为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投入品的产品和劳务(投入品通常被称为中间产品)”[26]。
可见,凯恩斯悄然将总产量以既定来使用,有意避开了总产量实际上无法确定的麻烦。很明显,既定在这里相当含糊,原本是不确定的。总产量无法确定的根本原因是供给的无计划性必然存在。既然如此,总收入就不能确定,总就业量也不能确定。那么产量、收入、就业达到均衡状态就成了虚构。这时的总需求也不会是有效需求。而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最终也只能看作是一种趋势。
既然市场经济下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只能看作是一种趋势,不可能保持一种均衡状态,生产过剩的危机也就无法避免。因此,经济周期已成为一种必然。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周期问题不可能解决。当然这是我的看法,即经济周期本身具有必然性。另外,有人是从解决措施的局限性上来看问题。认为时至今日,人们还只能依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经济衰退或者防止经济过度强劲扩张”,前者针对货币量或利率,后者针对税收或政府支出。但“这些政策工具的作用并不完美”,“并不能完全消除经济波动”,所以“商业周期最终仍将伴随着我们”。显然,人们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设法缓解商业周期”[27]。
经济周期并非通常说的那样百分之百地坏。应当看到,产品过剩在一定周期形成经济危机,而危机爆发后也会自动出现产业调整,就是说,产品过剩的产业自然会把相对劣质的企业淘汰,将相对优质的企业保留下来,使该产业在优胜劣汰后在新一轮从类似供给等于需求的起点上开始供给。供大于求—优胜劣汰—供求趋平,这就是市场经济。
有一点我们也可以去注意,经济周期性失业、产业结构性失业、游戏规则性失业是三个不同的问题,需要分别做出解释。
五、金融危机问题能否解决
提及金融危机问题能否解决,这一点实际上已不需要多说。只要有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完全可以不出现金融危机。
金融部门的高薪实属于不正常的现象。问题很简单,这个高薪只能来自金融部门的利润,而且先有高利润、之后才能有高薪,二者正相关。如果高利润与“覆舟”作用正相关,那么金融部门的利润必须控制在适度的位置上。
金融部门的利润适度,那么金融部门的薪酬相应地也会适度。不过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部门高薪是一种激励措施,有减少金融犯罪的作用。这似乎是“高薪养廉”的翻版。现实已证明,有效的制度才能解决金融犯罪问题。
虚拟经济始终是产生泡沫的土壤④,投机又是助长泡沫的加速器。实质为骗信用的金融部门的“促销”行为,相当于金融犯罪,因为它不过是披上一块“合法”的面纱。这一点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是用有效的制度完全可以杜绝的。
注释:
①我一直认为,如果最简单地说,经济活动无非是由需求、供给、管理三个因子构成。其中,管理的有效总是和一定条件相对应(陈勇勤:《需供管演进假说:探索经济史研究新体系》,《南都学坛》2006年1期)。需求和供给二者又涉及一个次序问题。美国学者G.吉尔德(Gilder)有段话反映出这一点,“在经济学中,当需求在优先次序上取代供给时,必然造成经济的呆滞和缺乏创造力、通货膨胀以及生产力下降”([美]G.吉尔德:《财富与贫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45页)。对次序的看法不同,也就有了一种观点认为需求优先于供给或者需求决定供给,另一种观点认为供给优先于需求或者供给决定需求。
②我们认为,凯恩斯对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假说有误解。实际上,萨伊是基于短缺经济的现实而得出的结论,凯恩斯是基于过剩经济的现实而得出的结论。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状态背景。
③凯恩斯在1936年《通论》的“德文版序”和“日文版序”中,都提到马歇尔生产和分配理论,说“他的在既定产量下的生产和分配的理论”([英]J.M.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德文版序”,“日文版序”)。由此可见,凯恩斯也可以心照不宣地使用这个研究方法。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提到,“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制造出虚拟资本”(第451页);“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第529页)。
[1][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162,35.
[3][11][16][17][18][26][27][美]P.克鲁格曼、R.韦尔斯.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6][7][8][19][20][21][22][23][24][25][英]J.M.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法文版序”,296-301,“法文版序”,“法文版序”,30,44,53,51,52,59,265.
[9][10][13][美]J.格林伍德.现代商业周期分析,南大商学评论(经济学版):第14辑[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34,32,36.
[12][美]G.吉尔德.财富与贫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5-51.
[14]Sen,Amartya K.On Ethics and Economics.Basil Blackwell,1987,pp.2-7.
[15][美]P.菲利普斯.经济转型和增长,南大商学评论(经济学版):第14辑[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67.
(责任编辑 钱亚仙)
F832.59
A
1008-4479(2010)02-0048-05
2009-01-15
陈勇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