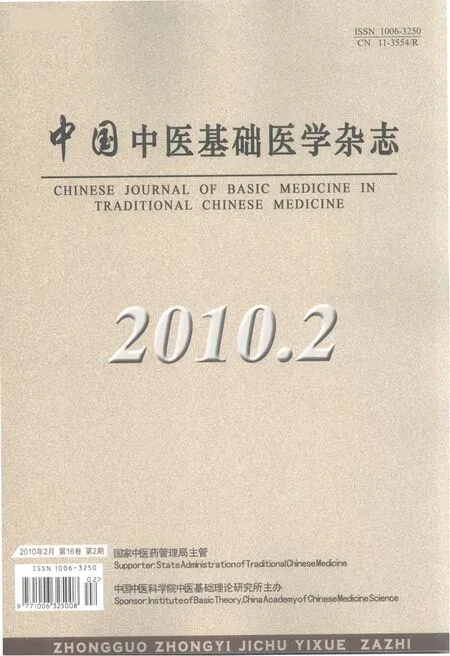历代中医学家对“三因制宜”学术思想的认识
2010-02-11李志更
李志更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三因制宜,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中医学的理论特色和精华,贯穿于中医学的发展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相互结合。本文主要是从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上考查其学术源流与发展路径,探讨其理论内涵,现综合历代医家对其认识,浅述于下。
1 秦汉及以前的阶段
中医学从诞生发展到秦汉时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无数医家知识和经验的总结。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了对许多种内科疾病的记载。从现存的书籍来看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 》是中医学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而在这 3部著作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三因制宜”学术思想。
纵观《黄帝内经》就可知其奠定了中医学“三因制宜”学术思想的基础。在因时制宜方面,《内经》对时令与人体生理、发病、治疗、预后、养生等多方面的关系都有所论述,初步建立了因时制宜的理论构架。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灵枢·寒热病》中记载有:“春取络脉,夏取分腠,秋取气口,冬取经输,凡此四时,各以时为齐”等等。此外,《内经》中的运气七篇是研究超年节律时序变化的理论基础,对于不同年岁的气候特点及易感疾病等都有讨论。
在因人制宜方面,《内经》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个体在禀赋寿夭、生理发育、情志心理、生活方式、发病及预后等几个方面的区别,并进一步提出了因人制宜的具体方式,包括临证时要参考性别、年龄、职业、体质等因素。如《素问·示从容论》指出:“年长则求之于腑,年少则求之于经,年壮则求之于脏。”《素问·三部九候论》中记载有:“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内经》中就有了五态人、阳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划分法。
在因地制宜方面,《内经》中指出不同地域的地理气候、物候物产、生活环境等常对人的体质、发病、寿命等产生不同的影响。如《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以及《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载:“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故导引按蝏者,亦从中央出也”等等。
《难经》相传为战国时秦越人所撰,书中有“男子”、“女子 ”、“老人”、“少壮 ”等分类 ,如 《难经 ·四十六难》中载有:“老人卧而不寐,少壮寐而不寤者,何也?然:经言少壮者,血气盛,肌肉滑,气道通,荣卫之行不失于常,故昼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气衰,肌肉不滑,荣卫之道涩,故昼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可认为与因人制宜相关。书中还体现了因时制宜的思想,如《难经·七十难》记载:“春夏刺浅,秋冬刺深者,何谓也?然:春夏者,阳气在上,人气亦在上,故当浅取之;秋冬者,阳气在下,人气亦在下,故当深取之。”
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书中除有 “虚人”、“强人”、“羸人”、“酒客 ”、“肥人 ”、“瘦人 ”等记载外,还记载有“四时加减柴胡饮子方”以及“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正月勿食生葱,今人面生游风……十一月、十二月勿食薤,令人多涕唾”等等。这些内容都可认为是三因制宜思想的体现。
2 三国至唐宋阶段
在这一阶段,我国先后存在过许多或大或小的封建政权,医学史上,西晋·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著,也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对针灸理论和临床经验的又一次总结。书中禀承 《内》、《难》的思想并指出:“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也(《针灸甲乙经·内外形诊老壮肥瘦病旦慧夜甚大论第六》)。”还记载了一些因时制宜的方法,如“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荥;时主夏,夏刺腧;音主长夏,长夏刺经;味主秋,秋刺合(《针灸甲乙经·五脏变腧第二》)。”在因地制宜方面,《针灸甲乙经·逆顺病本末方宜形志大论第二》记载有:“东方滨海傍水,其民食鱼嗜咸……西方水土刚强,其民华食而脂肥……故圣人离合以治,各得其宜。”《针灸甲乙经》中有“肥人 ”、“瘦人”、“常人 ”、“壮士”、“婴儿”、“美眉者”、“恶眉者”等记载,除五态人、阳阳二十五人的划分法外,还有按五脏的分类法,如“五脏皆小者……五脏皆大者……五脏皆高者……五脏皆下者……五脏皆坚者……五脏皆脆者……五脏皆端正者……五脏皆偏倾者(《针灸甲乙经·五脏大小六腑应候第五 》)。”
《千金方》是“药王”孙思邈的重要著作,也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孙思邈在书中总结了唐以前的医学成就并指出:“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薄脆,腠理开疏,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理闭塞,用药重复(《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思想。孙思邈还指出气在人体运行的时月顺序:“凡气冬至起于涌泉,十一月至膝,十二月至股,正月至腰,名三阳成。二月至膊,三月至项,四月至顶(《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以及一些因时养生的方法,并强调“衣食寝处皆适,能顺时气者,始尽养生之道(《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在针灸学方面,孙思邈亦认为,“灸刺大法:春取荥。夏取输。季夏取经。秋取合。冬取井(《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以及“针禁忌法: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 》)”。
唐·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整理了前人大量的医学文献,从四时外感病的角度论述了时令与疾病的关系,并将理论研究与治疗方药全面系统地结合起来。在治法上认为:“春夏无大吐、下,秋冬无大发汗。发汗法,冬及始春大寒,宜服神丹丸,亦可摩膏火灸。若末春、夏月、初秋凡此热月,不宜火灸,又不宜厚覆,宜服六物青散(《外台秘要·方卷第一·诸论伤寒八家合一十六首》)。”此具有鲜明的因时制宜思想。书中还记载了妊娠随月数服药及将息法和小儿变蒸论以及五行之人的特点。
唐代著名医家王冰是全面注释《素问》的第一人,对其中的三因制宜思想多有发挥。王冰也是传承运气之学的第一人,他将“运气七篇大论”补入《素问》,从而使运气学说完整地纳入中医理论体系。王冰的著作《玄珠密语》、《天元玉册》、《元和纪用经》对运气学说的内容和临床运用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钱乙被尊称为“儿科之圣”,其著作《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书中记载了小儿变蒸理论,并对小儿的抽搐、咳嗽、夏秋吐泻等提出了因时制宜的方法。南宋医学家陈自明提出了“大率治病,先论其所主。男子调其气,女子调其血。气血,人之神也,不可不谨调护(《妇人大全良方·调经门》)”的因人制宜原则。南宋医家杨仁斋亦指出:“肥人气虚生寒,寒生湿;湿生痰。瘦人血虚生热,热生火,火生燥。故肥人多寒湿,瘦人多热燥也(《仁斋直指方论·卷一·火湿分治》)。”
3 金元阶段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出现了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等杰出医家,他们在立论与风格上虽各有千秋,但均对“三因制宜”的学术思想有相当的精通和运用。
在因时制宜方面,补土派代表人物李东垣指出:“凡用药,若不本四时,以顺为逆。”并强调“大法春宜吐,像万物之发生,耕、耨、科、斫,使阳气之郁者易达也。夏宜汗,像万物之浮而有余也。秋宜下,像万物之收成,推陈致新,而使阳气易收也。冬周密,像万物之闭藏,使阳气不动也。”在其著作《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中还有“四时用药加减法”、“随时加减用药法”等论述,其弟子罗天益还提出了“舍时从证”的治疗思想。张从正还很重视对运气的运用,谓“病如不是当年气,看与何年气相同,只向某年求活法,方知都在至真中”。火热派代表人物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妇人胎产论》中提出了四物汤的四时增损法:“春倍川芎……夏倍芍药……秋倍地黄……冬倍当归……此常服顺四时之气……春防风四物……夏黄芩四物……秋天门冬四物……冬桂枝四物……此四时常服随证用之也。”攻邪派代表人物张子和认为,“人之伤于寒也,热郁于内,浅则发,早为春温;若春不发而重感于暑,则夏为热病;若夏不发而重感于湿,则秋变为疟痢;若秋不发而重感于寒,则冬为伤寒。故伤寒之气最深。”滋阴派代表人物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有达生散、愈风汤以及咳嗽一病的因时加减之述。
在因地制宜方面,刘完素认为:“东南方阳也,阳气降于下,故地下而热也。西北方阴也,阴气盛于上,故地高而寒也(《新刊图解素问要旨论》)。”张子和更是在《儒门事亲》中指出:“东方濒海卤斥,而为痈疡;西方陵居华食,而多頵腄赘瘿;南方瘴雾卑湿,而多痹疝;北方乳食,而多藏寒满病;中州食杂,而多九疸、食痨、中满、留饮、吐酸、腹胀之病。盖中州之地,土之象也,故脾胃之病最多。其食味、居处、情性、寿夭、兼四方而有之。其用药也,亦杂诸方而疗之。”李东垣在《医学发明·脚气总论》中曰:“北方之疾,自内而致者也。南方地下水寒,其清湿之气中于人,必自足始。北方之人,常食潼乳,又饮之无节。”朱丹溪的著作中记载了“西北二方,急寒肃杀之地,故外感甚多;东南二方,温和之地,外感极少(《丹溪心法·中寒二》)。”
在因人制宜方面,朱丹溪可谓四大家中最为重视因人制宜的医家了,在其著作中常可看到肥人、瘦人、肥白人、黑瘦人等字样,并认为 “肥者,血多湿多 ;瘦者,气实热多。白者,肺气弱,血不足;黑者,肾气有余(《丹溪手镜·察视二》)。”医家张子和的著作中有田野贫寒之家、富贵膏粱之家、贫难之人、富贵之人、贫乏之人、大人、小儿、男子、妇人、老人等区分。如《儒门事亲·风门》记载“凡富贵之人痰嗽,多是厚味所致。《内经》云:所谓味厚则发热。可服通圣散加半夏以止嗽;更服人参半夏丸,以化痰坠涎、止嗽定喘。贫乏之人,多感风冷寒湿。《内经》曰: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可服宁神散、宁肺散加白术之类。”刘完素的著作中也有对肥人、瘦人、长人、短人、大人、小人的划分,并指出“血实气虚则肥,气实血虚则瘦。所以肥者能寒不能热,瘦者能热不能寒(《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长人脉长,短人脉短,肥人脉沉,瘦人脉浮(《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脉论第二》)”。
三因制宜学术思想发展到金元时期,基本上形成了有医论,有运用,理法方药相融贯的格局,在传统中医学角度已经开始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4 明清阶段
明清时期是距现今较近的历史时期,也是医家众多的一个历史时期。温病学派在这一时期的兴起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四时温病发生的时序特点,是在因时制宜方面对三因制宜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概而言之,春季好发春温、风温;夏季易发湿温、暑温;秋季易感秋燥;冬季易发冬温等。正如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卷十·幼科要略·春温风温》中所言:“春季温暖,风温极多。温变热最速,若发散风寒消食,劫伤津液,变症尤速。”《叶天士医案》中亦指出:“湿温长夏最多,湿热郁蒸之气由口鼻而入。上焦先病,渐布中下。”叶天士还很重视因人制宜,并将其与温病理论结合起来,如《叶天士医案》中记载:“瘦人阴虚,热邪易入于阴,病后遗精,皆阴弱不固摄也。”“稚年纯阳体质,热症最多”。《临证指南医案·卷十·幼科要略》亦记载:“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此外,在叶氏的著作中,还有“粤东地卑多湿,阳气多泄”(《叶天士医案》)等有关因地制宜思想的论述。
张景岳也十分重视三因制宜思想,在《景岳全书·卷之十九·外感嗽证治》记载:“外感之证,春多升浮之气,治宜兼降,如泽泻、前胡、海石、栝楼之属是也。夏多炎热之气,治宜兼凉,如芩、连、知、柏之属是也。秋多阴湿之气,治宜兼燥,如苍术、白术、干姜、细辛之属是也。冬多风寒之气,治宜兼散,如防风、紫苏、桂枝、麻黄之属是也。经言岁气天和,即此之类。然时气固不可不知,而病气尤不可不察,若当其时而非其病,及时证有不相合者,又当舍时从证也。至于各脏之气,证有兼见者,又当随宜兼治,故不可任胶柱之见。”四时之气不同,在用药上所兼之法也自然不同。关于因人制宜的思想,张氏在治疗噎膈的方法中有所体现,如《景岳全书·卷之二十一·噎膈》谓:“凡肥胖之人,鲜有噎证,间或有之,宜用二陈加人参、白术之类。血虚瘦弱之人,用四物合二陈,加桃仁、红花、韭汁、童便、牛羊乳之类。七情郁结而成噎膈者,二陈合香附、抚芎、木香、槟榔、栝楼、砂仁之类。饮酒人患噎膈,以二陈加黄连、砂仁、砂糖之类。”
清·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明确指出了医者治病应本于四时之律和地宜之律。《医门法律·卷一》曰:“凡治病,而逆四时生长化收藏之气,所谓违天者不祥,医之罪也。”“凡治病,不察五方风气,服食居处,各不相同,一概施治,药不中窍,医之过也。”书中还详细记载了不本四时之气对五脏的伤害以及五方的地域特点等。
陈士铎所著的《石室秘录》将三因制宜思想融于各种治法之中,书中提出男治法、女治法、肥治法、瘦治法、日治法、夜治法、富治法、贫治法、老治法、少治法、东南治法、西北治法、春夏治法、秋冬治法等,分析其理,详析治法,明列方药,可谓深明三因制宜思想。
徐灵胎也指出,对待病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如《医学源流论·病同人异论》曰:“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不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心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
5 小结
纵观中医学发展史,可知历代医家对于三因制宜思想都是很重视的。概言之,三因制宜思想是对时间、地域、性别、年龄、职业、境遇、体质等因素对于人体健康影响的全面概括,是从天象、地象、人象的角度对人体状态进行全面的参照,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故而“三因制宜”学术思想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和实践价值,是对中医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并对后世医家的遣方用药产生了深远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