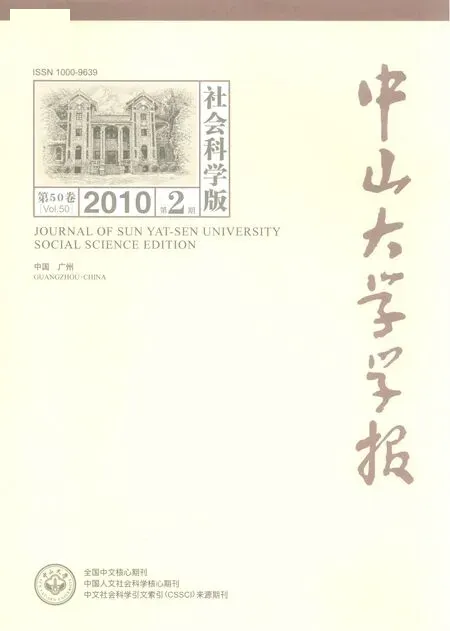多头怪兽与政治喜剧*
——《亨利六世》中篇里凯德的戏剧位置
2010-02-10娄林
娄 林
在《亨利六世》中篇,凯德(Jack Cade)①对莎剧文本的分析中,凯德这个角色一直少有人关注。以 Shakespeare Quarterly为例,这么多年来,仅有两篇凯德主题的论文,一篇仅1页,一篇仅3页,处理琐碎的文献问题:Stephen Longstaffe,“Jack Cade and the Lacies”,Shakespeare Quarterly,Vol.49,No.2,(Summer,1998),pp.187-190;D.Allen Carroll,“Johannes Factotum and Jack Cade”,Shakespeare Quarterly,Vol.40,No.4,(W inter,1989),pp.491-492。Ellen C.Caldwell有长文《凯德和莎士比亚》(Jack Cade and Shakespeare's“HenryV I,Part2”),载于 Studies in Philology,Vol.92,No.1(W inter,1995),pp.18-79。这是少数直接处理凯德这一主题的论文之一,只是,他一直在历史资料和莎士比亚的历史处境中打转,却对莎士比亚如何写作漠然视之。第一次与政府军对垒时,对手是史泰福德(Stafford)兄弟。凯德向他们宣扬了自己的“高贵血统”之后,威廉·史泰福德不屑一顾,说道:“杰克·凯德,这不过是约克公爵教给你的说辞罢了。”(4.2.147)②本文依据的 Henry V I2是 Arden版,Andrew S.Cairncross编,London:Methuen,1969年;4.2.147表示第4幕第2场第147行,下同;译文因求行文顺畅之故,勉力自行译出。这恰好和约克早前提到的情形(3.1.355以下)吻合,但奇怪的是,这本该是相当隐秘的谋反计划,史泰福德兄弟从何得知呢?更奇的是,早在第1幕,军械工彼得(Peter)状告师傅霍纳(Horner)时,说霍纳声称约克才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1.3),难道约克谋反已经成为大街上的秘密?可是,随后亨利六世听从神意的荒唐判决似乎表明(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亨利六世要回权杖后第一次处理政务),贵族们很愉快地认为这种传闻纯属无稽之谈。我们再看第5幕第1场,约克从爱尔兰率军抵达肯特郡之后,三言两语就糊弄了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然后俩人手挽着手晋见亨利六世(5.1.57)。
我们可以设想,在彼得状告霍纳一案之后(也许之前),对约克的忠诚程度究竟如何,很多人都心存狐疑,但是白金汉公爵和列席聆听亨利六世判决军械师徒一案的贵族们,也就是说应该真正具有政治决断能力的人,对这一事件的真相却毫不追究。判断出真相的是史泰福德兄弟,但他们当中只有汉弗莱拥有爵位,也不过是 Sir这样一个荣誉爵位,可是想像,这或许来自于他英勇的战功;以语言表达出真相的威廉·史泰福德,则完全没有任何爵位。某种程度上,约克之心其实已如司马昭之心,但面对这一情形,莎士比亚笔下人分三种:第一类是霍纳这种人,知道司马昭之心,却对此并不在意,他们并不关心谁当王(这在第4幕第8场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随着克利福德[Lord Clifford]和凯德的说辞而左右摇摆,最终凯德失去耐心,大骂他们:“这帮民众真如鸡毛,骑墙两边倒”);第二类是白金汉公爵诸位,他们当然很关心谁是王,但是,眼前的政治斗争(他们正在密谋干掉葛洛斯特[Gloucester])让他们忽视了约克,或者他们并不认为,约克是能给自己制造政治压力的对手;第三类是即将战死的史泰福德兄弟,他们知道真相,但死亡很快降临,带走了真相。这恰恰昭示了当时的政治情形:所有的人都只关注个体的利益,而对于共同体福祉的追求,随着塔尔伯特(Lord Talbot)父子的战死,已经完全遁于无形①亨利六世言必称上帝。3部《亨利六世》之中,他一个人呼唤上帝之名的次数,比其他所有人都多。他是一个虔诚的圣徒,这恰恰说明,他缺乏现实的政治头脑,缺乏对共同体福祉的追求。他曾称军械师傅霍纳是 traitor(叛国者,2.3.97),这种小题大做足见他愚蠢的政治才能。。正是由于这种政治处境,约克才能够隐藏他的计划,立足于约克和这种政治处境,我们才能理解凯德在剧中的地位。
我们先回到凯德在剧中的第一次出场(3.1)。凯德最初登场的形式并不是戏剧行为,而是言辞,确切地说,是约克的独白(3.1.355以下)。这一幕恰好发生在群臣共同密谋处置葛洛斯特之后,期间穿插了两条消息:法兰西的彻底丧失和爱尔兰的叛乱。当法兰西彻底丧失的消息传来,在场的红衣主教、王后和萨福克众人均毫无反应,只有亨利六世说了句:哦,上帝的旨意。倒是约克的苦楚似乎更甚,但他苦楚的原因是动物性的原因:猎物的丧失。约克和那些不苦楚的人区别其实不大,他们都像动物一样追逐猎物,而不是像人一样,对城邦的共同福祉有所追求。随后,约克利用爱尔兰动乱之机,要求带兵平定动乱(形式上倒有点像恺撒出任法兰西总督)。这样的背景,清楚地显示出政治斗争线路的转移:葛洛斯特彻底失势,但众位贵族还不知道下一个对手是谁。与此相反,约克对这一切早已了然于胸。某种程度上,《亨利六世》中篇基本上就是按照约克谋划的情形发展,他比剧中其他人头脑都更清醒。独白这种游离于戏剧人物的语言方式,恰好表明了他清醒的特征。约克提起凯德,就出现在这样清醒的独白中。
实际上,第1幕第1场的结尾就是约克的独白。我们可以把这个独白看做《亨利六世》上篇的剧情回顾:法兰西土地的逐渐丢失;也可以把这个独白看做《亨利六世》中篇的剧情梗概:约克自己的阴谋。独白清楚地表明,约克在某种程度上凌驾于剧情之外:他不但是剧中人,同时也是清醒的局外人②许金:《直接的自我表白》,杨周翰译,载《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9页。许金注意到独白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但他没有留意到进行独白(尤其是长篇独白)的角色在戏剧中的位置。。第3幕的独白正继承了这一特征。这次独白开始的两个词是:现在(now),约克。“现在”表明,约克已经知道,现在就是那个最好的政治 kairos(时机),约克这么早就自呼己名意味着,他认为自己现在应该作为一个独一的人物登场了。约克在本剧的第一次独白,却把“约克”这一名字隐藏在中间,或者延宕于结尾。然后,他的时态一转,连续用了两个will和一个 shall,预告了他将要带来的残酷未来。之后是过去时态:“我已经(I have)唆使了一个顽固的肯特郡大汉:约翰·凯德。”现在、将来和过去时态的融合,恰恰反映了约克的“先知”视角。在《伊利亚特》第1卷里,荷马写道:
……接着起身的,乃是
巧合的是,莎士比亚和荷马的时态用法完全一致,都是现在、未来再到过去。卡尔卡斯是一位真正的先知,而约克只是自以为的先知——但是,至少在《亨利六世》中篇中,约克的确是一位先知。他鼓动凯德,就因为他当时预料到今天的情形,并且,他相信,未来还会在他的预料之中。约克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之中说出凯德之名,确切地说,约克是在述说某种自己掌控之内的东西。
独白除了使言说者游离于剧情之外,还是一种自言自语。约克在这次自言自语中,将一半的篇幅给了凯德,而第一次独白里,他3次以“约克”自陈,10次说起“我”,甚至还有一次以“你”相称,展开自我的对话。我们再举一例,约克的儿子理查手刃亨利六世之后,他的独白几乎通篇都是“我”(《亨利六世》下篇,5.6)。这说明,独白也是一种自我描述。除了独白这种形式之外,在独白中,约克也清楚地说明,他如何训练凯德、考验凯德,并授予各种机宜。这就是说,凯德随后的行为都出自约克的安排,就好像是约克自己的行为。所以,约克在独白中花去一半的篇幅详细描述凯德,或是因为,凯德恰如他灵魂的一部分,约克不过是夫子自道,或者严格地说,是在描述自己灵魂的一部分。
那么,凯德是约克灵魂的哪一部分?在《王制》第4卷435c以下①《王制》译文参见《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随行文标识斯特凡编码,页码不再另行标出。,苏格拉底向格劳孔引入灵魂的三种组成部分:欲望、血气和理性;随后的 5至7卷探讨哲人王的灵魂,8至9卷探讨僭主的灵魂②参见Michael Palmer:《柏拉图〈王制〉中的王者、哲人和僭主》,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第18辑《血气与政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以下。。《王制》对灵魂的讨论,奠定了古典政治哲学对人类灵魂的根本看法,此处不详谈,而是以这一视野为基础,分析凯德和约克之间的关系。凯德说过一句名言:“只有狂乱无序,才是我们真正的秩序。”(4.2.181-182)这不像理性的言语,更能证明凯德缺乏理性的是他的种种行为:荒唐的审判和任性的杀戮③参见 CraigA.Berntha,《凯德的法律狂欢》(Jack Cade'sLegal Carnival),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Vol.42,No.2,Tudor and StuartDrama(Spring,2002),pp.259-274.。苏格拉底告诉格劳孔,欲望就是“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等物欲骚动的东西”(《王制》439d),血气则是天生的激情,如果不受败坏的话,恰好可以作为理性的助手。凯德要满足的是什么?“要你们拥我为王”(4.2),要以自己之口制定法律(4.7),但是他并不知道法律是什么。虽然他要进行改革,但事实上,他的改革只是破坏:杀人、打开监狱、摧毁宫殿。这些行为,作为一个有王族血统的约克,他想做而不可以做,他必须要像一个王者一样建立秩序,而不仅仅是拆毁秩序。相反,凯德完全无需任何秩序。但是,约克要建立自己的秩序,就必须首先破坏亨利的秩序,所以他极其渴望破坏亨利的现有秩序,这个时候他就是凯德,简言之,破坏的、非理性的欲望。在《王制》第9卷,苏格拉底用一个比喻形容这种欲望:请设想一只很复杂的多头怪兽(588c)。我们可以认为,凯德是一种败坏的激情引导下的欲望,所以他的破坏才无所顾忌。但是,这恰恰是约克灵魂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约克必须具备这种低俗的破坏欲望,才能够破坏现行的政治秩序,这是他建立自己的政治秩序的基础。
凯德的一切混乱行为都来自约克的鼓动和策划,所以,如果约克不能称之为有理性的话,至少可以说,他清醒地计算了凯德行为的始终。在描述寡头政制的时候,苏格拉底对阿得曼图斯说,在这种原则统治下,理性和血气将被迫折节为奴,理性只被允许计算和研究怎样更多地赚钱(《王制》553d)。约克的灵魂计算的不是赚钱,而是如何攫取统治英国的地位,他的理性实际上出于血气和欲望的支配(僭主的灵魂)。凯德呢,则是在血气和欲望支配的理性算计之下,得以放纵着低俗的破坏欲望。换言之,在《亨利六世》中篇里,凯德这个角色并不占据一个真正反叛的角色,他只是约克灵魂中破坏欲望的戏剧体现。
《亨利六世》下篇秩序完全崩溃,戏剧展现的就是约克父子的叛乱。但是,《亨利六世》中篇还只是处在“混乱的边缘”④Tillyard,Shakespear's History Plays(《莎士比亚的历史剧》),Penguin Books,1944,p.194.,当然这是个一触即碎的边缘,凯德恰恰是继爱尔兰的动乱之后,把混乱推向了秩序即将崩溃的边缘。详察最后一幕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最后一幕极短,只有3场,第1场还穿插了伊登(Iden)呈现凯德人头的情节,后两场才是约克破坏现行秩序行为的公开亮相,这与其说是在延续《亨利六世》中篇的剧情,不如说是为了衔接《亨利六世》下篇。随着凯德的死亡,他在《亨利六世》3部剧中的作用也告完成,而这个位置恰恰是约克叛乱明目张胆的开始,这就是说,凯德是衔接混乱和叛乱的最后一层薄膜。《亨利六世》中篇第5幕第1场就是这个衔接:伊登提着凯德的人头晋见亨利六世。注意莎士比亚插入这个情节的戏剧时机:约克刚刚糊弄了白金汉公爵,正在继续糊弄亨利六世,约克告诉他,自己兴兵一是为了赶出萨默塞特(Somerset),一是为了平定凯德,随后伊登提上凯德的人头。这一情节转换彻底终结了凯德的戏剧任务,约克不再需要凯德,作为灵魂中混乱的欲望,现在直接让位于建立新秩序的欲望。亨利六世的话倒是一语中的:凯德活着时给我制造了那么多麻烦(trouble),现在他死了。约克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亨利六世之下的臣子,根本不认可亨利的统治秩序,而是要建立一个和亨利六世同一个等级的统治秩序。但是,在这之前,凯德作为他灵魂的一部分,必须给亨利六世造成足够多的麻烦,现在他死了,麻烦结束了,可是,更大的叛乱或者新秩序的建立就要开始。不过,《亨利六世》下篇第1幕,约克便在平原战死。这或许意味着,约克虽比凯德力量强大,但凯德缺乏理性指引而来的无力,正是约克灵魂无力的前兆,凯德的死亡已经预示了约克的结局。这一点在他们临终场景的类似中可见一斑。他们都如同被囚困的野兽,无处可逃,都在一番羞辱之后,被利剑所杀,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一直都认为,假如还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他们便不会遭受这样的命运(中篇,4.10.74;下篇,1.4.24)。二者对强力的迷信如出一辙。
实际上,凯德(或者约克)这个多头怪兽只是一个更大的多头怪兽的一小部分。前面说过,当时的政治情形是,所有人都只关注一己私利。具有政治决断权力的治国者,却每个人都伸出自己的头,整个英国就是这样一只多头怪兽,约克即是其中一头。按照城邦与人类灵魂的对应,那么,在英国的灵魂中,理性只能是欲望和血气支配下的算计罢了,这就叫做阴谋,这是3部《亨利六世》中连绵不断的一个主题,尤以《亨利六世》中篇为甚。
所以,我们会说,在历史剧(和某些历史事实)的面具之下,隐藏更深的是莎士比亚对人类灵魂的洞悉。就如布鲁姆所说:
莎士比亚试图整体地描写人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每一个可以独立了解所有戏剧的人,也就能看清所有可以选择的重要生活方式带来的后果,并且完全了解各类美好灵魂的特征。①布鲁姆:《政治哲学与诗》,载张辉编:《巨人与侏儒》(增订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参 John E.Alvis等编《政治思想家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s Political Thinker),ISIBooks,2000,p.40以下。
只有知道灵魂的各种可能,才能了解美好的灵魂。前文已以凯德为例,说明莎士比亚对灵魂的洞察。现在,转向莎士比亚描绘凯德的具体戏剧形式。凯德的每一次出场几乎都伴随嬉笑。观众一定觉得这个多头怪兽可笑而不可怕。在整部《亨利六世》中篇里,有这样笑料特征的角色,多是下层民众,无论是作为群体的民众,还是单个的民众:奇迹制造者、决斗的师徒、跟随凯德的工人。但是,他们产生的笑料都不及凯德。莎士比亚为什么要以喜剧的方式展现灵魂中的混乱和欲望?其实,还有什么比混乱更能表现混乱呢?《亨利六世》中篇第4幕共有10场,是3部《亨利六世》中场次最多的一幕,而且其中地点变化频仍,本身就给人一种混乱不堪的印象。
从阿里斯托芬开始,喜剧中的笑料(甚至粗俗的笑料)就一直要营造一种荒诞不经的戏剧效果,质言之,就是一种戏剧假相的破坏。凯德在剧中正式亮相的时候,他的每一句慷慨陈词,都对应一句瓦解破坏的台词(4.2.31以下)。他对自己父亲、母亲、妻子和他本人特征的描述,全部遭到了拆解,但是,更滑稽的是,瓦解后的形象才是真相,这更增加了其中的喜剧效果。凯德不但是受害人,他同样也会拆解戏剧假相。
《亨利六世》上篇有几个庄严的封爵仪式(比如,4.4对塔尔伯特的封爵),但第一个受爵仪式是约克重新成为“高贵的约克公爵”。他当时的誓言是:我一定要铲除对陛下的一切冒犯(3.1.175-6)。这是一个十足反讽的誓言。《亨利六世》中篇的第一个受爵仪式则将这个反讽推向戏谑的拆解:凯德把自己策封为爵士。我们无法想像,他下跪时面对剧场的哪个方向。除了凯德与约克灵魂上的对应之外,这是凯德为约克而瓦解亨利六世统治秩序的开始。接着瓦解的是法律、衣着,甚至饮食。这就是说,凯德在成为别人笑料的同时,也使日常生活成为笑料,使更高贵的人成为笑料。戏剧反应了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也如同戏剧。凯德嘲弄的戏剧形象,不仅仅是《亨利六世》中的统治秩序,对于观看戏剧(包括阅读剧本)的人来说,他们所处的政治秩序同样可能遭到凯德的拆解。
在这些滑稽的混乱景象背后,却是莎士比亚严肃的思考①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第二讲》,徐卫翔译,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第8辑《苏格拉底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0页。,它促使有思考能力的人思考政治生活中的混乱。莎士比亚并不因为使用这些笑料而浅薄,相反,他从形式入手,在最直接的层面上让观众感受政治混乱的荒唐。加上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莎士比亚清楚地知道,混乱的根本是灵魂的混乱。作为多头怪兽的凯德,是约克灵魂中混乱的欲望,是约克缺乏审慎和理性的戏剧再现;作为多头怪兽的英国,缺乏最高贵的灵魂,理性地思考城邦的政治生存。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处理的根本问题是政治秩序,《亨利六世》3部剧中的政治秩序逐渐走向混乱②Tillyard,Shakespear's History Plays(《莎士比亚的历史剧》),PenguinBooks,1944,p.156以下;同时参 Joseph Candido,“GettingLoose in the HenryV I Plays”,Shakespeare Quarterly,Vol.35,No.4,(W inter,1984),pp.392-406.,但是,这不是说莎士比亚在追求一种混乱,恰恰相反,正是基于对人的灵魂和政治生活的理解,他才能够剖析混乱的本质。古典政治哲学对政制的理解基于对人类灵魂的理解。在人有几种类型的金属神话(《王制》,415a-c)里,苏格拉底以4种金属比喻人的种类:黄金、白银、青铜和铁。铜和铁是“废铜烂铁”,比喻一般民众,白银比喻城邦的护卫者,黄金则比喻高贵的统治者。苏格拉底的分类前提是:人的灵魂中究竟含有哪种金属。后来,讨论著名的政体退落和与之对应的人时,苏格拉底重提这一比喻,并特意加上一句,我们之前也说过(《王制》,546e),仿佛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最和谐的政治秩序。在《亨利六世》中,最高贵的人,拥有黄金一般灵魂的人,并不存在。即便是有着良好政治秩序的《亨利五世》,至多只有白银这种类型的灵魂(培福公爵等),《亨利六世》上篇中,亨利五世的秩序依然残存,也残存这种类型的灵魂(塔尔伯特、培福等,但他们一一战死),随后两部《亨利六世》中,几乎全部是“废铜烂铁”。这其中的堕落或许表明,莎士比亚很清楚,并不存在完美的政制,政治秩序并不是高尚灵魂治下的城邦生活,但是,他以凯德的混乱喜剧表明,绝不能因为这个缘故,而放弃对政治秩序的追求。苏格拉底以政制对应人的灵魂。所以,凯德的喜剧一方面牵涉政治秩序问题,凯德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是“废铜烂铁”对政治秩序的颠覆;另一方面是对人类灵魂的反思:人应该如何养育自己的灵魂。“莎士比亚是有教育意图的”③布鲁姆:《政治哲学与诗》,载张辉编:《巨人与侏儒》(增订版)。,而教育必然是针对灵魂的教育。
莎士比亚对凯德的喜剧描绘,并不仅仅是这些滑稽混乱的场景,还有一个最外表也最本质的层面:凯德之名。凯德究竟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身份,或许观众一目了然(就像他们自己以为的那样),但是作为剧中人的凯德,却生活在一种虚妄的自我认知之中。这种虚妄来自约克,是他让杰克·凯德成为约翰·摩提默。摩提默这个姓氏同样来自约克,这是他舅父的家族之名(《亨利六世》上篇,2.5),当然这也是豪尔记载的历史(Hall,《编年史》,第220页④Henry V I2,Andrew S.Cairncross编 ,附录1,London:Methuen,1969,pp.168-169.),但莎士比亚更细腻的处理在于,凯德对这一伪名的高度认可——这正是他是约克灵魂一部分的根本所在。莎士比亚的处理异常巧妙。第4幕一共10场,凯德只有3场没有上场,在其余大多数的上场中,剧本上都写着“凯德上场”,但是在第6、7场,莎士比亚写道:“杰克·凯德上场。”我们先看这两场的剧情。第6场,凯德第一个说话,第一句话就是:“如今,我摩提默已手握京城。”这是攻入伦敦的时候,凯德开始迈向人生的最高峰。突然,一个士兵飞奔而来,高呼:“杰克·凯德!杰克·凯德!”曾经是杰克·凯德的摩提默非常生气,因为一个普通的士兵竟然抖露了他的真名,这与他的自我认知不符,于是他说:“干掉他。”这当然是莎士比亚虚构的场景,所以更能清晰地体现莎士比亚的意图。在这个场景中,凯德忘记了自己是谁。第7场可以称之为凯德的立法。他到达了政治人生的顶点,于是开始最肆意的行为:立法。他的立法其实很简单,他,摩提默爵爷就是法律,当然他也规定了一些细节,比如如何着衣、如何处理政务、报复贵族等等。他的用意在于,从此以后,他是惟一的贵族,其他所有人都是臣民。换言之,他以为自己是上帝。但是,在他人生巅峰的登场剧本中,莎士比亚冰冷地写道:杰克·凯德上场。舞台上的这个人,无论取得了怎样的辉煌(假如那是辉煌的话),他仍然是杰克·凯德。这其中巨大的裂隙是凯德喜剧背后的智慧。凯德是约克的一部分灵魂,约克同样一直以为自己拥有最合法的王位继承权。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是否认为,凯德对自我认知的裂隙比约克更大,但他无疑清楚地表明,《亨利六世》中的政治生活缺乏理性。戏剧是一种政治和教育,莎士比亚要让观众体会到这种缺乏,最富戏剧特征的方式无疑最能夸张地(喜剧性地)表达这种缺乏。
不过,《亨利六世》中篇既非喜剧,也非悲剧,而是以政治生活为主题的戏剧,这恰是因为,悲剧和喜剧在一起才能展现人类生活的全部。在《王制》394b-c中,当阿得曼图斯简单地将戏剧等同于悲剧的时候,苏格拉底悄悄地纠正了他的错误,把喜剧也属于戏剧的主张巧妙地归于阿得曼图斯。所以,只能说莎士比亚对凯德的处理是一种政治喜剧,而不能说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是一种政治喜剧。政治喜剧的意思是说,喜剧是起点,悲剧是核心,必须从悲剧的层面领悟喜剧①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第二讲》,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第8辑《苏格拉底问题》,第18页。。通过凯德的临终一幕,我们可以有所理解。这是第4幕最后一场,凯德躲避在伊登的花园,忍受了 5天的饥饿之后,被伊登发现。随后,他以类似于决斗的行为终绝了自己的一生。喜剧最终的结局是悲剧。凯德经过虚妄的自我认识之后,终于重提自己的名字“凯德”,并且特别提到自己的灵魂。这是他对自己的真实认知吗?他的临终台词是:
伊登,再见了;为你的胜利骄傲吧。请代我转告
肯特郡的人们,她最优秀的男子离去了,请代我恳求
全世界的人们,都去做懦夫吧;而我,一个无所
畏惧的人,只是被饥饿征服,而非勇力。(行71-74)
这或许是一段令人动容的告白,他最终舍弃摩提默之名,而重新认识自己为凯德,不再以为自己是爵爷,而只是一位男子,就此而言,他似乎回归了自己最初的凡俗身份。但是,凯德仍然不明白,他所谓的勇敢这种血气,倘若没有理性的参与,终究会沦为混乱的欲望。而且,即便死亡来临,他还是要以另外一种身份自我虚设:“肯特郡最优秀的男子。”他在剧中的所为表明,他非但不是最优秀的男子,甚至连优秀都算不上。这时,死亡的悲剧也无法消解凯德在戏剧中的喜剧色彩——但是,从根本上,这恰恰是一种政治和灵魂的悲剧。在凯德最后的死亡之中,悲剧和喜剧互相交织,惟其如此,我们才会理解灵魂混乱的悲剧和喜剧,理解人类政治生活的悲剧和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