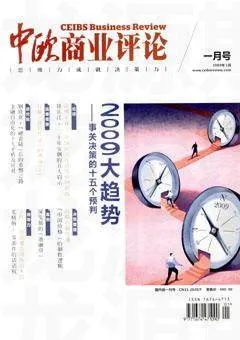金融自由化的十大矛盾及应对
2009-12-29刘胜军
中欧商业评论 2009年1期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深远,标志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急刹车,并警示我们反思金融自由化所揭示的一系列矛盾。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为特征的牙买加体系时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de-regulation)浪潮,催生了金融衍生产品、私募股权(PE)和抵押贷款的蓬勃发展,这一趋势延续到最近的次贷危机。从大历史的视角看,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深远,标志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急刹车,并警示我们反思金融自由化所揭示的一系列矛盾。
风险与效率的矛盾
放松管制加剧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金融创新产品的不断涌现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为企业融资、风险规避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另一方面,竞争压力迫使金融机构借助高杠杆来提升利润。80年代以后,银行为降低利率风险,把住宅抵押贷款打包在二级市场出售,特別是在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推动下,证券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5年指出:“过去很多贷款申请人被拒之门外,如今金融机构能非常有效地判断每个申请人的风险,并对风险做出合适的定价。”繁荣的市场掩盖了巨大的风险,然而风险是不能被消除的。金融创新只不过是将风险转嫁而已,所有人仍然被拴在同一个链条之上。一旦脆弱的环节崩溃,所有参与者都被拖下了水。
显然,监管者必须摈弃过去那种唯创新论的观念,严密关注金融创新所伴随的风险:普通投资者更应远离那些看不懂的结构性产品,牢记“买者自负”的谨慎投资原则,不要盲目相信信用评级机构,要做好投资前的调研工作(duediligence),搞清楚信用评级机构所采用的评级方法及其风险提示。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
与金融市场的突飞猛进相比,美国的监管理念仍然停留在80年代。美联储长期奉行自由市场主义,坚持“金融机构的自我利益确保它们可以最好地保护股东利益”(格林斯潘语),变成了金融创新的旁观者。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监管股票市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负责监管期货与期权市场,但属于场外交易的互換(Swap)市场实质上却没有任何监管。长期以来,监管者认为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支柱,而忽视了对投资银行的监管,正是后者率先把市场捅了个大洞。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认为,金融创新本身就意味着对现有体系的某种突破,而监管必然是滞后的,他甚至建议要成立类似于“全国交通安全委员会”的机构,来全面检讨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默顿认为,指责金融工程师是没有道理的,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是金融机构管理层、董事会和监管当局。
金融创新仍将不可阻遏,唯一能做的就是监管当局要学会与时俱进。其中,监管部门的专业能力持续改进非常重要。一个可取的建议是不断吸取金融从业人员进入监管部门,确保监管者对复杂的创新产品能保持鉴别力,此外,金融监管应不留死角,CDS(Credit DefaultSwap,信用违约互换,也叫贷款违约保险)等大规模的场外交易产品应建立集中清算机构,以提高透明度。商业银行之外的金融市场参与者也应受到与其系统风险相对应的监管约束。
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
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建立了“防火墙”。长期以来,商业银行受到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规制,根据巴塞尔协议要求,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但是投资银行却成了监管真空。与商业银行相比,投资银行没有存款资金来源,也不能享受美联储的贴现窗口,只能借助于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来提高杠杆率。商业银行杠杆率通常在1:10左右,而投资银行却高达1:30,2002年至2003年,美国投资银行自营交易业务占总盈利30%左右,但到2006年该比例升至70%。1999年11月,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又称Gramm-Leach-Bliley法),允许并提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联合经营,分业经营的界限开始淡化。次贷危机爆发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迫于生存压力转型为商业银行,宣告了美国独立投资银行业的终结,标志着金融混业经营的彻底回归。
但是如何防范银行业和证券业之间的潛在利益冲突,将成为美国金融监管的一大挑战。首先,应改变多头监管的局面。目前美国的存款机构同时接受五大机构的监管(货币监理署、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储蓄监管办公室、全国信贷联盟管理局),各个监管机构之间难免出现责任不清或者交叉。其次,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美联储等不同领域的监管机构必须进行有效的整合,以适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挑战。
救或不救的两难
在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的倒闭在所难免。监管当局一方面要避免过度救助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美联储在30年代初未能防止大批银行倒闭是加刚大萧条的重要因素,甚至在弗里德曼90岁生日时他还致辞说:“关于大萧条,您是对的;美联储做错了,很抱歉;伹是由于您的提醒,美联储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美联储1998年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危机的干预是个转折点。投资者认为,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情况,美联储还会同样应对。但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莫斯(David Moss)称,救助计划可能扭曲激励,被救助的人将来会冒更大的风险。
尽管政府救助金融机构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隐患,但“不救”的政治风险远远大于“救”:“不救”将在短期内导致市场动荡、加剧金融危机;“救”虽然会加大道德风险,但其成本是分摊在漫长的未来。正是因为金融机构倒闭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大而不倒”仍将是金融界的法则。监管当局能做的只有加强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
管理层与股东和监管者的博弈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指出,华尔街精英总是倾向于强调事情好的一面,在华尔街做一头大熊是难以谋生的。一个潛规则是:如果大家都错了,都没问题;如果別人对了你错了,你就是愚蠢的家伙;如果大家都错了,你对了,那是你运气好。因此,金融机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就不难理解了。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管理层可以从冒险中获得巨额的报酬,却不必为投机失败负责。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都批评金融机构高管没有为企业遭受的巨大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董事会成为公司治理架构中的关键一环。但董事会在防止金融机构过度冒险、为CEO确定合理报酬方面显然辜负了信托责任。动辄数千亿美元信用工具交易、复杂的风险管理模型,再加上管理层选择性提供信息,董事会只能一边倒地接受管理层的风险评估。
金融机构的冒险倾向也受到监管者的无意纵容。金融机构不仅是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而且是过于纠葛而不倒(toointerconnected t0 fail)。例如,贝尔斯登在CDS业务中有5000多个交易对手是金融机构,如果违约,连锁反应可想而知。对此心知肚明的金融机构高管们为了自利而不断做大企业规模,最终挟持了公众利益。
如何确保管理层行为符合股东的长期利益,并防止管理层过度冒险的倾向,应成为薪酬体制改革的未来方向。可以考虑的措施包括:以管理层持股取代股票期权;对管理层的奖金延迟支付;在业绩好时奖励管理层,在管理层过失导致亏损时回的过去的奖金。当然,要扭转过高薪酬的行规并非易事,需要投资者、监管当局、行业自律组织、国际组织协调行动。
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
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促使了表外业务(即不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但会影响损益表的业务)的急剧增加。在安然事件中,安然公司成立了3000多家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特殊目的机构/公司),隐瞒了数十亿美元债务。美国次贷危机表明,这种方式仍然被金融机构用来隐瞒风险和债务。2001年,次级贷款只占到住宅融资的2%,而到2005年飙升至20%。银行并末把次级贷款放到资产负债表中,而是将其打包成CDO(CollateraoizedDebt Obligations,担保债务凭证)出售。
由于表内和表外业务风险换算系数的差异,1988年巴塞尔协议鼓励银行设法把高风险业务转移到表外。针对这一问题,巴塞尔协议II要求银行采用复杂的资产组合模型来评估其资产池的风险。但是由于金融机构在风险评估时使用的是公司的内部模型,风险仍然会被低估。巴塞尔协议II确立了三大支柱:确保最低资本要求与银行承担的风险相匹配、强化监管机构对银行的监督、更充分的市场信息披露。尽管巴塞尔协议II远非完美,但它比巴塞尔协议能更好地应对表外业务和复杂的衍生产品之挑战,应积极推动巴塞尔协议II的普遍实施。
另类金融机构要不要监管
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对冲基金(hedge fund)在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86年美国有215家对冲基金,目前已经发展到8000多家,资产规模达1.9万亿美元。尽管这些机构拥有击溃英格兰银行、东南亚各国政府的惊人力量,却始终游离在监管范围之外。LTCM的杠杆率长期保持在30倍左右, 1995年底LTCM参与的金融衍生工具规模达到6500亿美元。1998年底LTCM瀕临倒闭,美联储決定出手拯救。《时代》周刊批评说:美联储向一家私营的、根本就不受美联储监管的对冲基金伸出援手,是很不严肃的一件事。负责调查LTCM危机的“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报告认为:LTCM事件所提出的一个最主要政策问题是,如何才能对过度利用财务杠杆进行有效的限制。
遗憾的是,LTCM危机过后,美联储并末采取措施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2006年5月,格林斯潘再次否定了加强对对冲基金监管的提议,认为那样只会扼杀创新,2007年2月,美国财长保尔森领衔的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仍然认为,不需要对对冲基金等机构进行特别的监管,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高杠杆率再次成为了众多金融机构的杀手。
将来,对冲基金监管可以从提高单个投资者门槛(目前为100万美元)、要求适度的披露以增强透明度等角度人手。
争议公允价值法
1993年由FASB(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推出的公允价值法,(fair value accounting)由于按照市场价值来评估资产,因此存在强烈的“亲周期效应”。出现危机吋,金融机构被迫进行资产减计,而资产减计又迫使其他参与者降低资产估值,诱发抢在资产价格下降更多之前恐慌性拋售,最终形成资产价格螺旋式下降。不过公允价值法并非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如北美保险业联合会(GNAIE)执行总监道格拉斯·巴内特(DouglasBarnert)所说:人们怪罪于会计准則,就像是把温度太低归罪于温度计。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对公允价值法的巨大压力,FASB是否会进行修改值得关注。在公允价值法中,资产定价往往参照交易活跃的产品或市场,而低估了一些资产隐含的流动性缺陷。金融机构对某类资产的集中持有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一旦出现恐慌情绪,被集中持有的资产很可能因流动性枯竭而价格暴跌。
金融稳定论坛(FSF)提出,金融资产的定价应朝以下方向进行改革:对复杂的和流动性偏弱的资产,建立严格的专家评估和动态审查;对定价模型和定价过程建立严格的治理和控制机制;提高对定价方法、定价过程及潜在不确定性的信息披露。
爱恨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机构是“贷款并证券化”(originate-to distribute)链条的核心角色。根据巴塞尔协议II,真评级资产比未评级资产的资本要求要低,评级机构成了判断资产风险的裁判。哈佛大学教授尼古拉斯·雷特西纳斯(NicolasRetsinas)认为,对次级贷款的监管实际上被外包和私有化了,但不幸的是,三大评级机构(S&P,标准普尔;Moody’s,穆迪:Fitch、惠誉)根本没有能力识别复杂的参与者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和安然事件中的会计师事务所一样,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中也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因为发行证券的金融机构既是评级机构的收入来源又是其需要监督的对象。
美国国会2006年通过了《信用机构改革法案》(Credit AgencyReform Act of 2006),试图降低信用评级行业的进入壁垒,通过强化竞争来弱化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但是,其效果并不明显,该行业仍将继续处于三大公司寡头垄断的格局。
要想确保信用评级机构真的可信,需要下重药。例如,可以考虑规定信用评级机构不得同时从事咨询业务和评级业务,以消除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信用评级机构一旦被查出问题,监管当局必须予以重罚,甚至吊销执照。此外,也应考虑建立专门的国际机构,负责制定标准并检查评级机构的内部流程是否符合标准。
金融政策要不要关注资产价格
1999年互联网泡沫越酿越大之时,伯南克曾参加了一次有关货币政策是否应考虑资产泡沫问题的大讨论。伯南克认为,美联储只应盯住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不应进入美联储的决策视野。伹如果泡沫破裂,美联储应该降息末缓解其对经济的冲击。并未发言的格林斯潘会后走过来对伯南克的观点表示了赞赏。显然,格林斯潘从伯南克的发言中获得了理论支持。
格林斯潘长期把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被指责是导致次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尤其是在2003年减税之后仍然末及时加息是一大错误。继任者伯南克也对“末日博士”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Roubini)和斯蒂格利茨等学者关于房地产泡沫的警告充耳不闻。
鉴于金融市场的庞大规模及其对实体经济日益增强的影响,中央银行把资产价格纳入决策变量已获得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美国最近两次危机的经历证明:央行希望只盯住物价水平是不切实际的。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联储不断降息最终酿出了次贷危机;现在美联储为应付次贷危机又大肆往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也许正在为下一次泡沫埋下祸根。如果美联储对资产价格泡沫事前进行适当遏制,或许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会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