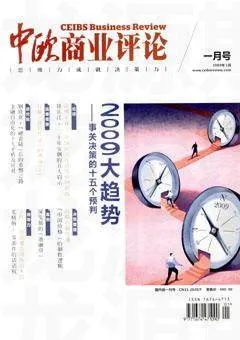打破“波特悖论”的鸿海(上)
2009-12-29郝亚洲
中欧商业评论 2009年1期
波特认为:企业若想实现“客户溢价”,或者在成本战略上做到低开,或者在差异化战略上做到高走,而“夹在中间”的企业将没有利润可图。但是郭台铭的鸿海却打破了这一战略学上的经典论断——不但成为出并伸之和乔布斯等企业家对电子产品高设计标准的梦想载体,还打破了制造企业只能徘徊在全球价值链末端的定论。
PS3、iPhone、Dell电脑、HP笔记本、Nokia音乐手机,你想到了什么?对,这些都是数字化生活的标准元素。它们表征了时代,也代表了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但是,如果说这些产品都是由一家制造商制造出来的,你会相信吗?事实上,鸿海正是这样的企业,它生产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想象得到的大部分品牌的数字产品。
20世纪后期,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发现很多企业在疯狂扩张、广泛进行产业布局的同时,忘记了一项最根本的任务——什么才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大部分企业的领导者都被这样一种假象所迷惑:自己企业的利润率是和产业的整体利润水平成正比的。比如,当互联网成为了一个用鼠标点击美元的产业时,大家都会拼命挤进去;当加工制造业随着产业内竞争对手的互相压价无利可图时,就会发现哀鸿遍野。于是,波特在自己赖以成名的竞争力模型的基础上,开始追本溯源,将企业的管理问题放回到了原点:探寻组织的竞争优势。
本文试图在波特竞争力模型的基础上,再次探讨鸿海的成长路径:企业的利润所得固然与产业整体的利润水平相关,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将“竞争优势”中看似悖论的两大特征融会贯通的话,取得利润的主动权就会掌握在自己手中。
“夹在中间”的悖论
翻开鸿海的执行力地图,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一幅蜘蛛形状的世界地图。核心是处于中国台湾的鸿海总部,其触角伸向了东南亚、澳洲、东欧、北欧、北美洲及南美洲。这里面有研发中心、采购基地、即时库存和制造基地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鸿海是一个办公室在台湾,执行部门在世界各地的全球化机构。
有人总结过鸿海这种全球化办公平台的办事效率:美国的研发中心下班后,可以将设计交接给开始上班的中国台湾或大陆的设计工程师,以接力的方式继续完成设计。鸿海具备了全球24小时的远程互动设计能力,每一个小时都在研发。亚洲和美国的工程师可以在24小时之内合作开发出令乔布斯这样的美学魔鬼都满意的产品。于是,鸿海有了“日不落帝国”的美誉。
这种看似简单的无时差运营状况,正是对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诠释。因为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打破其理论表述中没有得到解答的“悖论”:竞争优势归根到底来源于企业为客户创造的超过其成本的价值,在目前的产业环境下,企业如果想要实现这种溢价,要么在成本战略上做到低开,要么在差异化战略上做到高走,伹波特认为,差异化本身通常成本高昂,而已经建立起成本优势的企业如果进行差异化服务的话,将会损失掉已有声誉,最终在产业格局中被“夹在中间”,没有利润可图。譬如,曾经的“标王”秦池酒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
我们再将目光聚焦到鸿海的身上,会发现另一种情况。鸿海利用了自己深厚的模块制造能力和中国大陆的区位特色,打造出了全面低成本的竞争力(overall-cost-leadership)。这也成就了这家企业在一段时期内的高速成长。但是,低成本并不是鸿海所独有的。
而正如台湾作家张殿文所说:“如果鸿海只是一个会节省成本的公司,或是一个把成本隐藏在上百个子公司里的集团,它的成长规模将面临经济学的严酷考验。”的确,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当规模经济发展到足够大的时候,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将会高于市场交易成本,这个时候,就是利用规模经济追求低成本策略的大限了。
目前,郭台铭为我们展示出来的鸿海的竞争优势表现为全球无缝隙合作的CMMS(ComponentsModule Move Services,组件、模组、行动及服务)模式——以代工起家以后,全力提高研发的能力,特别是提高设计层面的竞争力,用组装扩大经济规模,再用零组件获利,使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让人无法取代的地位。随着电子制造产业不断橫向扩张,鸿海及时跟随产业潮流进入到电子、系统组装和通讯网路产品的代工模式,业务范围不断横向扩展,进入整机生产、光通信及手机代工领域。并在橫向整合过程中,自创了机电整合组件的CMMS运营模式。
鸿海利用自己模块化和组件化生产的优势,实现了低成本战略,然后,再利用这样的优势去和客户博弈,即可以主动为客户发现提高产业差异化和降低研发成本的方法,从而为自己赢得订单。就在他们和客户如此亲密接触的时候,鸿海自身追求的差异化战略也就得到了实现,因为为客户解决了个性化问题就意味着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加工制造业产生了极大的差异性。
差异化之道
台湾大学的李吉仁教授在谈到台湾制造业时曾说:“在技术更迭快速、竞争激烈的电子资讯产业环境中,厂商规模的扩张应来自于专业技能的提升与创造新的分工结构,而非在现有分工架构下不断追求最佳化。”对于鸿海来讲就是如何透过策略创新的逻辑,建立新的价值定位,从而寻找支撑其长期成长的落脚点。
事实上,郭台铭在创办鸿海之初就意识到,台湾狭小的岛内面积加之厮杀惨烈的产品价格,决定了企业必须要通过独特的产品战略参与全球竞争,作为生产电子类产品的企业,简单的低成本是不足以建立起波特所说的“持久性优势”的。首先,电子类产品对电子配件的质量要求极高;其次,随着消费越来越个性化,品牌商也需要给大众不断的惊喜,而这些惊喜常常取决于上游供应商的表现。比如,你是否能够如乔布斯所愿,打造出一个半透明的且底部密布针孔通风口的机壳?这些就成为了企业必须努力寻求差异化的潜在动力。
鸿海的差异化战略始于1991年。主动寻求差异化既是主观上的愿景,也是客观要求。上市以后,鸿海的核心产品——电子连接器已经为其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并帮助鸿海成为了台湾第一大电子制造商宏碁的重要供应商。
在参与全球竞争的时候,面对技术和客户群已经稳定的日本厂家,鸿海除了建立在成本优势之上的价格弹性之外,其区别于竞争对手的能力在于“开发迅速”,为了达到迅速响应的目的,鸿海把连接器的研发中心直接设到汇聚了大部分美国电子工厂的Cypress,从而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了解到客户需求,并不断调整自己的研发战略,电路板连接器、回路模组连接器,系统对线缆组培连接器以及后来的IC卡连接器都是在这种迅速研发模式下的产物。
1991年,基于对连接器模具品质的自信,郭台铭宣布要进行一个日后让全球制造业叹为观止的计划——垂直整合。垂直整合是一种用规模经济实现成本优势和提供差异化服务有机结合的最好途径,这样一来,客户就会变成企业的竞争对手,而企业对手有可能会成为商业盟友,
在台湾,制造连接器的公司规模都不是很大,200多家制造商里,大部分资本额只有5000万元新台币(合人民币约1035.73万元),工厂规模不过50人。唯独鸿海拥有1000多人,资产额上亿元新台币,具备了向产业链上游整合的实力。而向上整合的目的就是要让鸿海建立属于自己的模具开发能力。郭台铭认为,如果想占据更大的市场,就不能在模具工艺上受制于人。当可以自己制造模具的时候,鸿海马上开始了对模具工艺的颠覆——切割模具的制造流程,以分工的方式来完成,这样,一块模具在经过了这些流程之后可能会衍生出几种不同的模具。
有了强大而且自主的模具研发能力,鸿海随即开始进行横向整合,即向机壳业务领域拓展。1994年,鸿海完成了Apple提出的在iMac半透明的机壳上打出上百个直径不到14厘米的散熱孔的要求,一举击败了LG,成功拿到了乔布斯的订单。1999年,鸿海又成为了当时世界第一大电脑品牌商康柏的机壳供货商。至此,鸿海的垂直整合战略顺利起步。
1996年,郭台铭宣布进军“准系统”,也就是向下游整合的战略,对于品牌商和整个产业界来说,这恐怕是鸿海带给他们的最大差异了。以前,电脑整机的品牌商面对的是宏碁和大众电脑这样的大厂,鸿海不过是向这些大厂提供某些零部件而已。“准系统”的思路是鸿海先将电脑零组件进行一定程度的组装,然后再将系统转给宏碁这样的大厂,这样,企业就不再是以往的零件供应商的角色了,而是对整个产业链具有了话语权。
从连接器制造开始,鸿海不断将差异化思路滲透其中。在成本优势的帮助下,企业具备了资本和技术,开始了分别向上、向下以及橫向的产业整合的差异化道路。这也正是波特所说的差异化往往是从单个产品开始,然后向整个产业链条蔓延的战略思路。
鸿海用成本立家,差异制胜,最后打造出了低成本、高差异化的CMMS运营模式,这既是时代的限制所为,也是制造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从更广泛的商业意义来讲,鸿海战略告诉那些为“利润从哪里来”所愁的企业,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哪里,虽然时代在变迁、外在科技在发展、行业之间的区隔越来越多,但是成本优势和差异化是寻找竞争优势的两条轴线,在这个坐标系中寻找到符合自己经营特色的混合战略,才是企业管理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