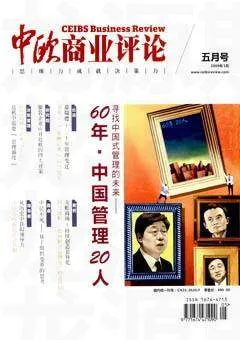错季的花朵
2009-12-29支维墉
中欧商业评论 2009年5期
培育企业家精神的花朵,既需要企业家内在人格的种子,也需要外部制度和文化条件的滋养。中国的企业家精神随着近30年经济的迅猛发展而蓬勃生长,但由于文化与制度尚未达到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它就像“错季”盛开的花朵那样,看似娇艳,实则脆弱。
在一个气候异常的深秋,植物园里的桃树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植物学家说,桃花的“错季”开放缘于全球变暖的气候——原本,这样的美丽应该在4个月之后的春天绽放。植物的早熟是为了应对环境改变而表现出的一种适应性。然而如果这种现象长期持续,某些物种将因无法适应环境的改变而消失。
从物种回到商业,我们要谈论的是中国企业家精神。自从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第一次将企业家才能与土地、资本和劳动一起视为四大基本生产要素之后,“企业家”的概念由此生发。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第一次明确界定了企业家的职能和作用。他将企业家评价为工业社会的英雄,因为他们具有创新精神,“是实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人”。在熊彼得的定义下,“企业家精神”的轮廓渐次清晰,包括首创精神、成功欲望、冒险精神、精明和敏锐以及事业心。
可见,“企业家精神”的概念起源于西方。我们的疑问是,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缘起何处,去向何方?沿着熊彼得定义的“企业家精神”框架,我们试图对比东西方企业家精神的异同,寻找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特质。分析后我们却倏然发现,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如同错季盛开的桃花,有着渴望生长的蓬勃力量,却还没有迎来最适合它开花的季节。
创新的繁和简
熊彼特定义的“创新”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供应的新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企业家不乏创新精神。1980年代,杉杉西服的领头人郑永刚尝试把西服卖给潮流意识渐渐苏醒的中国人,可被视为“引入新产品”;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推出保健型饮料健力宝,风靡十年,可被视为“开辟新市场”;红塔集团原总裁褚时健绕开僵化的国有体制,在田间乡陌向烟草种植者直接收购烟叶,可被视为“控制原材料供应的新来源”;格力总裁董明珠首创自建渠道模式,可被视为“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但熊彼特推崇的“破坏性创新”在中国的土壤中却较为鲜见。1994年柳传志与倪光南那场关于“贸工技”还是“技工贸”的争执至今还在被企业史的研究者们反复提起。在柳氏主导下,联想最终选择了“贸工技”的战略方向。在百度、比亚迪、海尔等中国卓越企业身上,我们都不难看到“模仿式创新”的痕迹。比亚迪的总裁王传福坦白地说,比亚迪的新产品开发有60%来自公开文献,30%来自现成样品,自身的研究实际上只有5%左右。对于许多中国企业家而言,“技术恐惧症”依然是前路上的一大障碍。
更意味深长的是,中国企业家将相当多的“创新智慧”投入到与制度的博弈中——起步阶段没有合法身份,于是有了“红帽子”的创新;苦心经营多年却无法明晰产权利益,于是有了暗渡陈仓的MBO……这样的“创新”是贡献还是消耗?华晨的仰融与伊利的郑俊怀让人扼腕的“落马”便是答案。成功欲望的原点和归宿
关于企业家的成功欲望,熊彼得认为,这群人“存在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成功本身”。从这一意义看,利润和金钱是次要的考虑。而“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受到重视”。正因为ZJTw3fbtsZuNpCLFY27sLA==如此,企业家经常“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
熊彼特描绘的“成功欲望”是人类的共性,无须以地域论之。但如果从宗教、社会、文化的层面解读企业家追求卓越的原动力,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下的中国企业家和基督教伦理滋养下的西方企业家仍有着明显不同的“原动力”。
在中国历史上,企业家愿景始终与“大国崛起”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从洋务运动中的“状元资本家”张謇、“张裕之父”张弼士,到更近一些的“造船大王”卢作孚、“火柴大王”刘鸿生,再到“红色资本家”荣毅仁,近代史上,无数中国企业家毕生的梦想就是重现强国气象。在新一代企业家如柳传志、任正非、倪润峰等人的心中,“产业报国”诉求也甚为浓重。张瑞敏曾说:“和跨国资本较量,就算死,海尔也要死到最后一个。”但随着“世界变平”,民族产业梦想会变得界限模糊。柳传志在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谈到:“等中国企业真的做到全球布局,形成品牌市场的时候,再提产业报国就不合适了。联想集团必须是国际化的公司,你不能叫美国CEO产业报国报给中国。”
西方企业家成功欲望的归宿,则更多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比尔·盖茨功成身退后将毕生赚取的财富“裸捐”,是因为作为基督信徒,他相信仅仅追求财富会阻碍灵魂的救赎;在许多西方企业家的心中,自己拥有的所有财产都是上帝委托他们管理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将这些财富交还给上帝。
冒险精神的得和失
财经作家吴晓波认定中国企业家是一群“工程师加赌徒”。他们往往有较好的专业素养,在某些领域有超人的直觉和运营天赋,同时,他们更有着不可遏制的豪情赌性,敢于在机遇降临的一刻倾命一搏,成者上天堂,败者落地狱,其微妙控制完全取决于天时、地利与人和等因素。
纵观中国企业家的命运跌宕,这种赌徒般的冒险精神在风云突变的气候中显得极度“无常”,甚至被比喻为“走铜丝”。“我只要有三分把握就去做”——黄光裕的这句“名言”在他辉煌时被捧为缔造首富王国的秘诀;在其落马之后,却被引为败走麦城的证据。
为什么中国企业家如此偏好风险?吴晓波认为,“因为他们崛起于一个狂热的商业世纪,这个时代给予身处其中的人们太多的诱惑与想象空间。”这个时代能让企业和个人实现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风险固然很大,但回报可能更大得令人不可想象。
更进一步思考,如果说西方企业家面对的主要是“市场风险”,那么中国企业家的风险维度还多了一重,那就是政策风险。从1978年开始,民营企业家的待遇时而春回大地。忽而又倒春寒,他们于是成为了背负悖论的一群:一方面他们大胆创新敢于冒险,另一方面,不安全感又成为他们的集体潜意识;一方面,他们希望把企业做成永续的王国,另一方面,又对自己所处的产业缺乏信心,很难致力于专业领域的深耕细作,四处打井,赚一笔就走;一方面,他们在营销投入上不惜代价,“人海战术”和“广告轰炸”是常用手段,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太愿意大笔投入研发,因为不确定性也许会在瞬间降临……
精明的锐和钝
企业家哪有不精明的?他们是最长于计算投入和产出的一群人;企业家哪有不敏锐的?他们是最善于发现市场机会然后从中获利的一群人。如果说中国企业家有什么特殊的精明和敏锐,也许就是他们独特的政治智慧。在中国任职近15年的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周伟煜感叹说,外资公司利用政府资源的能力远不及中国的本地公司。他直言不讳地认为:“决定中国某家企业的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获得政府帮助的多少。”
由于中国企业家(特别是资源匮乏的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是政策风险,所以他们本能地与政府靠拢,获得某种名分或者政治庇护。大多数企业家们都挂职当地政协,与本地官员过从甚密。民营企业家南存辉说:“做企业应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政治是天。”然而,“政治敏锐”会渐渐磨损企业家的“市场敏锐”,这几乎是铁律——想想看,当你能够依靠某种政治嗅觉和政商关系赚到“容易钱”的时候,还会那么在意企业的市场嗅觉和客户关系吗?这就是企业家精明中“锐”与“钝”的辩证关系。制度重建:等待“春季”
至此,我们临摹着熊彼特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框架,几乎就要完成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素描。然而却有了几分难下断论的犹豫——在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能看到中国企业家与世界各地企业家的共同之处:他们勇于承担风险、敢于创新、心怀梦想、敏锐而精明。然而他们又是那样的不同:他们将许多“创新智慧”都投入了与制度的博弈;他们将成功欲望与民族崛起的愿景相连;他们的风险意识中绕不开“政策风险”这个关键词;他们的精明和敏锐中,政治智慧尤为鲜明。任何一个层面竟然都离不开“政治”、“政策”和“政府”,无怪乎冯仑感慨说:“民营企业要想寻求长生之道,跨越历史河流,全面把握政商关系乃是当务之急。”
培育企业家精神的花朵,既需要企业家内在人格的种子,也需要外部制度和文化条件的滋养。中国的企业家精神随着近30年经济的迅猛发展而蓬勃生长,但由于文化与制度尚未达到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它就像“错季”的花朵那样,看似娇艳,实则脆弱。南开大学教授任兵对此的评说是:中国的管制、规范和认知层面的制度都具有很大的问题。当前我们的正式制度有漏洞,社会文化层面的规范和认知制度又没建立起来时,企业家精神便开了花。这种错季的“企业家精神”及其引导下的企业家行为体现出了很大的共性:具有严重的私利和机会主义行为导向。为什么中国的乳制品企业会“集体犯罪”?这恰恰说明,在企业家精神外部,我们的制度同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制度不仅包括政策、法律等硬性层面,也包括软性的文化。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是,企业家精神诞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基督教文化是孕育这种精神的温床。中国传统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并不能提供企业家精神发育的土壤。儒家思想虽然可以视之为一种伦理体系和社会功能意义上的宗教,但由于其仅有“外王”的人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因而难以提供企业家精神。这或许有几分极端,而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的见解亦值得反思,他认为,中国企业家不自觉地以传统文化心理的模式来应对全球化的新形势,这将导致惨败。三鹿奶粉也好,红心鸭蛋也好,假烟、假酒也好,都是不自觉地在同一个文化心理模式的牵引下应对现代化的需要。
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更多的是对商业和企业家的排斥和贬损。儒家强调中庸适度、温和而不过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的观念造成了对个人创造性的抑制和从众心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土重迁。商业精神包含积累资本、追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冲动和内驱力,但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本身并不企图通过生产来谋取最大利益,反而常以获取的利润加官晋爵,或是修缮祖坟,买屋置业。皇商、官商从经营方式到观念心态都是封建政权和封建经济的维护者,至于为数众多的小商贩,由于本小利微,在日常的集市贸易中只能成为附庸和补充,无法形成真正的商业精神。
制度与企业家精神的不相容更是绵延千年。《史记·货殖传记》指出,世人追逐富贵利益已久,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教诲他们,又其次是整顿他们,最下等的办法是和他们相争。西汉以后的两千年中,统治者真正用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发展商业经济的几乎没有,最多的政策制度恰恰是“整齐之”和“与之争”。这种政策制度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和上层建筑的“共识”。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反思过“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企业家”这一命题。他认为,政府管理手段依次是宪法一法律一行政命令一政策一领导指示一领导意见。在这个链条上,越往右,管理方式越多变;越往左,管理方式越稳定。但如今,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管理主要依靠“靠右”的手段,导致企业家面临的环境不稳定、难以预测。这是我国没有大企业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为了让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更为健康地、“去政治化”地生长,让中国能够在未来涌现堪与比尔·盖茨、沃顿·山姆比肩的大企业家,关键在于什么?
仍在于制度。丁学良的结论是:要降低政治风险的因素,降低企业家面临的种种“不可控性”,我们只能依赖于一个法律制度的建立。如果中国的法制环境没有改善,当今企业家们的未来绝不会比以前的企业家更好。但如果今后政府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管理、调节方式能够从领导的个人喜好转向稳定的法制方式,而且这种法律不仅仅是很好地写在纸上,而且在实际的司法和执法部门中间也能得到很好的贯彻,那么,即便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只要我们向这个方向迈进一步,中国就会多一批企业家出现,再迈进一步,就会有更多的企业家成功。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如同错季盛开的桃花,有着渴望生长的蓬勃力量,却还没有迎来最适合它开花的季节。培土,施肥,灌溉……是的,我们需要这些。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等待更加适宜的季节,更加恰当的温度和湿度。到那时,中国企业家的精神之花才会如遍野山桃那般蓬勃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