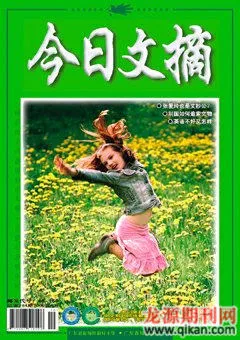乌镇行记
2009-12-29谢若莎
今日文摘 2009年10期
在中国人的性格里,刚毅与温柔,豪迈与温婉,洒脱与多情,大气与细腻,种种看似相反的心性交织,共同架构起了中国人复杂而完整的个性特点。古人的心里往往兼有入世的欲望和抱负以及出世的情怀和愿望,总是一边念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边又吟出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矛盾,勾勒出了千古的犹豫。这份矛盾照亮了历史,完整了历史。正如豪放派与婉约派诗人完善了中国诗的艺术,“大漠孤烟直”和“小桥流水人家”造就了中国独特而多样的风景。
江南,因其静,因其美,因其脱俗,而成为千古文人墨客心中永难割舍的情结。江南的那桥,那水,那人,总是在不经意间寄托了情,荡涤了心,灵魂静了,净了,醉了,难舍了,于是愁了,叹了,憾了,留恋了。在这里,萝卜白菜都沾满了诗,石板青苔皆可入画。江南升华了诗人,诗人诗化了江南;江南陶醉了画家,画家写意了江南,不算报答吧,应该是一种默契,感性的世界里人与物交融的默契。江南又岂是文人墨客的心灵归宿,也许,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江南的情结,在岁月的流逝里,永不停歇地梦着,向往着……
踏上乌镇的青石板,江南对于我就不再是多幅水墨画拼凑的风景,诗词歌赋中流淌的意象,她那样真实地包围着我,那份古朴,那份宁静,诗一样,雾一样,身处其间却仍觉其渺远、朦胧。尽管在人群之中,静静呼吸一口,水乡的气息便自然屏蔽了人间的喧嚣,涤清了人间的烦恼。有的时候,人是需要静的。江南,是个洗心的地方。
乌镇的水诗意盎然,也许因为清代最出色剧作家洪升醉卧在此,点点波纹都流淌着优美的诗句。游客坐在江南小船上,船夫轻轻摇着桨,经过典雅的石桥,经过一间间质朴的小屋,无论镜头对着哪儿都是一幅绝美的图景。我去的时候,乌镇下起了小雨,我有幸目睹了细雨中的江南别样的风韵。走在昏黄的灯光下,轻轻踩着被雨水湿润的青石板,心里自然而然会生起一点淡淡的忧郁,忧郁也是这份景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分。这时,过快的行进速度成了一种浪费,慢慢前进,方能品出这种独特的意境。路边的长排木椅有个好听的名字——美人靠。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撑着油纸伞的江南美女,温柔地斜倚着美人靠,望着远方,静静地坐着。
乌镇的小吃也很有特点。石板路边有很多卖青团的人家。我一路买下来,吃了不少。青团的滋味便如水乡一样,淡淡的,但充满香气。乌镇的青梅和姑嫂饼也十分受欢迎。当然最有特点的可能要数三百酒了。刚踏进酒坊,酒香就扑面而来。在水畔茶楼上,吃着江南小菜,望着小桥流水,即使不会喝酒的人,也难免想小酌几杯。清晨醒来,吃点儿江南粽子,一碗酒酿圆子,江南的情怀便荡漾心间。
乌镇是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相传乌镇的小商人想扩充店面,又不愿干扰邻居的生活,便将小屋向水面上延伸,延伸的部分就好像枕在水面上似的。乌镇人的聪明机灵可见一斑。我相信这片土地是有灵气的。梁昭明太子萧统曾随老师沈约在此地昭明书室读书学习,乌镇的水滋养了他,《文选》佳句千古传颂。说到乌镇,就不得不提茅盾。乌镇是茅盾的故乡,他幼年读书的立志书院便面对着乌镇这条静静流淌的水,而“林家铺子”正是在书院附近。水声、桨声、雨声萦绕耳旁,景与情交融,化作一种带有乡土气息的独特的文化底蕴,深深积淀在作家心间。可见宁静淡雅之景并非索然无味,静与淡包容了世间种种,有生于无,诗意悄悄流淌于无声之中。乌镇人的灵气还表现在他们的商业头脑。商业已融入了乌镇人的生活,但是我却并没有觉得这里俗气。乌镇分为西栅和东栅,西栅商业气息浓厚,很多人工雕琢之景,但东栅却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这种开发模式满足了商业需求,又保存了古典之景,不得不让人赞叹,也许也是其他江南小镇可以借鉴的地方。乌镇的饰品很有特点,扇子、头巾、衣服、小伞、小包、围脖……花样繁多,每样东西都染上了水乡特有的图案,既宣传了乌镇的染的艺术,又推广了乌镇的文化。
这里的人生活上并没有太多烦恼,做点小生意似乎只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打发打发时间,充实充实生活。因而,可以感觉他们都挺和蔼,并不斤斤计较。过日子嘛,可以维持简单的生计,还可以顺便推广文化,不过度就不失为一种别样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夜幕降临了,我静静走着,对面水阁里坐着一对老夫妇,他们面前是一盘盘江南小菜,老两口闲适地吃着、聊着。望着这一幕,我不知不觉停下了脚步。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若是没有大隐的功力,真不妨便在这江南小镇,粗茶淡饭,静静地沉寂一段时间,与小桥流水为伍,与诗情画意相伴。隐士之超世并非总是与世不合,也许正是阅遍人间种种辛酸冷暖之后,选择了一条自我解脱的道路。尝尽百味方知平淡是真。在这里,在江南,浅酌一杯小酒,静静旁望世俗的喧嚣纷扰,嘴角扬起一丝微笑。■
(高波荐自《石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