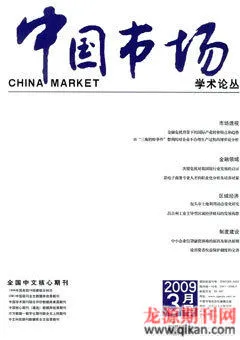简议宋代纸币流通和其监管法制
2009-12-29尚
中国市场 2009年13期
[摘要]宋代金融业发达,除了金属铸币外,还发行纸币。交子就是作为中国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北宋的四川。早期纸币的功能还具有初级性,但是其发行和流通对于解决宋代钱荒问题和发展商品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宋代纸币的流通并不稳定,除交子以外,还有钱引、关子和会子等多种名称的纸币。宋代封建政府为保证纸币发行流通的成功,也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法令,这套监管法令对于宋代金融体制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政府为了应付财政困境,常会不遵守其所制定的法令政策,使纸币成为政府搜刮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最终使宋代纸币通货膨胀,也导致宋王朝走向灭亡。
[关键词]纸币;通货膨胀;政府监管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09)13-0126-02
中国历史上的宋代金融业非常发达,这个时期曾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绢帛已退回到日用实物的原来地位,宋王朝不仅发行和使用金银铜等金属铸币,而且还发行了纸币。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即出现于北宋时期1023年的四川成都。整个宋代发行过四种纸币:交子、钱引、关子和会子。宋王朝对纸币的发行、流通和操纵,对于我们今天了解纸币的发行和流通规律以及政府在金融法制方面的作用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纸币产生的直接原因与宋王朝出现的钱荒有关。其钱荒的产生首先与宋代的商品经济的发达和金属铸币的落后密切相关。宋代商品经济非常活跃,而宋代的铜矿开采能力不足,其所制主要流通货币铜币远不能满足经济的需要;其次与其发达的对外贸易有关,宋代与周边辽、金、西夏、高丽、日本以及南洋诸国有着频繁紧密的贸易关系,北宋的铜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周边国家从而加剧了钱荒;另外还与连年战争以及战后向邻国输纳“岁币”有关。这些都造成了宋王朝金属货币量的严重短缺,形成了钱荒的局面。
由于宋代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仍处在一个初级阶段,所以这时的纸币带有临时性和早期不成熟的色彩。在产生之初往往只是起到证明资金的功用,是一种具有汇票性质的证券。这种票券最早始于唐代的飞钱。飞钱是唐朝的进奏院为商人开具的联单式“公据”或“文牒”,是给予商人用于官方承兑的凭据,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钱荒以及异地贸易金属钱币携带不便的问题。而宋王朝的几种货币的产生原因都与其大致类似。
交子产生于四川成都。当时四川使用的金属货币是铁钱。铁钱是贱金属,价格只有铜钱的十分之一,因此携带体积大,很不方便。《宋史·食货志》载宗正少卿赵安易所言:“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两万。”李攸《宋朝史实》中引述张若谷、薛田二人的奏文中的话:“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据此每文折合为6.5斤,一匹绫罗需要130斤重的铁钱。这无疑给商业交易带来极大的不便。于是民间首先出现“私为文券”的铺户。铁钱持有者将自己的铁钱存入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可见,这时的交子还与飞钱一样只是为了满足民间的汇兑需要。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在转运使薛田和张若谷的建议下,设立益州交子务,自二年二月发行“官交子”,交子的发行权从此转移到国家政府的手中。
其他几种纸币也大体类似。《宋史·食货志》载,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令诸路更用钱引”,把纸币定名为“钱引”。“钱引本以代盐钞”,而盐钞恰是给予商人买盐的一种凭据。既然钱引的目的是代替盐钞,可见钱引产生之初的功能与盐钞类似,起到一种凭据作用。关子的产生是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请椿办合用钱,而路不通舟,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人中,执关子榷货务请钱,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关子产生也是因为军情紧急携带金属铸币不便而采用的临时措施,可以和茶、盐、香料等钞引一样兑换国家禁榷物资,当然也可兑换为金属铸币。会子最初是南宋初期民间通行的便换性质的“便钱会子”。到绍兴三十年(1160年)改为官办。由此可见,宋代纸币在其发行之初往往是为了满足两地划拨款项的商业汇兑需要,侧重于证明性的票据功能,还不具有货币的完全职能。因此《宋史·食货志》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当然这些票券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其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慢慢具有了统一的面额和格式,用来买卖各种货物,作为支付工具使用,也就具有了一般等价物的特征,成为了真正的纸币。
纸币跟金属铸币比,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之所以能被流通和使用,就在于它是铸币的替代物。如果没有铸币作支撑,其本身就变得一文不值了。纸币在市面上的发行量需要与能够流通在市场中的同名金属货币量相对应,纸币的信用就能维持。当然一般情况下,流通中的纸币数额可以少于发行者实际藏有的金属货币,当人们信任纸币时,他们一般也不会需要将手中的纸币都兑换成实际的铸币的,因此往往不需要藏有等量的金属铸币。在早期,由于纸币与金属铸币相比信用度低,往往需要有相关政策和法规保证能够自由兑换为等价的金属货币,这样才能保证使用者对纸币的信心。纸币信用的维持,需要发行者有巨大的财政能力和信用能力作为支撑和保障。应该说相比于私人,政府的公信力要大得多,因为政府有固定的赋税保证,有其他政府实业的支持,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宋王朝政府为了保证发行纸币的成功,也是不遗余力出台了相应的金融管理法规和政策来保障纸币的信用,其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规定纸币的流通期限。一般是以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宋真宗(997--1022年)时,“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三年立为一界”。
第二,每界的发行总量有限定,币值有固定的面额。比如交子每次发行总量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其最初的面额为一贯至十贯等。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改为十贯和五贯两种。会子面额起初以一贯为一会,后来增发二百、三百、五百文三种。
第三,每印发一界纸币,一般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宋史·食货志》载:“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与其一界的发行量相比,其准备金大致为其发行量的28%。
纸币作为一种信用货币,其发行和流通的成功取决于政府的公信力。只要封建王朝政府能够维持其能够保证不滥发,或者保证自由兑换为金属铸币,那么纸币就能稳定。在纸币发行初期,一般来说封建政府是比较谨慎的,其监管纸币发行所公布的法律和政策也说明封建政府对纸币的内在规律是有充分认识的。然而一旦有了巨额财政开支的需要,封建政府往往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再遵循纸币的内在规律,通过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支出,从而使纸币成为了官府搜刮钱财的工具,无情地掠夺人民的财富,竭泽而渔。其结果必然造成纸币贬值,丧失信用。宋代纸币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其封建政府破坏纸币信用的行为如下:
首先,封建政府不再遵守原有的按界发行、新旧相因的相关法规。不按期换界,发行下一界交子时,不销毁上一界的纸币,两界交子并用,造成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数量严重超量。《宋史·食货志》载: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有两界自此始。”由于二十三界“给用”过多,需要用二十四界和二十五界两界的数额来补偿,其结果“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太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最终导致“罢陕西交子法”。如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诏第三、四界各展限三年。”以致招致当时大臣的指责:“会子界以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何以示信?”三年的期限被延至了九年,势必造成了纸币额的大量增加。
其次,纸币准备金不足甚至没有。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交子六十万贯,以支付粮草费,无钞本。北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仁宗时没有准备金的纸币发行只是偶尔为之,到徽宗时这一行为成为常态。
再次,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发行数额,而大量超额发行。《宋史·食货志》载: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耀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可见,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总量的数倍,甚至导致成都地区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大观元年(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这年的发行数“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也就是说发行量由一百二十万缗增加到二千多万缗。以致货币贬值,“至引一缗当钱十数,”价值一千钱的缗只能当十多个钱。
由于贬值很厉害,封建政府不得不在换界发行新纸币时,往往规定新币值按一比几的比例兑换旧纸币。比如大观元年(1107年),“新交子一当旧四,”即新旧比价1:4。元符年间(1098--1100年)换发时,新交子一缗要换回旧交子五缗,即新旧比价1:5。甚至新交子“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换界新币的发行演变为“通货膨胀”的障眼法。
宋理宗末年(1264年),市面上米价飞涨,市面上只见纸币不见米。咸淳十年(1274年),一贯会子已不值一文钱,通货膨胀恶化,最终蒙古兵灭亡南宋王朝。宋代纸币的兴衰对今天也有着重大启示:即纸币的发行能够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满足国民经济需要,甚至在一定时期能解决政府财政的燃眉之急。但是宋代纸币兴衰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政府的监管法制的维持对于纸币的流通使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纸币的通货膨胀,一般都与政府丧失诚信息息相关。封建政府为了“敛财”的需要,往往是主动毁坏了原有的金融法制,滥发纸币,其结局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体系的崩溃,甚至王朝的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