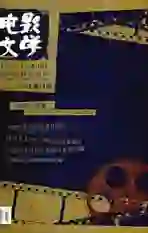《白鲸》中人物的精神生态困境
2009-11-26李小海
李小海
[摘要]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同时也会发生在精神领域。相对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来说,人类的精神生态的危机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价值取向褊狭,情感世界苍白、人性扭曲变异等,都是精神生态危机的种种表征。本文将从精神生态的审美高度,对麦尔维尔的《白鲸》中人物的精神生态进行探究,并尝试在精神领域寻找其生态学意义上的“污染”“变异”和“困境”的原因。
[关键词]精神生态;变异;危机;困境
一、引言
美国著名作家麦尔维尔(1819—1891)的长篇小说《白鲸》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作品,英国文学批评家卡尔·范多伦称它为“全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海洋传奇小说之一”,如果说霍桑的《红字》是阐述“人性”善与恶的力作,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梭罗的《瓦尔登湖》是描写美好的自然,倡导一种返璞归真、自然生存的一部作品。《白鲸》就是一部阐述关于人性、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类与自然如何相处、生存的又一部《圣经》。因此,它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作。笔者试从精神生态的角度来解读《白鲸》中主要人物的精神生态困境。
二、精神生态的界说
随着人类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摧残和戕害,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濒临崩溃的边缘。尽管人类已经做出种种努力,但生态危机的局面仍在日益加剧。那么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人类如何才能和谐、自然、诗意地生存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地球上?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因为人类只有在思想上去认识,在精神上去改变自己,才能融入自然,回归“人类内部的自然”(nature),即我们人的自然天性。所以,建立一个健康的精神生态环境,清除人类精神生态方面的污染、净化人类的精神生态,才是消除生态危机之根本。
鲁枢元先生在《生态批评的空间》里,把生态学分为三类:“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并且,鲁先生认为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
根据鲁枢元先生对精神生态的界定,精神生态学的研究可以分以下三方面:第一,在自然生态中实现自然地生态和谐、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即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和谐。第二,在社会生态中实现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的生态和谐,即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和谐。第三,在个体思维和内环境生态中实现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生态和谐,即精神生态主体的自我和谐。
如果我们用精神生态学的这面镜子,映照现今精神困乏的时代,就会看出:地球上人类社会中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正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污染所造成。本文从精神生态的审美高度,对《白鲸》中人物的精神生态困境进行探究,并尝试在精神领域寻找其生态学意义上的“污染”“变异”和“困境”的原因。
三、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生态异化
1精神生态被异化的埃哈伯船长
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应先于自然环境危机、自然生态危机。“因为,人类的精神危机将导致异化,人的异化反过来又导致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实际上,人类精神危机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者把人类抬到万物之灵的地位,人类成了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宰!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就是人类个体精神生态被异化的过程,在《白鲸》中,埃哈伯船长的精神异化主要就是疯狂的个人中心主义。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埃哈伯船长精神生态的异化。
(1)埃哈伯自我身心内外的生态异化,即精神主体的自我异化。自我中心主义使埃哈伯自立、坚强、勇敢、充满了自信和力量。然而,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又使埃哈伯精神异化,变成了一个邪恶、偏执、狂热的复仇主义者,一个极度自恋、孤僻的精神病人和狂人。他远离亲人,远离他的船员,远离社会,离群索居,沉默寡言。他四十多年的时间都是在海上度过,是一种漂泊的捕鲸生活,同时,他的心灵深处又透露出一种孤独和恐慌。四十年捕鲸生涯,四十年艰辛备尝,四十年危机四伏,四十年雨骤风狂!他经常把自己关闭在船舱里,远离众人。四十年来,为了捕杀白鲸,他发誓走遍好望角,走遍合恩角,走遍挪威的大旋涡,走遍地狱的火坑,他发誓,不是鲸死就是船破。这种变异的精神生态使他不能如常人一样去自然地生活,只能像魔鬼一样在海上疯狂。另外,断腿的生理残疾也标志他内部的精神失衡,同时也象征着埃哈伯内心自我精神生态丧失了整体性、和谐感。
(2)埃哈伯精神生态对社会生态的异化,这主要表现在埃哈伯对社会、对他人的一种敌视和冷漠,同时还表现在他的渎神。对神灵的不敬,对上帝的不敬实际上是对社会的不敬、也是对社会仇视、冷漠的象征。他虽为基督徒,但不敬神灵,唯我独尊。另外,埃哈伯精神生态对社会生态的异化还表现在他对水手的冷酷无情。埃哈伯性格暴躁,对人冷漠,对待自己的水手犹如使唤奴仆一般。在“披谷德号”上,埃哈伯自认为是船上的上帝,海中之王,当他的二副斯德布带着祈求的口气跟他说话时,埃哈伯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道:“下去吧,狗东西,到狗窝里去!”他甚至威胁道:“骡子,蠢驴子,给我滚,否则,我把你清出这世界。”这种对他人的冷酷无情、对社会的仇视都是他精神生态变异的表现。
(3)埃哈伯精神生态对自然生态的异化。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人类越来越狂妄和自以为是,他们逐渐抛却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而代之以对自然的贪婪和掠夺,甚至是一种疯狂的仇恨。”埃哈伯就是一个征服自然、掠夺自然、复仇自然的恶魔,一个追杀白鲸的疯子。在追杀白鲸的过程中,他的一条腿被自鲸吞噬,这象征着在与自然的决斗中,人类是不可能完全战胜自然的。相反,人类要遭惩罚,被大自然报复。尽管如此,埃哈伯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寻找白鲸并与之决一死战。这种复仇的心理让埃哈伯变得行为异常,变得残酷无情。为了捕鲸,他拒绝帮助他的同行寻找丢失的刚一岁的儿子:拒绝大副斯塔勃克放船员一条生路的请求。不管天气是如何恶劣,海上的形势是如何险峻,他强迫船员发誓找到白鲸并与之决一死战。这种发疯的复仇心理使他自己乃至所有的船员(除了以实玛利)走向灭亡,导致这场悲剧的发生。
2精神迷途的以实玛利
《白鲸》这篇小说,除了要体现埃哈伯征服、控制自然的精神思想外,还有一条很清晰的生态思想发展线索,即以实玛利对自然的观察和探索。以实玛利富有探索精神,他随“披谷德号”出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然的好奇并试图探索生活的全部奥秘。他是这样描绘他对自然的好奇心的:“这样一头凶猛异常而又神秘莫测的怪物激起了我
多大的好奇心啊。其次,是那浩淼无际、远在天边的大海,而这怪物就在其中腾跃翻滚它那岛屿一般的身躯……所有这些都促成我的愿望产生。”从精神生态学的角度看。以实玛利对自然的观察、探索彰显出人类希望有一种认识自然、融入自然的健康精神生态。尽管如此,以实玛利最终以猎人的身份加入了“披谷德号”捕鲸船。这种以猎人的身份去认识自然也体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社会里一些人迷茫的精神状态。在《白鲸》第十九章“预言生疑”里,也能看出他的精神迷途。在这一章里,当以实玛利、季奎格和“披谷德号”捕鲸船签了协约后,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问:
“你们当了他的水手了?……”
不错,我说,“我们刚签了约。”
“上面有没有提到你们的灵魂?”
“提到什么?”
“噢,你们没有灵魂,”他急忙说,“不过那不算什么,我认识许多没有灵魂的人——祝他们走运;他们没有灵魂倒更安逸些。”这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是以利亚。在《圣经》中,以利亚是希伯来的先知。这些对话的寓意是先知以利亚告诉以实玛利、季奎格他们加入“披谷德号”捕鲸船是没有灵魂的表现,签和约实际上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以实玛利代表着渴望健康的精神生态,而又逃脱不了人类中心主义影响的一些精神迷途的人。幸运的是,在追捕鲸鱼的过程中,以实玛利渐渐认识到自己的精神生态困境,从开始发誓捕杀鲸鱼到后来以实玛利以对鲸鱼的接受、欣赏,到和平共处,都表明了他对自然的理解、宽容,所以,最后只有他一人幸存下来。
3季奎格——被摧毁的原始精神生态
季奎格来自一个食人生番部落,他是原始道德、文明的象征。他有着被毒日头晒成黄里透紫的原始人的肤色,有着粗壮、遍是伤痕的胳膊和胸膛,他穿着粗布厚外衣,是个异教徒,是原始自然生态文明向现代工业化文明过渡的象征。在小说里,作者是这样描绘他的:“季奎格是个过渡状态的生物——既非毛毛虫,也非蝴蝶。他开化的程度最好让他以一种最为稀奇古怪的方式来表现出他的粗笨。”他粗野、诚实、善良,毫无文明人的虚伪和甜言蜜语。季奎格高大的异教徒形象,崇高的气质及高尚的情操,对以实玛利的心灵上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季奎格参加捕鲸船,象征着原始精神生态被现代文明所污染,季奎格的死亡象征着原始生态被现代文明完全摧毁。在这一点上,麦尔维尔比任何一位美国作家更早地开始审视所谓的现代文明。
四、结语
生态人文精神的价值向度在于,将传统的人类文明扩展到地球生态文明。人文精神生态已经超越了单纯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狭隘观念,而是将维护自然界的所有存在物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职责。人类的自由也只有在自然界的良性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相反。人类如果仍坚持传统的人类文明的人文精神生态,使自身的精神生态受到“污染”而“变异”,进而处于“困境”,人类的命运就会同“披谷德号”捕鲸船的命运一样,最终船毁人亡。这就是《白鲸》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麦尔维尔给人类发出的生态预警。
[参考文献]
[1][美]麦尔维尔,白鲸[M],成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陈茂林,解构与建构:生态批评的批评策略与思想内涵[A],郭继德,美国文学研究[c],济南:山东大学学报,2006:66,
[4]胡天赋,《愤怒的葡萄》:一部伟大的生态文学之作[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05):37,
[5]岳庆云,《白鲸》:人与自然关系的悲剧性预言[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