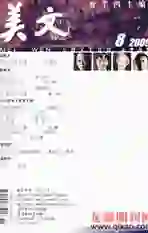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2009-10-24田炳信

田炳信资深记者,作家。现任暨南大学中国口述历史传记中心主任,曾出版了《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中国第一证件》、《思想咖啡厅》、《基围虾现象》等十余本著作。
北 风
北风过去了
北风过去了
北风过去了
人们都说太阳通红
我凝视了一分钟
打了十二个喷嚏
伸出双手
冻红的还有五颗铜扣子
大漠风有龙的基因
大漠的风妖冶,放荡,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无人能拦,无人敢挡。来时无声响,走时无招呼。随意,放肆。像野云,似浪月,飘哪算哪,挂哪亮哪。无拘无束。像半仙,似老僧,横七竖八,佛魔不二。
风在大漠的聚合,像牧草在草原的聚合,聚有力量,散有基础。静时是大漠的筋骨皮,动时是大漠深处的一口气,大漠是风的家园,风是大漠抚着的孩子,顽皮,淘气,无大无小,无强无弱。
人对自己驾驭不了的事,总是怀有七分恐惧,三分敬畏。敬鬼神而远之。这六个字是人类对大自然中神秘、莫测的事物的一种矛盾、复杂、无奈的种群心态,敬的东西不靠近,靠近的又不敬。对大漠游荡的风,人也是如此,明晃晃的暖阳刚笑出一朵大菊花,风就像成吉思汗大帝的铁骑,呼啸而来,人正纳闷时,风又像乖乖的小兔,匍匐不前。喜怒无常、行踪不定的大漠风,人类给它起了一个又敬又怕的好名称:龙卷风。龙是人类控制不了的一种天神,龙卷风是人类驾驭不了的一种风,人是欺软怕硬、趋炎附势的一种高级动物。控制不了,驾驭不动,不是人类无能,不是人类中的头头脑脑无能,实在是龙的家庭出来的龙哥龙弟龙姐龙妹谁敢惹,谁敢碰。
骆驼不怕风,骆驼有龙的基因,是龙的家庭中的异类,传说骆驼有十二属相:风静卧时,软软,松松,绵绵。一种软力量,一种以柔克刚,一种以静制动,骆驼不惧,它有九只大驼蹄,踩软踏松。风狂舞时,骆驼有一双像小梳子般的长睫毛,微闭半睁,风奈何不了,双腿一弯,像凝固的沙丝,像战场上的掩体,赶驼人只要蹲在它身后,风卷不走,刮不跑。
大漠中不怕风的还有植物,甘草,根的长度,像一条条地龙,吸纳大漠中稀少的水分,芁芁草,在夏季就像干柴,无水分,有绿色。风来了,抖抖,风停了,立立。风奈何不了。风是一种时间的刻度,风是一种试验的机器,风是一种打掉瞳仁伪装、装蒜的一种力量,能与大漠风共舞,那是一种博弈后的平衡,角斗后的喘息。一片大漠中,植物、动物能多姿多彩的共存、共生,一定有多姿多彩的个性在张扬,一家有一种神秘难测的力量在支撑。
大漠的风,真是人类该尊重的一种风。
草原三大害
巴谚浩特,是内蒙古阿拉善盟的首府所在地,按小城的规模也就相当于内地的一个镇,不过,比发达地区的镇更僻静,萧条。虽说人少,但土地面积大,2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宁夏建制,也是地厅级,“衙门”的格局一个都不少。我去的时候,阿拉善盟有14万人口,骆驼有20万峰,羊有几十万只,吃皇粮的人数有一万多人,平均14人养一个吃“皇粮”的。
盟宣传部长是个蒙古族人,叫那木,我们称他为那部长。人长的精瘦,却很精神。大小记者他见多了,新华社记者可能来阿拉善的比较少,而且还要骑骆进沙漠采访的就更稀罕,那部长挺重视。当天晚上在他家杀了一只羊,吃了一顿手扒肉,晚上在他那宽大的院子里,有半院是已熟了的葡萄架,皓月当空,一边吃茶,一边吃着马奶子葡萄,一边闲聊着。聊到什么话题,我忘了,那木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笑话,讲了你别生气。我知道凡是笑话准与一种人或一种职业为调侃的对象,我说,没事,你讲吧,笑话嘛,听了就笑的话,不就是笑话嘛。那木喝了口茶,不紧不慢地说开了。当地牧民说,我们阿拉善草原上有三大害,狼是第一害,狼吃羊这你是知道的,还有第二害,是干部,干部吃的羊比狼还多,狼吃一只羊,半个月不来吃了,羊群能安静好一会儿,可干部是天天来吃,一次不是吃一只,是吃一群。我问,第三害呢?他看了我一眼,诡秘地说,第三害,就是你们记者了。我知道,单纯从吃羊的频率上计算,狼和干部是早已定型了,第三害呢,一般是可以替换的,有时是记者,有时是乌兰牧骑,有时是税务局,有时是公安局。
我问那木,阿拉善这么偏远,来的人多吗?那木说,怎么不多,除了盟里的干部,还有旗里的干部,还有苏木的干部,再加上呼和浩特的干部,北京的干部,和各个口子的上级单位的干部,你算算,我们这里每天要接待多少人,有时真让人招架不住,可是没办法 ,哪路神仙都是神仙,哪个口子下来的都是爷,得罪不起,惹不起!
很多年了,鼓励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又鼓励干部深入基层,其实,就那点事,能解决的不去也解决了,不能解决的,谁去了也解决不了。有些事了解是那个事,你不了解还是那个事。
我翻闲书,明清两朝对官是有明文规定的,一般情况下,不准随便深入族里、村里、乡里、林里,扰民是一条罪。民间对相互串门子也有一种不好的说法,没事瞎串门,非奸即盗。可见,古人对人性恶的一面是有透彻、清醒的认识的。
没给阎锡山平反
1983年10月底,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派我带车到河南原阳县和武陟县给单位搞福利——拉大米。那时,单位好不好,就看福利搞得好不好,是很多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一种常态。原阳县的大米在中原一带是有名的,装车后,经武陟县到了竹子多得像小森林的博爱县。博爱县就在太行山脚下,从山脚翻越太行山,前后走了17个小时,太行山上的盘山公路正在翻修,只有一车道,汽车慢得像蜗牛爬,在半山腰上,汽车一米、十米的向前挪动着爬行。这时,公路边,一个穿着破旧黑棉袄,腰中扎一绳子的老农民向我打听,你们是新华社的?我说,是,有啥事?听说现在给地主都平反了,我过去是打日本人的,不知能平反不?我心中好疑惑,莫非碰到一个当年的老八路,流落到此,人世间什么事都会发生,特别是那个动乱不宁的年代,许多人的命运由红变紫,由紫变黑,由天上到地下,由好人变坏人的事,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我问,当年你们最高首长是谁?老人答,阎锡山。阎长官当年带领我们在太原打日本人,战斗很激烈,死了不少人。我想了想,右派是平反了,地主、富农是平反了,没听说给阎锡山平反。我告诉老人,没听说给阎锡山平反。老人估计识字,看了看喷在驾驶室的车门上的几个字“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还是蒙汉两种文字,失望地说到,你要说没平反,我信,他指了指驾驶室车门上的几个字,然后,沿着下山的路走了。
信息的闭塞,会搞出许多政治笑话,同时,也会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落差形成的缝隙中间,该有多少人的眼泪、青春、梦想在充填着。无法调查,无人去了解,历史是由一群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构成的,是由一群得意和失意的人涂抹的,是由说谎的嘴巴和不辨真伪的耳朵构成的。历史就是在一声叹息,百种感慨,千种联想,万种猜测中,不慌不忙地消失在一代代人的视野中。
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小时候在军工厂看电影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在俱乐部的放映厅,5毛钱一张门票,第二种是单身宿舍后的足球场上,露天放映,你要看,就要拿上小马夹子、小板凳提前占座位,晚8点准时放映。晚6点到8点之前,总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当晚上映的电影的片名,一般是十回有十回准,问他怎么猜得这么准,他诡秘一笑,放电影的是他二姐夫。有人就有消息。
许多部电影是放了又放,那时被查禁的电影多,能放的电影又少,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又不能不放,一部《地道战》我看了不下十遍,一部《小兵张嘎》也看了不下十遍,台词都记得烂熟,那时孩子们在一起,最爱说的一句话:学着《小兵张嘎》中的日本翻译的口气说,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下馆子都不给钱。成人后,才发现这台词也是一句真理,每朝每代都有一批人是下馆子不给钱的。
当时没有大片和黄片的说法,只有批判片和内部片的说法。内部片和批判片一般是在厂子的俱乐部里放,也是免费的,中间休息20分钟,一般是一场连着一场,先是党员副科以上干部,军工厂当时级别是正厅级,党委书记是一把手,厂长是二把手,党委书记长的像个笑西佛,体大肉多;厂长长的像个山中道人,面黑肉少。第二场一般是党员,包括工人和技术员中的普通党员,然后是革命群众。这个知道信息的顺序到今天也没有多少改变,只是因特网这个淘气蛋,一个恶作剧,把这种程序搅了个乱七八糟。
《英雄儿女》我看了不下十五遍,受电影中王成的影响,只恨晚出生了几年,不然也可冲锋陷阵当回英雄,那是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代,也是时刻准备打仗的年代。穿军装,戴军帽,是一种时尚,崇拜军人,姑娘嫁“三点红”也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时髦。
只有一部电影看了一遍,名字到现在想不起来了,可有一句台词至今还记得: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墨索里尼在二战时是意大利的总理,“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应是墨索里尼是总理的一种诙谐的说法。就像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其中由四野、二野喊出的一个口号,响彻半个中国:“打倒蒋该死,解放全中国”。蒋介石是个名字,怎么会发音成了“蒋该死”,原来湖南人发音蒋介石就说成“蒋该死”,毛主席是湖南人,他发音蒋介石就是“蒋该死”。伟大领袖都这么说了,北方兵加上北方的宣传干部,大标语一贴,大喇叭一吹,快板一数落,这种说法就一次定型。这算不算是一种以文化传讹,不管怎么讲,把蒋介石叫成“蒋该死”至少当时是代表了民众的另一种情绪和看法。民意如江,一泄万里,无人敢挡,无人能挡。
当年的墨索里尼,据说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铁嘴钢牙的一个主,有理搅七分,无理搅三分。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紫的,只有赢,没有输。这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好马在腿上,好男在嘴上”。你现在慢慢一琢磨,总能品出一点味道。历史上也好,现在也好,外国也好,中国也好,其实当你成了控制真理的人,掌握真理的人,制造真理的人,解释真理的人的时候,真理真是长在你眼眶里的一对眼球,想白眼仁多就白眼仁多,想黑眼球大就黑眼球大,想看那里就看那里,谁也奈何不得。我上大学时,其实是刚从一个极为简单而又盲目崇拜的年代泡出来的人,能有多深刻的思想,能有多阴险的念头,那时有个没读大学,可在中国名大学校园里如雷贯耳的一个诗人,他办了一本地下刊物,叫《今天》,上面有一句,至今还觉得深刻的味道十足: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代愤青的头子随着这一句名言而在当时确立了他的江湖地位。那年头,学深刻,扮深沉,玩深遂也是一种校园流行文化。我赶着潮头的小尾巴尖,也写了一句:真理是狼,谁抓住了,都能吓唬对方。
真理不是狼,也不是羊,既不是披着狼皮的羊,也不是披着羊皮的狼。真理说到底是一种实力,在真理的背后,至少站着这样一群保镖,实力,科力,武力,财力,而在这一群咋咋呼呼的人的背后,又站着一个字:利。我说“利、力、理”,顺序不能排错,不能排颠倒。一颠倒,不是力量储备不足,就是大脑神经出了故障。
大漠炊烟是信号
当记者,半仙半鬼,居无定所,食无定点,飘泊不定。走哪吃哪,到哪睡哪。牌子大,接待规格自然高,招呼自然热情周到。不是你有神功,不是你长得异于常人,人未行,电话到,再早是电报到,口信到,传真到。有通讯员相接,有宣传部相送,有车坐,有肉吃,正所谓,食有肉,行有车。大牌国家通讯社记者下乡采访,大都是这一套路,没啥牛可吹。
在巴丹吉林大漠转悠的日子,一种完全无依无靠,无信息传递的环境中,能体验到一种原始人性的温暖和光芒。
那天,风没有撒野,日头没有撒泼,倒是骆驼撒着欢,像在一幅油画中慢慢前行,翻过七座沙山,远方透露出一点绿,两三座火柴盒大的房子,几天大漠中行走得来的小经验,那又是一户牧驼人家。看山近,跑山远,对山而言是真的,对大漠中的沙山而言也是真的。
没有通讯的社会是一个落后的社会,更是一个人性纯朴、人性纯真的社会。大漠的牧驼人家,大多是一家一湖,相距甚远。鸡犬之声相闻,这话至少是农耕社会的语言痕迹,大漠中无鸡鸣,无犬吠,寂静得像天上永不讲话的一颗星星。
骑驼是另一种乐趣,慢,晃,或者说一摇一晃。心能放平,肉体能放松,视野里少了许多人造的景观,听觉里过滤了杂七杂八的声响,那是一种精神与肉体的大漠浴。
驼队慢慢地前行,可参照的物体就是那户牧人的三间小土房,我看到房子开始变成一个装电视机的包装箱那么大时,一股细细的炊烟羞答答地飘向天空,向导说,像是已看到驼队了,正给我们熬茶呢!我说,你怎么知道会是熬茶?他说,到了你就知道了,这儿牧人心眼实。
我在历史书中看到每有战情,外敌入侵,最原始的通讯工具就是烽火台上的狼烟,一站连着一站,我想狼烟应该是用狼粪烧的一种烟:耐着,烟气大。这次的沙漠之行,我看到了另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炊烟升起,他们烧的不是狼粪,应是羊粪和驼粪吧。
炊烟由线变成一缕缕时,三间黄泥巴的小土屋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户牧民全家都出来,在门前等着我们这群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到来,对他们而言,来的人都是稀客,贵客,没有城市人那么小心眼,那么势利。
房间是一进二开的甘肃民勤一带的土房结构,互敬了烟后,热腾腾的奶茶一碗一碗地端上来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屋子收拾得挺干净,土墙上有孩子的奖状,有装在玻璃框里的全家福的照片,还有过期的挂历。大漠人家是干干净净的,家里每个人也都收拾得立立整整。朴素,简单,整洁,全不像一户独居大漠深处的人家。这些年,我走南闯北,见了不少人,也参观了不少画展、影展,大凡到了人迹罕至的地方呆上那么几天的人,在戈壁上流窜过几天的人,在大漠中游走了几天的人,一定会给自己留几张照片,装一脸苍桑,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好像吃了天上的苦,遭了人间的罪。装风尘,这也是这些年又一种新的时尚。人啊,总是变着法地折腾自己,也折腾别人。
大漠对我们是驿站,对大漠中的牧民是家园,是天堂,是一份自在,一种自足,一份自得其乐。不给外人看,不用装什么,也用不着焦虑地去显摆。高僧讲,人生最难得的意境是一份大自在,我看这户牧人家每个人的眼神透露着平和,祥和,那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大自在。像我等凡尘中的俗人,别说大自在,就是小自在也难受。
一湖沙水是镜子
巴丹吉林沙漠是中国的第二大沙漠,是垂直高度最高的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的神奇,不在于沙漠本身,只要你有机会深入沙漠腹地,你就知道比大漠还神奇的是沙漠中一汪小湖。半月型的,周围长满了两三米高的芦苇,有蜂飞旋,有蝶环绕,有鸟斜插,有野鸭飞渡。
我骑驼走了四天,按天算是长了点,按驼程算也就12公里,在广深高速路上,一踩油门,汽车再好点,也就是20分钟的车程。在大漠里晃荡,视觉是疲劳的,颜色是黄色,早晨是淡黄,中午是沙黄,傍晚是金黄,风起时是灰黄,风停了是桔黄,满眼是黄颜色。远看是黄色,近看也是黄色,养眼有两种,一种是美人,一种是绿色。在大漠中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看骑的骆驼是一种褐黄,沙漠中的沙蒿是一种焦黄,甘草是一种苦黄,无上的云和风拢在一起是一种白黄。白天的太阳是一种暖黄,晚上的月亮是一种冷黄,星星们总是眨着一种琥珀黄问你看懂了什么,按色谱分析看,真颜色有七种:赤橙黄绿青蓝紫,黄和绿是颜色季节中的分水岭和里程碑。赤是深黄,橙是中黄,青是浅绿,散发黄毛丫头加楞头小伙子的胴体气味的一种绿,蓝是中绿,不温不火的绿,紫是深绿,一种熟透的绿。
大漠幽幽的生命流程图中,正暗合着这两种颜色,我原以为大漠是一种颜色,一种病色,一种真色,一种大色,当我看到湖,大漠中特有的湖,绿得像一块玉,静得像一幅画。
湖里也是一个喧闹的小世界,芦苇的倒影横七竖八,展现着一种繁杂和茂盛,鸟的影子是一闪一闪,湖水像看透红尘的老者,笑容满面,一种包容,一种大度,任你点,任你划,任你飞,任你翔。野鸭谁都不怕,不飞不惊,在湖面上不紧不慢,不徐不疾,不慌不忙。
我站在湖边,先看到了自己的脸,再看到了身影,照了又照,很久没有见到镜子,原来湖水也是一面镜子,白云滚过他照过,大雁飞过他照过,风起风停他照过,照过就照过,其实什么也没有。骆驼不照镜子,蝴蝶飞来飞去也不照镜子,只有人照镜子,看看自己,再看看周围,原本无痕无迹的大千世界,留下的乱痕糟迹,只有人在意,人留心。湖水并不当回事。
月亮升起来,湖里多了个痕坑,太阳落下去,湖里多了一幅乡情的红唇。风来了,湖皱皱眉头,雨来了,湖水变成水晶宫。
换个姿式再来一次
在省府大院的卫兵,晨练列队跑操时,在整齐有力的步伐中,不时夹杂着各种口令,除了一二一、一二三四,还有一句:换个姿式,再来一次。谁听了谁都会笑,这句口号会让人产生很多歧义,毕竟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年轻人,口令都能玩出花样。谁也不能说他们喊得不对或喊得对,你总不能用六七十年代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口号让他们在21世纪再喊一遍吧。
仔细观察社会的各个部位,也都是换个姿式再来一次,形式不同,内容也不同,加多少减多少,完全看当时的情形和文化背景了。
1964年,毛主席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而解放军里又主要学习雷锋,3月5日是雷锋逝世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各个部门、机关、院校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纪念雷锋,学习雷锋,而核心内容,不外是免费做好事,当好人。
1991年3月5日,我还在新华社广州记者站工作。一天,我看到广州的南方大厦的附近,挂出了一大横幅,学习雷锋做好事,XX牙膏大甩卖,特幽默的标语又特实在,如果要讲典型标语,这应算一条。政治说教和商品推销完善结合,不自觉的政治行为和自觉的商业行为结合,一虚一实,我看也属于换个姿式再来一次的范畴。
中国的社会,在近26年中,是一个逐渐转型的社会,有时急,有时缓,有时让你摸着头脑,有时又找不着北。当时,民间有一顺口溜: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才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我认为对那个时代转型的不稳定的概括是相当到位、准确的。广州作为一个南方的大都市,本身也是在“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的多种评价体系中慢慢熬过来的。好与坏,香与臭,错误与正确,本身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只是领潮的个人、团体、城市的再来一次,来得快了一点,早了一点,所呈现出的不成熟、不稳定会留给后人许多说法,笑话和谈资。
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健全的社会除了道德层面的尊老爱幼外,更本质的核心是尊强爱能;从人性的角度看,喜新厌旧也一定是人类不断进步的一种原始的推动力和神奇的爆发力。
“换个姿式,再来一次”,不仅仅是跑操的大兵的口令,更是一个转型社会所能包含和包容的一种姿式。
大森林印象
建国后,大兴安岭森林被两个正厅级林业管理局管理,说是管理,说白了就是砍伐。这两年,人们伐着伐着才发现,次生林再生也生不过原始森林。儿子像老子,但怎么也不是老子。虽然人工补种、飞机播撒,怎么长都长不出老森林的财大气粗,膀大腰圆。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人家生了孩子,邻居笑着说,这娃儿不像爹不像娘,倒像隔壁的王木匠。
上帝造森林时,就算到人类会有这一手,你以为像人类造小人人一样,越造越幸福,越造越快乐啊。原始就是原始,次生就次生。原始不是次生的爹,次生也不是原始的儿子。一个叫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局址在黑龙江,森林面积只是大兴安岭森林的三分之一;一个叫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局址在内蒙古,管辖的森林面积占大兴安岭的三分之二。奇怪的是,面积大的得了个小名,面积小的得了个大名,我估计当年的林业部长有黑龙江情结,胳膊肘一拐,就把大名送给了黑龙江。
这种事,过去有,现在也不少,当年的深圳,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蛇口,十几年后,蛇口和南头区合并时,已是响当当的蛇口,没有变成新区的名字,反而起了一个南山区取代了蛇口和南头,现在人们记忆中还有蛇口,什么南山北山,有几个人能知道。这是闲话。
我前后去过三次大兴安岭,第一次是到牙克石林管局管辖的阿尔山林业管理局,属牙克石林管局下属的二级局,第二次是大兴安岭着大火,我是新华社驻满归报道组组长,前后呆了二十多天。还有一次专程到鄂伦春自治旗,探访中国唯一的游猎民族和那个孕育了少数民族精英的嗄仙洞,鄂伦春就在大兴安岭的南麓。
我就说第一次吧,二十郎当岁,混进新华社的队伍,兜里揣个小本本,走哪哪都挺重视。阿尔山林管局专门开出了专列,所谓专列,就是专门运送木材的小火车,比正常的轨道要窄。当年京剧《林海雪原》里有“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那火车指的就是我乘坐的这种窄轨小火车。阿尔山林管局挺夸张,专门在管局门口挂出大横幅,有生以来,受到超规格的接待还是第一次。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新华社记者来我局指导工作”。局部所在地,环境优美,白桦林和红松是管局的背景色。
第二天早晨,驱车到了一片还是原汁原味的老林边上。我是第一次来大兴安岭,也是第一次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大森林。用一个有时代感的词形容,我看到的大森林是一派老贵族风范。林子里的枯叶、腐叶、病叶铺得厚厚实实,散发着一种独有的森林的腐气。林子一老一大,阳光洒不进来,月光漏不进来,那是一个盘根错节、互相缠绕、封闭而骄傲的森林家族。在林子里漫步,是没有响声,不留印痕的。松软的树叶,你踩上去总会觉得不踏实。白天的林中的光线看上去像黄昏,黄昏的景色看上去像夜晚,夜晚的景色又像走进一个怪异的梦中,大森林就是这么千奇百怪。
我去的季节是森林最肥的季节,红的红透了,紫的紫过了,绿的绿出油了。所有的野果,地上,树上,草里,都到了“临盆”的日子,你稍一不小心,就会听到一阵阵瓜熟蒂落的野果的啼哭声。人开始忙碌起来,采摘到的野果少的自用,多的晒干。人忙,各种小动物也早早忙上了,三条杠的松鼠,大嘴的杜鹃,都各得其所。
草原白蘑赛狗肉
世界上不讲理的事很多,其中也透着一种大歪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河北张家口,并不产蘑菇,张家口的口蘑早已名闻暇迩,蘑大,色白,肉鲜,营养价值高。蘑菇莫非是从天上掉下来,不是,是锡林郭勒大草原上几个旗盛产的蘑菇。拾蘑人在每年七月份,雨水大的月份,长了一春一夏的牧草见水就绿,在牧草丛中,那一圈圈的蘑菇也不讲价钱,忽啦啦白出一地,特别是羊群休息过,交配过,成群结队拉过羊粪,撒过羊尿的卧营地,更是蘑菇生长的小天堂。拾蘑人拿过大桶,一桶桶地采摘后,等明晃晃的大太阳打哈欠时,蘑菇就晒成了干,晒成干的蘑菇再装到大麻袋里,坐上大马车、小驴车、四轮拖拉机和草原长途汽车,一路颠颠簸簸到了张家口的蘑菇市场,就有了一个统一的番号,名称叫口蘑。
我去锡林郭勒草原的乌珠穆沁旗正是七月底,雨水像赶集似的,一场赶一场,草地上的蘑菇也就淀出一圈圈的白,一团团的白,像是白云下凡,又似羊羔成仙。
同去的人中,有一北京老知青,在乌珠穆沁旗下乡七年,会蒙语,会操蒙古刀吃羊肉,也会假装豪爽地喝马奶酒,还会唱几段跑调的蒙古长调。他告诉我,草原有三鲜,一是当年的羔羊肉,二是新挤出的鲜马奶,三是七月草地冒出的白蘑菇。我说羊肉鲜,马奶鲜,我领教过,蘑菇鲜怎么讲。他说,很简单,你跟我来,在牧民朝鲁巴根的蒙古包里,拿了一个铁皮大桶,走出也就十几分钟,就见到了像画一样的蘑菇圈,大的如巴掌,小的如拳头。很快就捡了一桶。回到蒙古包,他熟练地点起了一堆干牛粪,上面放个铁皮筒子,把蘑菇一个个倒放在铁皮筒子上,热后每个点上黄油,撒上盐粒,不大的功夫,在牛粪火的炙烤下,鲜蘑菇水被炙出来,他说,可以吃了,这才叫真正的一口鲜,我拿了一个,放到嘴里,味道是任何酒店大厨烹制不出来的。那一次,我才知道鲜蘑菇还有这种吃法,原始,刺激,真味道。这那是干蘑菇无法相比的。那次的草原之旅,让我明白了一个浅显而又不夸张的真道理,人世间许多事,许多人,一旦离开了特定的环境,也就失去了其真味道,原本色,大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