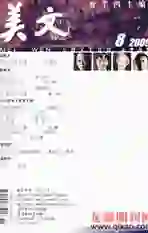文友三记
2009-10-24炜评
炜 评

刘卫平笔名炜评。1964年生于陕西商洛市,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西北大学中国西部作家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兼事文学批评及散文、诗词创作。兼任陕西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柳青文学会副会长等。
上 善 若 “孙”
我说的“孙”,是指文人孙见喜。
文人孙见喜的职业,是文学编审,供职太白文艺出版社,前年已退休。他在编辑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策划出版过数量相当可观的好书。但孙公被更多的人知道,是作为一位著名作家。然而,在我眼里,孙见喜的形象,更偏于另外几个方面:仁者、智者和韧者。
孙见喜家里挂着一幅他的肖像画,系画家马河声所作。画面上的孙见喜不修边幅,胡子拉茬,颇似一位饱经风霜的老矿工。但嘴角和眉宇间荡漾着的微笑,略带几许俏皮和嘲讽意味,仿佛在说:看清楚啦,我就是苦大却笑对世事的老孙。马河声既才盛,又眼“毒”,这幅画,端的是状绘出了孙见喜的神态。
孙见喜这多年,生活上受苦多,写作上下苦也多,所以我说他“苦大”。他中年以后,日子不顺,尤其是妻子出了车祸以后的十多年间,遭的作难,无法尽述。要是换了我,天天都烦心,哪有心力务弄文学及其它?可孙公,竟有能耐措理诸多头绪,且笔耕纸耘不辍。这20多年间,他既给别人编文章、编书,又自己写文章、写书,迄今为止,累计出版、发表的散文、小说和评论,已有好几百万字。前不久,陕西作协评选出的“柳青文学奖”获奖作品,就有他的长篇小说《山匪》。他还是一位追踪研究贾平凹的学者,读解贾氏及其作品的海内外专家,早就无法绕开他的著述,特别是篇幅长达130万字的《贾平凹前传》。人生的成绩,来自运气的,比如“福将”的战功辉赫之类,有是有,但极少。苦出来的,十有八九。我吃苦精神差,出的活就少,因此格外佩服他。
受苦多的人,有的变得脾气暴躁,牢骚满腹,或待人接物“生噌冷倔”,我戏称为“仇深”。另一些,则更有恻隐之心、怜爱之心、理解之心。我眼里的孙见喜,是后一类。朋友们善意传笑过他的一件事,是他惜老怜贫反被怜惜对象“耍故事,用方英文的话说,就是“心好得快没原则了”。
孙见喜人缘广泛,有交无类,政府官员、作家诗人、专家教授、贩夫走卒、渔翁田氓等等,都可以是他过从、往来的友朋。双仁府街的孙府,既是文人雅士的会馆,又是家乡“下苦人”的办事处。商洛老家的农民在西安出了事,首先想到的是找孙老师,然后才考虑是否去派出所报案。相识多年间,我从不曾见他拒绝过给谁帮忙。当然,他扶助最多的,还是业余文学作者。不少学写作的青年人,因了他的鼓励和扶植,挺过了最难的阶段。孙见喜起居简单,生活却丰富。西安文人自发组织的几个民间艺事沙龙,都活跃着他的身影。节假日里,孙见喜经常邀朋友们一起上山下乡。朋友们吃住不惯的土屋草舍,他不仅习惯,而且怡然。他有过几句说法,我一直不忘:“给下层人办难场事,和下苦人快乐相处,是一种很人文的情怀。”
仁者孙见喜,可能会让施仁对象“日弄”一回甚至多回,可他更多的作为,散放着智慧。孙见喜穿着不甚精致,精致的,是他的文字。他的散文和小说,都有自家路数。他写文章,用笔不苟,运句讲究,绝少平板话语。我曾见到陈忠实关于《山匪》的评论,老陈文中最赞赏的,是孙见喜以方言作小说描述语的慧心智手。我对孙见喜慧心智手的感受,比忠实老师更多一些。他的慧心智手,不仅施于散文、小说创作,还施于写书法、玩乐器、通电脑、吟诗赋、唱歌、炒股、鉴宝等等,颇有些关汉卿式的丰富多彩。
孙见喜的仁和智,接触过他的人,都有鲜明的感知。可在我看来,既坚且韧,才是此公最可贵“性情线”。他40多年经营自己的文学园田,收获逐年渐丰,靠韧;30多年跟踪研究贾平凹,自成一家,靠韧;10多年独撑一门光景,老少俱安,还是靠韧。孙见喜的韧,与他对孙氏家族的精神基因的传承有一定关系。他们孙家几代人的生存毅力和智慧,在家乡一带是有名声的,也被他作为素材写进了《山匪》。但作为文人,这种韧性,更多得于建立在自信之上的自为。的确,这个男人身上蕴藏着的丰沛的、沉实的、活跃的生命能量,常令我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在他60多岁时,这能量,依然时时外化为种种积极、乐观的行走姿态,成了我眼前常见的一道生动景致。所以,我乐与他游,并说他“上善”,由衷地。
师 傅 何 丹 萌
五年前,我在酒席上结识了作家何丹萌。不久之后,他成了我的师傅。
起先认何丹萌为师,只因了戏谑的话。何丹萌多年走南游北,积攒了满腹的“风土歌谣之诗”,在朋友聚会场合,张口便能唱道出大串大段的野谣酸曲,辅以他不无夸饰的解说,庄谐并出,妙趣横生,使我大为艳羡,遂对他说:“收我为徒吧,将来城市不养文人了,我跟您一起穿乡过镇打井卖唱去”。他大笑,说我拜师学艺动机不纯,因为我说的“打井”云云,双关了一个“典故”:贾平凹中篇小说《天狗》中的主人公随师傅打井,手艺日益精进。后来师傅工伤瘫倒,要徒弟与师娘成亲,演绎出一段令人嘘唏的悲喜故事。20多年前,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歌剧曾上演并轰动一时,编剧者正是何丹萌。戏谑归戏谑,师傅却就这样拜定了。五年过去,我并没有从何丹萌那里学到多少俗歌俚曲,但我们互动频繁,肝胆相照,无话不谈,烧洒喝了几大缸,做了文章先拿给对方讨表扬或招痛骂。在这样的过程中,师傅和徒弟的关系,逐渐铆紧焊实了。
在我看来,先生与弟子、老师与学生、师傅与徒弟,乃是三种相近却有别的人伦。大抵而言,先生与弟子的钮接,在于学问;老师与学生的关联,在于学业;而师傅与徒弟的牵涉,在于谋生。总之,上述三种人伦中,师徒关系是最劳动人民化的。也正因了这个原因,在师傅和徒弟之间,往往贯通着某种类似亲情的感觉。可很多一辈子被人尊称先生或教师的人,其实与称呼者并不亲近。自从会说话以来,四十年间,被我叫过先生或老师者,多得去了,但我称作师傅的,却只何丹萌一位。
其实,我尊何丹萌为师傅,不是因为他长我8岁,也不是因为他学识渊博,更不是因为他能授我以脱贫致富的高招。真正的原因是,他是一个活在当下中国陕西地面上的“古希腊人”——我指的是性格、情操和行止。用较为时髦的语词来说,何丹萌是一个非常“阳光”的男人,其磊落与坦荡,今世实鲜见焉。这种男人身上的阳光性,对我具有亲和性和渗透力。让我把毛泽东的话揉进句群中给何丹萌写一小段“操行评语”吧:何丹萌,散文家、剧作家、美食家、棋手、饮者、玩家……挥金如土过,穷愁潦倒过,也风光一时过。为一些人所激赏,亦为另一些人所不屑。其言行也,不屈己,不干人,任情率性,不拘细谨。总的来说,不失为一个善良的人,厚道的人,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由此尊敬了他,也爱戴了他。
我师傅是一个游走在文坛边上的作家。我读他出版的《有了苦不要说》、《贾平凹透视》以及很多大小戏剧作品,很鲜明地印象了他的写作天分。他有很强的文字造型能力,能把人、物、事描绘得“蔚似雕画”。他的文学语言,非常清新流畅,只是不甚注重字句推敲。我师傅写作20余万字的《贾平凹透视》,前后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功夫,可见他驱笔之速。但我师傅不是一个勤奋的写家,所以作品数量有限。和我一样,他写东西没计划,从不给自己加压,想写便写,不想写了拉倒。至于文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更不进入我师傅的思维。这后一点,方英文曾在一篇随笔中做过生动的评述。我知道,不少文朋诗侣对我师傅的创作“实绩”很不满意,就像他们对我的学术“实绩”不满意一样。他们认为,他未能把个人才质、阅历、感受等方面的“资源优势”转变成“产品优势”。这种不满意,当然纯出一片好心。但我并不这样想,至少不完全这样想。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态,理想生态的关键指数,乃是过得“适我”,而这“适我”,说白了就是,自己感觉好,比什么都重要。20年前,我写过一首绝句《自题》:“白衣不悔为词客,纸上王侯已自封。谋食舞文由我手,日间屠狗夜屠龙”。“屠狗”谓措理俗事,“屠龙”谓以文字自娱。屠狗和屠龙的变奏,就是我的生态。我想,我师傅也是这样。我们自适着白日屠狗的忙碌,也自适着夜间屠龙的乐趣,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贾平凹、迟子建那类天生的“屠龙专业户”。
在男人中,我师傅属于偏“排场”的一族。陕西话称男人“排场”,是指高大加英俊;用于女人,则谓颀长加漂亮。我师傅身材魁伟,形貌英武,似可“倒拔垂杨柳”。他的夫人是位温婉女性,多年从事艺术表演。我常想,和我师傅偕行,我师娘一定会感到坚实可靠且不无自豪。我和师傅都生长于陕南偏僻山区,也都在人生成长的最关键时段被父母带出了乡村,上学,工作,成家,最终落脚省城。少年的乡间生活经历,奠定了我师傅心地的天然与淳朴;城市的长期“摸爬滚打”,又使我师傅扬弃了“稼娃”的畏葸与固陋;而对文学的爱好,则更提升和扩大了我师傅的精神视域,使他能够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大抵在自己的生态里自得着。至于他的懒散、任性,不能“乘长风破万里浪”、“咬住青山不放松”,大约缘于天性。这就是我师傅。
我师傅嗜酒,我也嗜酒。我们聚饮的间隔,一般不会超过两周。我喝了酒,话特别多,可我师傅喝了酒,比我话还多。我师傅酒后发表时,从不在乎座上客人的身份显微,也从不大顾忌听者的反应,臧否人物,诋诃文章,近于口无遮拦,而他的一些精辟识见,也正在此时才会雪崩石显。有时,我师傅也使气骂座,状若汉之灌夫、明之徐文长辈,使使气对象难堪而无奈。不过,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未有朋友在事后计较过我师傅的这种酒场“耍性子”行为。因为,我师傅从不对任何人“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甚至“心谤腹诽”这个词,都和我师傅毫不搭界。
有一个近年被人们较多使用的词,叫“基因”。科学概念上的基因,大约是指生命遗传中最坚挺的元素。而人文意义上的基因,我宁愿理解成一个人精神上最具统摄性的“经络线”。我具有的基因,何丹萌都具有,但他使这种基因外现的充分与生动,却是我所相形见绌的。所以,他永远是我的师傅。
“活谥”方文慧公
我不止一次说过,方英文的文学才华,每每让我心情颓丧。颓丧什么呢?颓丧我的文字,总不及他的漂亮。
就说上周吧,有朋自远方来,我在大唐芙蓉园的“御宴宫”设席接风,也兼请本地诸友一聚。回家后,想起前些日子,方英文不满时下“复辟”了的丧事铺张风习,遂屡倡对人对己都要“厚养薄葬”。此日我设华宴,宾主醉欢,开销不菲,更觉有践行方说之趣,遂成绝句一首发他:“闾人食尚帝王风,一掷千金御宴宫。厚养从今效方令,死年裸葬亦鬼雄!”句中“方令”,就是指方英文,因他正挂职陕南汉阴县副县长;“裸葬”,典出汉代杨王孙之事。很快,方回短信曰:“妙甚,然裸葬有伤风化;刘郎裸葬,尤令众芳羞睹也。建议末句作‘他年草葬亦酒雄,如何?”我阅之大喜,即从其改。我不得不承认,“草葬”确比“裸葬”妥贴,“酒雄”亦较“鬼雄”更合宴席场景。至于他说的“众芳羞睹”,则是揶揄我“女弟子”多。我愈想,愈觉此语词既智且趣,便忍俊不禁了。
再往前说。今年8月下旬,我的老师费秉勋教授过70大寿,方英文和我都献了贺寿诗。他那首,摹状费公情性做派,极为传神,然语多谐谑,词欠雅驯。我手机上改动后发还他,佯责他“对吾师放诞”,将其戏词如费公打牌之类,皆订之以庄语。他觉得可乐,信手一挥,书法二诗各成条幅,随后在寿费书画展上并壁众目。费公寿宴时,我的同学丁斯对我说:“人家老方的‘琴哑无语来俗客,牌出有品逢高朋写得多好,活句让你改死了。你们学院派写诗,就知道个中规中矩!”听他这么一说,我就竭力回想我的改句,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历来有一个朴素的经验:凡让人不能记住的句子,即非佳句。于是我承认,我点金成铁了。
仍往前说。近年读方英文发我的散文,其中两篇实在是雅人深致之作,我目为质文双美的上品,屡屡推荐给学生阅读。一篇写于前年,题为《嘉树》,清丽而隽永;一篇成于去年,题曰《无非图个闲闲的散步》,舒展且通脱。当初读罢两文,有句赠他:“美文三阅意惶惶,妒火中烧暗自伤。叹我平生习兵法,未曾亮剑已身亡!”这是很真实的感受。说“习兵法”,是因我也曾受过写作的“正规训练”;说“身亡”,则是因我读他文章的上段时,便推测下段该怎么措笔,结果总是他写的,比我设想的更出彩,这使我很气馁。方英文的文章,我并非都服,但这两篇,我不能不服。然而同时,我也不能不自忖:我咋就写不出这样的好文字呢?今年,我主编一部《大学语文》,将《嘉树》收了进去。我想,即使有行家怀疑我作为选者的眼力,也决不会是因为收入了这篇。
还往前说。2005年冬天,方英文和我分别为一家出版社即将再版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写序言。我序完“水浒”,给一位朋友看。朋友说,好着哩。又让朋友看方英文的“三国”序,朋友阅毕,不再吭声。问:不咋样?答:你的好,人家的更好,我不敢说嘛。我求闻其详。复答曰:你的是学者之论,平稳、得体,但不灵动;方是文人之说,读来更觉摇曳生姿。我大笑,戏云:施耐庵是罗贯中的师弟,我是老方的师弟。为师弟者,写得比师兄好不礼貌啊。说施是罗的师弟,纯属即兴杜撰。方英文是我的师兄,却一点不假。27年前,我从商州中学考入西北大学读中文,不久便结识了方英文。他与我同专业,但长我两级。教过他的老师,十有七八也教过我。他是作家,我是教师,术业各有专攻。他把散文写得光昌流丽,小说写得妙趣横生,我弄不过他,这很正常。就像他讲课,大概也讲不过我一样。可是,同给小说做序评,我还是弄不过他,这状况,便让人惨淡了。莫非,有什么仙人点化过他么!
话还没完。方英文给我造成的颓丧感,不仅在于他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还因为他能写得一手好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项。我的弱项之一,是字写不好,尤其毛笔字。方英文的钢笔字写得棒,毛笔字也写得棒。他的行楷,运笔潇洒,风格秀逸,喜欢的人很多。我个人,格外偏爱他的行书体手札。方英文有过毛笔字方面的一点童子功,近几年,愈对各种名帖夜读日临,书艺长势明显,字价随之攀升。看来我这辈子,要想在写字上追赶他,无异于武大和姚明赛扣篮了。
正因为这样,我怀着喜欢又嫉妒的心情,封了方英文一个“谥号”:“方文慧公”。词典上对谥号的解释是:君王时代,帝王将相或名人身后,依其平生作为所给予的称号,意义或褒或贬。因此,我给方英文的称号,属于谑词性质的“活谥”兼“私谥”。我觉得,这个“谥号”赠他,实在合适不过了。
但方英文并非全能,也照样有他的弱项。这弱项就是:他写旧体诗中的律、绝,虽常有雨后风荷般的好句,但大多篇章,都无法尺以传统规则。他和我往来频繁,唱和亦多。我曾为他写诗不合律开脱:“方子为诗,语多机趣,然运字不计平仄,用韵亦不为‘平水所囚。窃谓才盛者,固格律所难缚束矣。”但问题是,方英文写律、绝时,其实是希望能“律己”的。到现在,他未逾此隘,真乃咄咄怪事也。
我还得承认,我对方英文的喜欢和嫉妒,除了因为他的才华横溢,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和一笔好字,让我看了既养眼又颓丧外,还有生活上的彼此性相近、习亦不远的原因。他和我,都属于心地柔软的人,从来不曾做过、也永远不会做出心硬手狠的事情。我曾说,方英文一生,即使想学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所以,我对于他的心情,一向很“重”。而他,不仅是我的朋友,不少时候,还得担当兄长的角色。我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委屈,最愿意和他说,以求在他那里得到缓释。他状态欠佳时,我亦情绪为之不怡。前段日子,我们共同的朋友刘少鸿来西安做胆结石手术,方英文在汉阴,要我速去医院看望,我立刻照办。翌日一大早,他发来短信说:“昨夜遥陪少鸿,胆囊剧痛,几死。”我阅罢,整个上午,心情都不好受。
说“方文慧公”的“慧”,却扯到了“慧”以外的方面,文气不笼了,就此打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