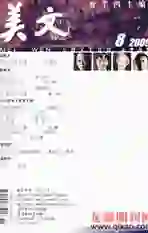我的大学
2009-10-24胡宗锋

胡宗锋陕西凤翔县人,西北大学文化与翻译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翻译学会理事,陕西翻译协会副主席,陕西译协文学翻译委员会主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俄本娜-香槟校园)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英美诗歌、文化与翻译、陕西作家与世界文坛等方面的研究。
第一次见到贾平凹先生是在二十二年前的1986年10月。
当时我在西安交通大学外语系读研究生,我的英美文学课老师,美国明尼苏达州作家、诗人和钢琴家比尔问我当代最有名的中国作家是谁,我回答说是贾平凹。他说自己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这个作家。我说这不奇怪,中国当代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都没有被翻译成外文。比尔问我最喜欢贾平凹的什么作品,我说是散文,其次是小说(我当时真是这么认识的,他的书读多了以后,才又喜欢上了他的小说)。他问我能否将贾平凹的散文作品翻译一两篇让他看看,我说当然可以了。 但我又补充说我的英语水平恐怕还没有达到能传神地表达贾平凹作品真谛的水准。他说你的英语已经够好了,如果你都翻译不了,恐怕世界上再无人能翻译了吧。我知道比尔说的是玩笑话。但我还是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贾平凹的两篇散文。比尔看后说,不愧是我的学生,还是很有眼光的,你所喜欢的这位作家很有沈从文先生的文风。比尔教授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学和英语写作,是一位不通中文的“中国通”,他鼓励我以后可以将自己的事业放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对外翻译和介绍上。他说要翻译一个作家,首先是要研读和了解这个作家,这样才能真正的翻译好这个作家的作品。于是,我产生了与作家贾平凹联系的念头。
当时贾平凹先生已是全国很有名的作家,我一个毛头小伙子人家会给我面子吗,况且我还不知道他的具体联系方式。于是,我就很冒昧地给贾平凹先生写了封信,说我是一个研究生,想研究和翻译他的作品,问能否拜见他。由于不知道贾先生的具体通信地址,我便把信寄到了西安市文联。
没想到一个礼拜后,我就接到了贾平凹先生的亲笔回信,我是那样的激动,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信封,信中云:
胡宗锋同志:
好!
收到您的信很高兴,您如此关照我的创作,我万分感激!
至于翻译的事,我想这样,您是否在空闲之时,能到我家来一趟呢?咱们谈谈,我交您一、二本书看看。因为我不知您的具体要求。
我家住:市南院门大车家巷横巷一号楼一单元七号。
致
礼!
贾平凹
86.10.11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旧保存着贾平凹先生的这封亲笔信,每每看到此信,心中依旧有二十多年前的感动和感慨)
1986年10月13日,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敲开了贾平凹先生的家门。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一点儿也没有名人的架子。他那憨厚、诚实、热情、认真的待人态度以及那双有神的眼睛使我一下子觉得离他很近。他给我让烟,给我倒茶。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来拜访一位全国有名的作家,倒像是到了一位失散多年的亲戚家。他像一位长兄那样询问我的学习和生活,并嘱咐我要在年轻时多把时间放在学习上。他还问了我许多外国作家的问题,只可惜我当时由于学识浅薄,竟有好多东西都回答不上来。从那一刻起,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特别是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否则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再见贾先生呢!
那天我在贾老师家呆了大约有近一个小时,临走时,他送了我他的两本散文集:《心迹》和《爱的踪迹》。
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分吧!二十二年前贾平凹老师的这一颗心和一份爱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句话的含义。正是有像贾平凹老师和比尔老师这些人无私的关怀和鼓励,我才从一位乡村少年成长为了一名大学教授。
1988年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了贾平凹先生的母校——西北大学,终于实现了我做大学老师的梦想。
但我没想到的是,贾平凹就住在与我只有一条甬道之隔的西北大学校园里。我与他的友谊从此真正的开始了。在西大,我又结识了贾平凹老师创办《美文》后从河北挖过来的作家、优秀编辑穆涛。古人云“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这句话说的是人与人交往的高境界。每每在西大遇见贾老师,虽然只是一会儿的寒暄,都会让我激动好几天,也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因为,总会有人问我“呵,你认识贾平凹!”
记得我谈恋爱的时候,我的女朋友问我:“陕西有个贾平凹,你知道不?”我有点得意地说:“当然知道了,不是陕西有个贾平凹,是中国有个贾平凹,他是我的朋友哩。”女朋友说:“吹牛吧?只怕你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你。”我说,“哪天你有时间我带你去见他。”女朋友说:“你就吹吧。”
有天下午,穆涛给我打传呼(当时流行的是BB机,手机还是显示人身份的高档玩意,被人们称为“大哥大”,我一个大学穷教师还用不起)说有个东西要翻译一下,我就叫上女朋友赶到了贾老师任主编的《美文》杂志社。穆涛说:“老贾有几封国外来信,你给翻译一下。”我问,“有没有钱?”穆涛说:“你向老贾要去,他对你那么好!”我忙问:“贾老师在不在?有个美女想见见他。”穆涛知道我说的是我的女朋友,便说:“美女老贾肯定要见,你就算啦。”话虽这样说着,我们还是来到了主编室。见到了贾老师我就介绍说:“贾老师,这是我的女朋友。”贾平凹老师一边和我的女朋友握手一边笑着说:“怪不得好久不见你了,原来是忙着谈恋爱去了。”穆涛在旁边说:“美女的手握一会儿就行了,不要拉住不放,我老兄这人好不容易找个女朋友,再握有人就要打你了。”贾老师笑着说:“穆涛就这一点不好,老把人想得跟他一样,握个手能咋的。”
那天,贾老师给我的女朋友送了一本他的书,并在扉页上写到:送给我朋友的朋友。
2001年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一是我终于结婚了,二是我当上了正教授。人们常说的“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孩子、车子和票子我已经拥有了前二子。在大学里,当上了教授算不了啥,但当不上教授,啥都算不了。其中的艰辛我就不言了,但我结婚确实是在贾老师的关心下完成的。
一天下午,穆涛打电话(这时我已有了手机,因为已经到了连收垃圾的人都有了手机的年月)给我说他和贾老师在一起吃饭,让我也过去聊聊。就在那次吃饭的时候,贾老师说:“胡,你还不结婚,你这个人表面上看来很西化,实际上跟我一样,骨子里是很传统的。结婚有了老婆和娃,日子就更踏实了。”我说:“那你给咱看个日子么!”他伸出手指算了算说:“一个礼拜以后。”我说:“啥?一个礼拜以后,那不行,咱现在都当了教授了,好赖得准备一下吧!”他又算了一次说:“那就是一个月以后了。”并给我说了具体的时间。我说:“可以, 但我有一个要求,我结婚时你得来参加我的婚礼。”贾老师说:“那没问题,参加教授的婚礼还能不去。但你的罚单不要太高了,咱又没多少钱。”我说:“只要你来,那就是最好的礼。”
我结婚的那天,一大早天灰蒙蒙的,《美文》的小夏说:“贾老师,你看你给人家胡看的日子,天都不亮堂么!”贾老师笑着说:“你知道个啥?等一会儿你再看。我看的日子能不好?”果不其然,到了十一点,天开始晴朗了,不一会儿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艳阳天了。贾老师对小夏和我说:“你看, 咱看的这日子!没两下子,敢给人看日子!”
纳礼的时候,贾老师问我:“你那些好朋友纳多少钱?”我说:“我给人家说最多也就是五百块钱,纳多了给人感觉咱不是结婚,是敛财来啦。”贾老师说:“那我就纳六百吧,六六大顺吗!”
有的朋友写文章说,贾老师很吝啬,吃一碗面都不想掏钱,这是幽默和开玩笑。实际上,贾老师的平常心是让人很感动的。
有一次,我和他参加完一个熟人孩子的婚礼,顺路搭他的车,我说到西大附近的一所诊所,孩子在那儿打吊瓶。车到了诊所门口,我说你们走吧,但他说:“那不行,一定要把娃看一下。”于是,他让车停在路边,陪我到诊所去看望打吊瓶的我女儿。诊所的人认出了他,惊讶地对我说:“你还认识贾平凹!”
2007年,一个让人伤感的年份。
这一年,有几位好朋友的父母离开了这个世界。其中就有贾平凹先生的母亲——我妻子的干妈。我有了女朋友以后,有一次去看贾老师,贾老师的妈妈说:“胡有福气,这女子长的很水灵,干脆让我认个干女儿。”我和妻子也很高兴,我妻子高兴地对贾老师说:“以后,我见了你就叫贾哥了。”贾老师说:“你不知道,给人当哥不好当哩。你干妈都把你认了,我还敢不认。”
从那以后,我每年都按旧礼数去贾老师家纳礼。有一年都正月十四了,我还没有去,中午老贾打电话说:“你再不来纳礼,年就过完了。”我忙问:“那你说我啥时来?”(在陕西,走亲戚都要定个日子,要不你去了,亲戚家没人,而亲戚家的人也不能等半天没人来,这一点倒是有些西方化)贾老师说:“明天是十五,你上午来吧。”
贾老师母亲病危的那天晚上八点多的时候,我刚打完吊瓶回家,穆涛打电话让我赶到西安至陕南的高速路口。我接到穆涛的电话后,立即下楼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临走时,我妻子还说你一定要告诉咱哥说没有人看娃,她走不开。老贾的弟弟、妹妹、穆涛和我,护送老人回丹凤县棣花镇的老屋。老贾留在西安料理并准备后续事情。
到棣花镇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两点多了。老人家在家里安详地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三天。我清楚地记得,老人家去世的那天是个星期五,我刚好上完课,穆涛在电话上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今天凌晨老太太走了,你准备一下,咱们中午就往棣花赶。”
坐在开往高速路口的出租车上,我的心里很难受。三天前,我们都还觉得老人家回到故土以后,心情好,病情也就会减轻,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样突然。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出的是我在西大校园里遇到她的情景,她总是很亲切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泪水在不知不觉中流了下来。出租车司机是个有心人,他问我:“这么着急地赶往高速路口,是不是出了啥大事?”我回答说:“家里老人去世了。”
穆涛的车早就在高速路口等我了,我们一行下午两点多赶到了老人家的身边。老贾身着长子的重孝在门口带我们进去,为老人上香磕头。
老贾的妹妹为我准备了一顶孝帽,因为我是干女婿,按规矩着半孝。在陕西的乡下,办老人的丧事时,人们从你着孝的样式就能看出你与老人的关系。小夏不懂问我:“你光戴个白帽子干啥,谁知道你是谁。”我说:“你碎娃不懂,村上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出殡的头天晚上,祭奠老人的时候,是从远房的人先开始上香、烧纸和磕头,直到最后是重孝的儿女。当司仪喊女婿上香、烧纸和磕头时,我和老贾还在老人家的棺木跟前坐着说话。听到喊声,他推了我一把说:“该你去烧纸了。”两位姐夫着重孝,我和他们跪在一起给老人烧纸和磕头。我只戴一顶孝帽,这就是女婿和干女婿的区别。
给老人烧纸是有讲究的,既要把纸烧干净,还要不让纸灰飞起来。连续几天,每遇大的场面祭奠老人家,我都是在火纸堆旁帮人烧纸。其实我知道,这个工作一般都是由村上有身份的长者负责的。我做了,没有人说什么,因为我是戴着孝帽的,那就比村上的人更亲近了。老贾是知道这个讲究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人想叫我出去一下,他只说了一句话:“胡不能走,他要管烧纸呢!”
我很感谢老贾,感谢他对我这个干兄弟的认可。更感谢他让我有机会代我妻子——老人家的干女儿最后为老人家尽一点孝心。
老贾是名人,但也是普通人,他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母亲的去世,让他很难过。他为母亲跪肿了双腿,为母亲哭红了眼睛,为母亲尽到了一个长子和孝子能做到的一切。在为母亲送葬的那几天里,他的话很少,只是默默地按照村上主事人的安排做他该做的事。主事的让他跪他就跪,让他烧纸他就烧纸,让他磕头他就磕头。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和朋友,他一定会坚持将他们送到门外头。人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当母亲入殓的棺盖就要盖上时,他像一个小孩子喊妈妈那样,泪如泉涌,大声哭喊着,把两只手伸向棺中的母亲。这也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这样当着那么多的人,哭喊着要妈妈。妈妈走了,再也不会亲切地叫“平”了。那一刻,房间里男人们呜呜的哭声真的让人的心都碎了。那一刻,孩子们将母亲深深地葬在了自己的心底。
老贾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名人。我为有这样一个干哥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