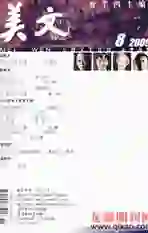走秦岭
2009-10-24李琦
李 琦

李 琦女,1956年出生,哈尔滨人。现供职于黑龙江作家协会。一级作家。出版过诗集《最初的天空》、《李琦近作选》,散文集《从前的布拉吉》、《云想衣裳》等若干著作。
二十多年前,我几乎每周都会有一封至两封信,日夜兼程穿过秦岭,投递到汉中某地。那是个以番号为代表的军营,有两个人在期盼着我的来信。一个是我的妹妹,一个是我的男友。彼时她与他都在军中服役,企盼远方来信成为重要的生活内容。后来,两人先后回至我的身边——妹妹还是妹妹,男友则变成了丈夫。陕西或者秦岭,就这样成为我们共有的一段回忆。
第一次面见秦岭,是乘火车走宝成铁路去成都。那时,我还很年轻,处在凡事只知皮毛的阶段。对秦岭的了解仅限于从书本上学过的那点常识——中国南北方的自然地理分界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我尚不知道这座山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和影响,更不知它曾怎样连结着华夏历史上的绝代风华。车过秦岭时,我的眼睛舍不得从窗外挪开。古道西风,气象苍茫。我看到许多从未见过的景象。大山巍峨,百姓清贫。我看到了小兽一样在山间奔跑的孩子,看到了如从旧画里走出的老人——他竟穿着缀满补丁的土布长衫!那种衣服,我只是在电影或戏剧里面见过。深山老人的衣着和神情,都古旧迷茫,和我们这列从远方而来的列车,和我的一知半解以及兴致勃勃,如同隔着时光隧道。恍然中我觉得自己一脚迈进了从前。那一瞬间,我触到了秦岭一个神秘的按钮。这大山的皱褶之处,还有多少深藏不露的秘密和未知的事物?应该说,是那次经过秦岭的经验,让我对秦岭有了探究的兴趣。后来,我又有过深入秦岭的短暂旅行。所见所闻,均甚为震撼。
在地理学家眼中,秦岭是中国版图上最重要、最奇特、最复杂的山脉。它来历遥远,出身不凡。之所以姓秦名岭,相传是春秋战国时秦国的领地,同时又是当时秦国最高的山峰。周、秦、汉、唐,长安城十三朝帝都的气派和繁华,都曾靠在秦岭那花岗岩的脊背上。别说在中国,就是放在世界,还有哪座山,能够如此被指名道姓地赞叹,被名人雅士诗词吟咏。这浩然秦岭,一边生长奇花异草,珍禽猛兽,一边掩映着古今各路英雄豪杰的履历和传奇。在中华民族心灵的情节里,它一路逶迤,百转千回,有时让人倒抽一口冷气,有时让人感慨唏嘘。
不久前的5月,我去西安参加诗歌节。老友相逢,喜悦难掩。来自长白山脚下的某诗人和某著名主编,说既已来西安,相当于迈进了秦岭朝北的前庭,就孩子似地惦念秦岭。于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善解人意的地主穆涛就带着我们几人,奔秦岭腹地宁陕县而去。此行目的简单,去看秦岭。车子刚开,关于秦岭的回忆便扑面而来。这座在每个人思绪里矗立的大山,先行在我们各自的心念中蜿蜒。尽管它虎踞龙盘已逾千年,此时,却有点像是让我们一行人给想出来的。
当传说中的秦岭,那座著名的“分界线”出现在眼前的时候,竟是那么安静素朴。说云蒸霞蔚?说巍峨耸立?都是,又远不够。最准确的感觉竟是理屈词穷。这声望高耸的山峰,像是一位道行深厚的长者,风度卓然,毫无肤浅之象。而所有的赞美和感叹,在这苍翠的连绵起伏的群山里,变成了一片巨大的静默。这就是名山秦岭的气韵,天降大美,移步即景,壮丽得叫人简直有些措手不及。
一瞬间,不知是山的声响,还是我在耳鸣。反正我发现,面对美,人会有一种生理反应。安静,止语,动作放慢,一切轻巧的赞誉,此刻都有矫揉造作之嫌。
过隧道,走山路,车子在秦岭中穿行,却无任何崎岖之感。经过的那些村镇,房舍田地,井井有条,院落人家,处处洁净。这些坐落在秦岭之中的民房,色彩清净素淡,有的白墙青瓦,有的翘角飞檐。与关中民居明显不同,竟是一派江南韵味。这些流露着细腻和精致的建筑、细节之处的毫不苟且,本身已是注解和说明。无疑,这里居住的都是要强的人、正经过日子的人。想到我去过的一些地方,那些尘土飞扬的村镇,那些潦草邋遢的民居和又脏又乱的公共设施,秦岭之南的民风和习俗,让我们忍不住唏嘘赞叹。说这里是中华民族的龙脉,看来一点不为过。哪怕仅仅是匆匆过客,也让我对这样的地方、这样房舍里的人家,生出敬重和好感。这姓秦的大山,就是不同寻常。一座山丰厚的内涵,就在这如指缝一样的村镇里,悄然显露了出来。
迎接我们的是宁陕县的县长刘云。他中文系出身,面善,文人情怀。谈吐中的胸襟和视野,笑起来满脸清朗的样子,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履历,让我们一见如故。他的接待可谓行云流水,顺畅又诗意盎然。先领我们到清澈的河水之畔,让山风和水气荡涤旅途的疲劳,再领我们围坐在农家庭院,享用地道的陕南午餐——黑米酒,豆腐,腊肉,山野菜——这是食物和胃肠的知心会谈,那么熨帖而富有特色。真是心旷神怡,尤其是当他说:走,带你们去山上,去养护基地看朱鹮!
我是知道朱鹮的。作为珍稀物种,这天性贵重的鸟儿,无法做到自轻自贱。它更喜欢从前的世界,所以当居住的环境日益恶化时,它不仅不再抛头露面,而且懒于挣扎着为生活打拼,干脆准备了最后的撤离。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俄罗斯、朝鲜,这些它从前活动的地方,它基本已消失得杳无踪迹了。人们只能是在照片上、在日本人的和服上,见到这美丽的精灵。
作为一个关心秦岭的人,那一年,当我从新闻中知道,人们在秦岭又发现了朱鹮时,特别高兴。真正的惊鸿一瞥,我把这看成是秦岭的吉兆。
当朱鹮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时,那瞬间的感觉真是奇妙:我看到了秦岭最美的色相——这山林里的鸟儿如此典雅端庄,大方而又矜持。它长喙,胭脂面颊,浑身的羽毛呈贝壳那样的珠光之白。两翅、腹部及尾部,又夹带着柔和的朱红。已经很美,还嫌不够,它们锦上偏要添花,颈后还披着下垂的柳叶型羽毛,形成一个华贵美丽的羽冠。无论体态还是神情,这鸟儿都皇后一样雍容。在宁静的山林,与这等绝美的鸟儿相遇,这是一种缘分。悄声静气中,我看见一只朱鹮正在把略带弯曲的长嘴插入背上的羽毛中。山风吹动它头上的羽冠,柔美的羽毛在微风中微微颤动,真是风流飘逸。一瞬间,我不知为什么,竟匪夷所思地联想到栊翠庵里的妙玉了。
上山的时候,已觉得有些疲劳了。而望着朱鹮的那个时刻,滞重的时光一下变得云朵般柔软。这世界还有这种这稀世珍禽,真是造物主的情有独钟。素衣红颜,朱鹮是鸟类里的名伶。身世不凡又孤高寂寥,不染尘埃,宁愿与嘈杂裂帛。它们一动不动时,像是画在树梢上的静物;而展翅飞翔,则尾羽如扇,翅膀下呈现一片醉人的桃红,修长的脖颈和细腿舒展成一线,其从容不迫的美姿,不愧为是秦岭仙子。它让这安泰寂寥的大山,添了空灵和不同凡响。
它在叫。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朱鹮的叫声。不是那种啁啾,而是率性的嘎嘎而鸣,甚至和乌鸦的叫声有某种接近。它不是鸟类里的播音员,像大人物说话带着口音。静心细听,粗憨之声里,其实带着薄薄的凉意。
枝头上,一对朱鹮正在卿卿我我。它们肯定是一对情侣。负责养护朱鹮的人告诉我们:朱鹮深情敦厚,一旦结亲,彼此恩爱忠诚,安守本分,毫无虚浮之心。没有琴棋书画,却真是花前月下。养育儿女期间,朱鹮夫妻交替外出取食,到达一定时间,无论觅食与否,必回到巢穴,彼此亲热一番,鸣叫抒情而后,另一只再外出觅食。一旦遭遇丧偶,未亡人便只身飘零,不娶不嫁,直到孤独怅然而死。
它们还是最好的父母。宁陕保护站的人观察到:一对朱鹮夫妻孵化了三只宝宝,其一因为体弱不幸去世。父母非常伤心,不舍遗弃,每天用身体温暖已死去的爱儿,直至十天后,才绝望而无奈地将其抛出巢外。
这动人的朱鹮,简直就是住在秦岭里的童话!它们在教堂里宣过誓么?在此之前,我早已一次次感到生命的虚无。而这一刻,带着静穆之气的小小朱鹮,竟美好得让我心乱,纯粹得让人鼻酸。有朱鹮飞过的山谷,这般迷人,让人顿生贪生之感。
离开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人都拾捡了一根朱鹮落下的羽毛。这柔和的带着淡淡绯红的羽毛,如今就插在我的笔筒里。那朱鹮是鸟类,可心性与情愫,已算得上是某种意义上的师尊。我愿意自己的文字,经过朱鹮之羽的摩挲,沾上它那不凡的气韵。
在秦岭的那一夜,一反往日的辗转反侧,我睡得很沉。月光像浓稠的米汤,汩汩滋润了我的梦境。宽大的床上,恍然觉得自己也蜷缩成一只朱鹮,夜卧枝头的巢穴之上。这秦岭深处,氧气之足,让人如晕似醉。在中国南北分界的地方,我的梦安稳踏实,有了一种被安慰的舒展,也有了一种被引领的觉悟。
离开的那天早晨,天气晴好。这秦岭南麓的翠峦叠嶂中,白云袅袅。想到这里至今繁衍生息着如金丝猴、熊猫、羚羊、大鲵等珍贵的野生动物,想到自古以来,这里便是中国古代隐士聚集的地方。千年烟云散去又聚拢,这草木葱茏的空气里,我觉得依旧凝聚着一种高蹈奇异的气场。
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人还未走,念想已经生根。连我们的车好像也不想走,车胎兀自就坏了。换车胎的时候,我们得以坐在城关镇一位香菇养殖户的院子里,悠然看远近山景,说谈宁陕的现在和未来。女主人和我见过的黄土高坡上的陕北女子确实风貌不同,一头披肩直发,眉目清秀,素淡羞涩。她正在吃饭,米饭,油菜,腊肉炒菌,连饭食也颇具陕南特点。她给我们每人倒上一杯茶,客气,礼貌,声音轻缓,并不多言。温婉的笑容和门前的翠竹,又一次让我相信,这南北分界,真不是一句空话。居住于此的人们,兼有北方的质朴和南方的细致。这秦岭,真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大书,而我们,不过是刚刚掀起它的封面。
离开时所有人都意犹未尽,这也正是告别的最佳时段。时间短暂,印象久远。这竟像一句广告词了。再见,秦岭。云雾缭绕的山峰,童话般的朱鹮,甘醇美味的黑米酒,香溢唇齿的宁陕豆腐,清新得让人感激的空气,刘云县长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路边人家温和的女子,宁陕境内洁净的房舍庭院,门前的修竹,杯里的清茶,还有那胖墩墩带着一堆儿女从容觅食的花母鸡,以及那干脆算是家中人口的小黄狗,这些元素合起来,就是我对宁陕温厚绵长的回忆,就是2009年5月,一个外乡人带走的秦岭的味道和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