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能以弱化国家权力为前提
2009-0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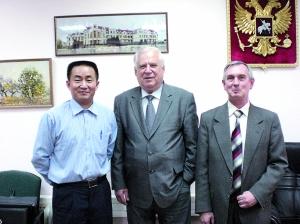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谈教训
本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 李亚龙 本报特约记者 王伟平
本报记者(左)与雷日科夫(中)及其助手合影。
“任何国家的任何改革,都不能在弱化国家权力的前提下进行”——一位年近80岁的俄罗斯老人在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句话时,表情凝重。这位老人就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他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苏联最后一任部长会议主席(后改称苏联总理)。在原苏联的众多国家领导人中,雷日科夫对苏联解体的研究最为深刻。他的著作《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在中国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近日,《环球时报》独家专访了雷日科夫,他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他眼中的大国兴衰。
苏联解体的最大原因是内耗
环球时报:您是苏联后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能否分析一下苏联解体的原因?
雷日科夫:这些年我写了几本书,试图客观地分析苏联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书在中国最有需求。去年我到上海、北京,参加我的著作中文版的发行仪式。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同志没有隐瞒这一点:他们想通过我的这些书来分析究竟发生了什么。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段艰难岁月,损失很大。而中国是一个大国,也存在各种矛盾。所以我理解,读过我书的同志是希望不再重复我们的错误。
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客观原因可以导致国家的解体。有些人认为所有帝国都会崩溃,举出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等作为例子,但这些都是臆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成为帝国。大英帝国近40%的收入和财富来源于殖民地。(苏联)有15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作为主要的共和国,拥有50%的领土、人口和经济潜力。与需求相比,我们更多的是给予。把我们和那些帝国相提并论,实际上是某些人想为我们的崩溃找理论基础。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首先,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来自俄罗斯的政治对抗。叶利钦带领自己的团队掌握了权力,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权。历史没有假设,我想,如果那时对叶利钦说:好,让你成为苏联总统,那么他可能不会去走摧毁之路。这是政治斗争,这场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政治斗争最终以他们的胜利而结束。但是,他们的胜利是建立在苏联解体之上的。当俄罗斯宣布自己是主权(国家),其他共和国开始分崩离析,因为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在看俄罗斯如何行事。如果俄罗斯不采用这样的方式,我认为除了波罗的海(国家),我们是不会失去苏联的。我常常想,如果在今天的俄罗斯出现像叶利钦团队所做的事情,那么他们最少可能要坐15年的牢。
其次是民族的自我意识问题。我认为,那时苏共没有真正分清民族自我意识和需要更正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界限,这是不同的东西。我们有100多个民族在苏维埃政权期间拥有了文字,此前他们甚至连字母都没有。(现在)民族主义开始高涨,比如说乌克兰,他们说是他们供养了俄罗斯。我们想说服大家,相反是俄罗斯养活了乌克兰。乌克兰人却在柱子上贴着(告示)——是俄罗斯把我们的咸肥肉拿走了。
第三,美国一直在反对苏联,也包括东欧国家,但是战后最主要的反苏者是美国人。美国人一直在考虑如何摧毁苏联。我估计,你们也知道杜勒斯1945年讲的话。当时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在斗争中无法击败苏联。他直接提议:战胜苏联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要逐渐瓦解、腐蚀它的价值观、腐蚀它的精神,让它的文学、艺术走下坡路。这是一个摧毁我们的一整套计划。他们就是按照这套计划来行动的。杜勒斯考虑会用20年时间,但实际上用了40年。
环球时报:您认为应该从苏联的解体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雷日科夫:首先,不要重复我们采取的(那些政策)。一个国家永远都不要原地踏步,就像一个有机体,应该发展、生病、老化并需要治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一个国家的机制不可能100年都不变,没有改变这是不可能的,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是这样的。但是,如何治疗和改变,应该深思熟虑。而不应该向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顾问说的那样,一切彻底摧毁,然后再重建。我觉得,所有的改革都应该是渐进的,绝对不能采取革命性的方法。马上做一切,只能导致崩溃。
第二,根据我的研究经验,任何国家的任何改革,都不能在弱化国家权力的前提下进行。1985年我们从经济改革开始,我强调一下,仅仅从经济方面开始。从来就没有提出过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进行改革。大约过了两三年,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就提出,应该改变社会体制。(结果是)社会体制改变了,党不再起领导作用。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把党摧毁了,因而出现了混乱。在这方面你们是个例外,我们知道,你们的党起着领导作用。因此,希望不要考虑在改革的同时放弃对国家的管理,不然会出现难以想象的局面。
没有能够影响俄中关系的乌云
环球时报:能否谈谈您年轻时对中国的印象?
雷日科夫:我曾在乌拉尔地区读大学。当时,有成百的中国大学生在乌拉尔工业大学读书。他们的学校非常好,中国学生比我们的学生要更为刻苦。后来,我进入乌拉尔机械厂工作,我们的工厂非常大,整个工厂装满了要供给中国的设备:冶金业设备,挖掘、钻探设备等等。你到任何一个车间,到处都写着“中国”。几年之内的工作都专门针对中国。在我们工厂,除了大学生外,还有中国工人:车工、铣工等。他们主要向我们学习,希望掌握专业技术。我本人就认识几个中国工人,对他们有非常好的印象,他们守纪律、勤奋和专心。周日的时候,我们一起喝伏特加,吃饺子。以前我们认为饺子是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特产,中国工人来了之后,才知道饺子是中国的。我们与中国朋友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现在的中俄关系?
雷日科夫: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们对你们的政治体制、商品流通、苏中所有可能的接触等等都感兴趣。其中一个原因是你们已经积累了六七年的改革经验。我们研究后认为,和我们急躁的、想一夜成功的改革相比,你们的改革更为专业、更为深思熟虑。您知道,经济具有惯性,凡是惯性的东西,总是运转缓慢,对此应该承认。我认为,你们选择的改革风格是正确的,对此我很赞赏。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关系良好,我没有看到那些能够影响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的带有雷电的乌云。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回到20年前的那种各奔一方的关系中。所以我们应该做一切能够(使关系)继续发展的事情。中国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我经常和中国使馆的人见面,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我也知道,你们将今年经济发展指标定到8%。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也能够做到这些。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正常。至于那些建跨江桥、输电等不愉快的事情始终会存在的,未来也会存在。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国家领导存在,目的就是疏通这些瓶颈。因此,我祝愿你们有大的成绩。也希望我们始终有这种好的关系。
我喜欢没有保镖的生活
环球时报: 1990年12月,您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辞职,退下来之后是否感觉很轻松?
雷日科夫:如果有人对你说,这一切很轻松,千万不要相信他。哪怕你没有被关进监狱、甚至没有被赶走。比如我,是自动辞职的,也一样不轻松。你昨天是国家领导,今天什么也不是了,你就是一个普通公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不太舒服。我知道很多例子,包括我们的领导人,包括我会见过的外国领导人,我以前的同事,所有的人都生病了,只是病的程度不同。比如我熟悉的俄裔法国总理贝雷戈瓦,他1993年饮弹自尽。有些人感觉会好些,我对自己说:你是从哪里走向权力顶峰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母亲几乎是文盲,哥哥是一名矿工。也就是说,来自于普通人家庭,现在又回到普通人之中。应该像大家一样,习惯于现有生活。我也就开始习惯、并很快习惯了。
现在也有很多诱惑,让我到什么地方工作。我说,我哪也不去。不是因为年事已高,哪怕我再年轻20岁也是一样。我喜欢这种没有保镖的生活,鬼知道他们保护的是谁,为谁保护我、还是为了我保护谁,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很快适应了正常人的生活。我可以在没有保镖的情况下安静地散步。(退下来)开始的几年我没有工作,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我自己决定要参加杜马选举,并两次当选,前后8年。我现在是无党派人士,不属于任何党团。我在杜马工作了8年,在联邦院工作了5年,也就是说,我在议会已经工作了13年。我认为,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情。在这十几年中,我没有去追求更高的权力。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对我们国内的生活,我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