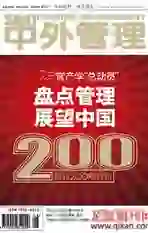李维安:危机涌动时,董事会在哪里?
2009-08-25邓勇兵
邓勇兵

率先提出“中国式”公司治理——行政型治理的概念,进而提出应向经济型治理模式转
型的李维安教授,如何看待在经济危机中似已天塌地陷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不仅金融危机,而且治理危机
《中外管理》:您认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治理结构的问题,还是外部监管体系的问题?
李维安:华尔街基于“问题”资产的过度创新,背离了资本市场的根本使命和诚信法则,也违背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金融机构治理在其逻辑起点上就出现了根本的偏离,其相应的治理安排必然是畸形无效的,包括:刚性且无后顾之忧的高管激励机制、对公司重大决策行为风险的预判和控制力低效的董事会等。
而此时,作为公司治理重要外部机制的监管机构,在对“问题”产品的监控上也存在缺位、滞后现象,从而造成了市场虚假繁荣背后巨大风险的积累。这些风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风险,而是金融机构治理风险。
另外,评级机构原本为确保债券等的信用度而设立,却在利益的驱动下丧失了中立性,“随意”给那些所谓“创新”债券盖上5A标志,导致治理风险极度加剧。
正是因为治理风险的积累、引爆、释放,最终导致了这场震惊全球的金融海啸。显然,此次危机和几年前的“安然事件”从根本上看如出一辙:缺乏治理保障的金融创新,最终导致了空前的灾难,也再次凸显了“繁荣”背后的金融机构治理风险问题。
《中外管理》:那么,从公司治理运作层面来看,董事会在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李维安:在内部治理制度的安排中,董事会是一个关键要素,因为董事会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对公司重大决策行为风险的预判和风险的控制。一旦发生危机,董事会应具备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这次危机中很多公司出了问题,包括雷曼兄弟、通用汽车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董事会缺少对系统风险的把握。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应把握什么?把握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控制整体和系统风险。为什么出了问题股东诉讼要告董事会?就是因为它没有把握好这类风险的底限,以至公司破产或受到重创。
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样作为大型金融机构的苏黎士保险,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苏黎士保险的董事会中,所有成员都是外部董事,包括董事长。其最大特点就是董事会成员与管理层完全分开,没有任何交叉,做到了决策、监督与执行的分离。董事会成员在决策前与管理层成员充分沟通,但独立决策。最后,其董事会认为金融衍生品风险太大,决定不参与有关业务,因此躲过了这次灾难。因此,独立性以及规范的运作机制是董事会改革的关键。
反思英美治理模式
《中外管理》:那么,您觉得在今后世界金融机构治理模式的改变上,在哪些方面需要进行改革?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李维安: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以为榜样的“英美模式”发生了很大问题。这就启发我们认识到:首先,公司治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美国的模式多少年了?它还有大问题,我们也是一样。这是猫捉老鼠的过程,出了问题再完善再解决,又会出新的问题,它是一个伴随企业始终的过程。
其次,我们要考虑到,所有的管理措施和治理措施都是有双面作用的。比如说薪酬制度的激励效果与约束影响。而怎么样趋利避害,是我们要注意的。
再次,我们看公司治理,不能光看它的董事会里独立董事有多少人,或者光看它的结构,而要看它是不是有效的。如果公司都快垮了,都还没有采取防范措施,那么这就是无效的。
英美模式是在分散的股权结构和发达的证券市场背景下形成的,拥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内外部治理安排。从实践看,它也有一定问题,例如刚性且无后顾之忧的高管激励机制等,这些都是今后公司治理改革中应该重视的问题。
高管限薪是双刃剑
《中外管理》:刚才您提到了高管激励机制的问题,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包括美国、中国,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发布了高管限薪令,您如何评价限薪令?
李维安:薪酬机制本来是用来激励高管人员的,以期实现利益趋同、降低代理成本的目标。然而,此次危机中,金融机构高管收入的刚性,没有后顾之忧的薪酬体系,助长了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干好了,拿得非常多;干不好,也很高,而不受惩罚。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这个不合理的薪酬体系是导致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来看高管限薪令,不难发现:在短期内它是有正面作用的,但长期而言是无效的,不应该提倡。如果长期提倡,就假设你给他规定了薪酬的最高额度,而实际上薪酬机制是各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来确定的,不能千篇一律。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高薪、限制高管自我利益机制,可能意味着约束机制强化了,但同时也意味着激励机制会受到影响。而且,长期来看,政府的作用要逐渐淡化,最终由董事会来决定高管的薪酬,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一样。搞限薪,统一薪酬,对市场经济一定没有好处。不能因为美国出问题了,我们就走另一个极端。
要结束治理模式的摇摆
《中外管理》:那么,您觉得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主要方向是什么?
李维安:我在1996年就提出,中国式公司治理必须逐步实现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即,从以往的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合,各级政府部门直接监管企业运营的政企合一的行政型治理,逐步向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分开,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下,外部通过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和法律法规,内部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对企业实施监管的经济型治理方向转型。
然而,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经济型治理体系的缺失,企业常在“内部人控制”与行政型治理之间摇摆。中国企业行政型治理放松的同时,经济型治理却未及时确立。由此,行政型治理一放松,企业常陷入内部人控制状态。而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强有力的行政型治理。中国企业的薪酬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行政型治理一放松,部分企业高管薪酬就“井喷”,偏离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企业的实际绩效水平;而面对这一问题,又要以政府的限薪令来应对,董事会却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而经济型治理模式下,主要靠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是董事会,很多权力在董事会。我们国家现在都是上面任命好了再过渡到董事会,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中广泛存在。刚才说到的薪酬、资源配置等,这本来都应该是董事会的事,需要依靠这个内部机制来发挥作用。而外部治理,则主要靠市场来实现,包括:职业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竞争市场等,都不能靠政府来安排。
李维安对《中外管理》说
《中外管理》杂志各方面都不错,包括这次采访主题也是如此。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我们也做刊物,《南开管理评论》,创刊的时候杨总也专门过来,是我们的编委之一,我们当时借鉴了《中外管理》的一些经验。《中外管理》主要往应用性方面发展,而《南开管理评论》往学术方面发展,为工商管理提供一个学术平台。因此,我们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为补充。再一个,我参加过《中外管理》的恳谈会,影响力比较大,感觉不光是这个杂志本身,而且集合了各界的力量在发挥影响力,这一点我印象比较深。管理
责任编辑:杨 光
格言:治理风险的积累,最终导致了这场震惊全球的金融海啸。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应把握什么?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