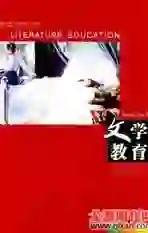《那树》对生命与生存的哲学追问
2009-07-24薛城
薛 城
王鼎钧先生的《那树》是台湾散文的名作,曾得到过许多散文大家的赞誉,因其所独具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被选入初中语文教科书。作为经典的散文作品,《那树》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历久弥精,反复细读与品味,一种难以诉说的感受涌向笔端,这篇散文所具有的鲜明的寓言性叙事风格,使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灵韵。文章通过对一棵常年造福于人类的大树最终被“屠杀”的故事,揭示了现代文明对大自然的破坏与攻伐,表达了作者对人与自然的深层思考。
《那树》首先抒写了大树不凡的外貌:“那树有一点佝偻,露出老态,但是坚固稳定,树顶像刚炸开的焰火一样繁密。”“那的确是一株坚固的大树,霉黑潮湿的皮层上,有隆起的筋和纵裂的纹,像生铁铸就的模样。几丈以外的泥土下,还看出有树根的伏脉。”远看、近看,粗看、细看,大树都是与众不同的。像寓言故事中饱经忧患的老者、智者。与众不同的外貌意寓不同的生活经历和高贵的品格。沧海桑田,世事变迁,那树经久屹立,抗御了大自然的各种灾害,幻化成了古老而茂盛的生命旗帜。它绿化大地,荫庇百鸟,护佑人类,无条件默默奉献着。那树是作者情感与希望的某种寄托和外化。因而它在文中,从头到尾被赋予了一种优美的诗意,一种深刻的意象,它代表着一种古老的田园风光,一种平和、安详的精神。可以这样说,大树就是人与自然相处的一种象征。大树不见其利己,只见其利人,默默庇护芸芸众生的精神,更是一种守望,这种守望既是精神上的,更具有一种原始的执着与美丽。
大树的生存环境遇到了现代文明的攻伐,“所有原来在地面上自然生长的东西都被铲除,被连根拔起。只有那树被一重又一重死鱼般的灰白色包围,连根须都被压路机辗进灰色之下”。但大树依然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没有抱怨,没有退缩,反而“绿得更深沉”,“让下车的人好在树下从容撑伞”。环境的改变没有改变大树诗意的生活。大树把人们的生活点缀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
面对工头和公务局的科员不怀好意的“端详”,“他依然绿着”,面对他施恩过的人们的误解“为什么这儿有一棵树呢?”那树依然屹立不动,连一片叶也不落下。“那一蓬蓬叶子照旧绿,绿得很。”很明显,大树意寓一种坚守的道德情操,虽然这种坚守带着浓浓的悲剧情怀。因为“树是世袭的土著,是春泥的效死者”。大树明知自己将被砍伐的悲剧结局,但他仍然愿做土地一生一世的守护者。如果说过去的守护不乏田园牧歌般的诗情画意,但面对工业化、城市化的攻伐,大树的守望更多的带有一种寂寞的、凄婉的、哀伤的、无可奈何的悲情。
就是被人类“屠杀”后,大树仍把自己的最后的绿色献给了这个世界。“早晨,行人只见地上有碎叶,叶上的每一平方厘米仍绿着。它果然绿着生,绿着死。”大树是人类的恩人与导师。每读这篇文章,总让我想起电视连续剧《狮子王》,在丛林之王辛巴的成长过程中,每次遇到危境,总是大树爷爷指点迷津,大树爷爷还送给辛巴一面斗风,使它在危险的时候能够隐身,对于我们人类,大树所赐予我们的不是比这还多吗?轰然倒下的大树了结了人类生活的最后一层诗情画意,引发了作者对人类和自然生命与生存的深邃的哲思。对大树最终命运的描述,隐含着作者愤恨、悲哀、幽怨而又无奈的心情。
但是作者决不是要求我们回归到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思索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人类社会中间各种形形色色的摩擦时,应该具有一种健康、智慧和追求,和谐地向前发展的心态……”①作者就是要引发我们思索在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中,人的精神困境和尴尬的地位,引导我们思索生命与生存的深层内蕴,让我们追求更为人性而理性的生活。人与树的关系,说到底,其实就是人与自然、城市化与生态保护、古老的道德理念与现代文明心态之间既为矛盾又互相依存的哲学关系。对于因人为原因而葬身的大树,作者是充满哀伤和缅怀之情的。人们何时才能不干这灭树毁绿的傻事?爱树就是爱人类自己啊。
对大自然的挚爱,对人生的感悟和人类文明深切的关怀。使全文的气氛与节奏,就像一首悲情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又像阳光炽热的夏日午后,独自的鸣蝉,深邃而安静。它是生命与生存的哲学追问。
这样的阐释和启示是作者恰切地借助于寓言性叙事的手法。“他将一般的寓言象征,改造和廓大成世界本体的象征,……在想象的方式上,他还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输入以前,就不时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抒情中常常错杂进奇警的幻觉和错觉。”②作品鲜明的寓言性叙事不可忽视,对这种寓言性叙述的细品和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作品的主题。“散文是人类精神生命的最直接的语言文字形式。”③《那树》主要由作者以第三人称作全知全能的叙述。文中有几处以别人之口引起的话题:
“认识那棵树的人都说,……总有人到树干上漩涡形的洞里插一柱香呢!”
“与树为邻的一位老太太偏说她听见老树叹息,一声又一声,像严重的哮喘病。”
“老树是通灵的,它预知被伐,将自己的灾祸先告诉体内的寄生虫。于是弱小而坚忍的民族,……表示了依依不舍。这是那个乡下来的清道妇说的。”
这些描写为作品创造了一种悲壮而又神秘的气氛。意寓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屠格涅夫曾经说过“我们都是自然的孩子”。自然孕育了人类,哺育着人类,从古至今一直荫庇着人类,但人类对自然没有回报之心、感恩之心,甚至连一点敬畏之心也没有。人与树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整个人类生命与生存的哲学意义。作品足以引起我们内心的震撼和深思。那些被“高贵”的人类视为无生命的动植物却有情有义有爱,与此对比,人类倒是鲜情寡义,甚至忘恩负义。
敬畏自然,善待自然,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们才能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一切成果。
注释:
①林非:《<当代散文精品1998>序言》,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楼肇明:《谈王鼎钧的散文》,见《王鼎钧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③林贤治:《论散文精神》,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薛城,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教育硕士,江苏徐州市中学语文兼职教研员,徐州经济开发区中学教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