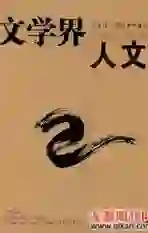论北村小说的文本结构
2009-07-10张小平于京一
张小平 于京一
摘要:北村小说的文本结构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样态。他采用暴露叙事的方式,元小说的痕迹清晰可见。文本的空缺导致其文本状态呈现四处散落的标志性特征。暴露叙事与文本空缺最终导致了北村小说情节的纷纷扬扬,其最终完成的既是对读者阅读期待的伏击与挫伤,也是作家本人煞费苦心劳作成果的轰然倒塌。这一状态是对当下本真生活的文本投射,而投射的背后是平面化生存状态下的深度精神探索。
关键词:文本;叙事;逻辑;情节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2-016-03
作者:张小平,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讲师,文学博士;江苏,南京,210003/于京一,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山东,济南,250100
缠绕迷恋的语言和花样迭出的叙事使北村小说的文本结构很难呈现出清晰规整的面貌,更难以定义为循规蹈矩、铁板一块,小说文本整体呈现出支离破碎、零乱不堪的样态和特征。
一、暴露叙事与元小说
作为新潮作家心仪的叙事策略,暴露叙事曾经获到极度得推崇,某种意义上说,暴露叙事甚至成为新潮作家共同的身份认证。所谓暴露叙事,就是指在作品中“叙述人或者作者常常公开自己的身份,甚至谈论小说的叙述技巧,将小说家自己看世界、表现世界、蒙骗读者的家数(叙事成规)全给抖了出来,叙事行为、叙事方式本身被主题化了,成了被谈论的对象。小说在此情况下就成了关于故事的故事,关于叙述的叙述,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种暴露叙事行为的小说又称为‘元小说……”[1]。北村作为新潮一代中醉心于形式实验的主将,自然更热心于对暴露叙事的运用。小说《玛卓的爱情》的文本主体讲述的是玛卓与刘仁悲剧性的爱情与婚姻,但小说的开头与结尾却类似话剧的序幕与尾声,叙述者在开头告诉我们说:“伙计,我要跟你讲的故事已经开始了,……”这是个悲惨的故事;在结尾处又自我辩解地说道:“唉,这个故事太长了,你一定不耐烦了是吧,伙计?它的确太长了,而且让人难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显然,这里的“故事”与“千真万确的事情”之间难以划上等号,作者的用意既是在讲述故事,但叙述的同时,又产生了叙事逻辑上的分歧与冲突。这种暴露叙述的方式,使荒诞的阅读感受充溢其间,在一种常规发展的逻辑推理中暴露出种种不可信的因子,愚弄本身的浅薄把戏又在相反的维度上将读者引入荒诞故事背面的巨大思考空间。如果说《玛卓的爱情》对暴露叙事的运用还有些含蓄的话,那么到了《孔成的生活》则变得直接而大胆。小说在开篇不久就写道:“鉴于我的慵懒的习性和日益衰退的笔力,以下的记录不是一篇成熟的小说,它在时序上的混乱和遣词造句上的失误,使它成为一则杂乱的采访手记,我对霍童和孔成的陌生更使它在叙述上出现漏洞。我唯一能做的是,用几个俗常的词汇分开它的段落。所以,现在看到的是一篇未定稿。为了讲述上的方便,我暂时记住了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三日这个时间”[2],这到底是小说还是采访稿,是完成品还是未定稿,所有的一切在叙述者顽皮而认真的话语中瓦解了,这一叙述方式是对真诚的阅读态度的调戏,也是对认真的生活态度的玩弄,这一调戏和玩弄的背后,隐藏着现实真实与文本真实的巨大张力,这一张力实际上是现实本真状态与理想生活幻境的真切反映。在接下去的叙述中,关于这篇东西的真假和“我”的身份也是歧义丛生:如“到现在为止,我与这个女人的奇遇已经显得十分难堪,如同我那些胡编滥造的小说中的一个枝节,没有原因、荒唐和不着边际”[3],叙述者时常站出来提醒读者这是“我”写的东西,“我”究竟是不是稳固的第一人称,“我”所写的东西究竟还能不能称其为作品,这一作品是真实的还是作品中的填充物,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交叉缠绕的。混乱不清的逻辑穿插其间,歧义丛生,令人如置云里雾里,使人玄想不断。另外,小说中唐松为了缓解孔成的情绪,提议一起去拜访一个叫“康洪”(注意这也是北村的本名)的考古学家和作家,而我们知道这就是小说的叙述者“我”,但这里叙述的冷漠给我们的感觉是这个“考古学家”似乎并不是“我”,于是,考古学家,叙述者“我”与康洪之间出现了身份模糊,三者分辨不清的身份关系,将所有的清晰叙述脉络揉成一团,分不清枝干,小说固有的真实游离于文本内外,隐现在开放的文字游戏中。而且,小说的结尾部分两次提到“我”在写一篇关于孔成的小说,并且已经成书出版,等等。所有这些谜团都是作者玩弄暴露叙事的结果。这样的把戏北村在《家族记忆》中又一次故伎重演,小说中的家族直接就命名为“康家”,出现了大量康姓人物;小说在考证家族历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康洪”的名字,并用“我于1985年从厦门大学毕业,后来当了作家”(北村的情况确实如此)这样的话来证实。这篇小说很大程度上给人的感觉确实是一部关于“康家”家族历史考证的文章,甚至也出现了一些考证式的术语,如“我一直对上述这段历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为整个过程跟儿戏一样。父亲在讲述四个祖宗的死亡时,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平静,其中有一个还是他的亲爷爷”,“如果不是父亲对我亲口所述,我很难相信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迄今,我无法对这段历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让我迷惑不解的是,这八兄弟被杀的理由在我父亲的讲述中语焉不详”。小说采用断片拼贴的方式,任何一个断片都可以看作是真实的,但是连接起来的断片,却呈现出无尽的虚假性。整体的破碎来自于真实的断片,张力的呈现来自于文本自身的显而易见的逻辑矛盾。
我们看到,这些作品通过暴露叙事的运用将小说与现实、虚构与真实搅和在一起,表面上在暗示读者这是真的,实际上根据理性和小说常识我们获得的信息却是:这些都是假的,是作者的虚构。暴露叙事不仅使小说充满了迷幻与智性的交锋,耐人寻味,而且也使小说的结构变得突兀崎岖、旁逸斜出。
二、文本空缺的四处散落
阅读北村的小说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和高超的粘贴本领,否则将会陷入纷乱的话语中难以自拔,因为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过程中,往往会由于情绪、感觉、思路等的波动而出现话语跳跃或中断的现象,留下无法填补的文本空缺。小说《孔成的生活》中,关于孔成的死因,他的尸体显然是最重要的线索,然而“奇怪的是,当处理后事的人抵达杜村时,孔成的尸体已经不翼而飞了”,尸体哪里去了?是被什么人故意埋藏了吗?出于什么目的这样做?孔成真的死了吗?这个关键的问题化作一个巨大的空缺横亘在小说中,而整部小说在尸体缺失,或者说在孔成生死未明的情况下调查他的死因,未免显得有些荒诞无稽。“我”在查阅有关霍童地震的材料时,小说写道:“我在万坚所撰的这篇唯一真实记录事实的报道下方,看见了一个不知名的查阅者批注的一行小字:他们能逃亡到哪里去?”无论如何,这行字的语气在整个文本中很像是出自孔成之口,但“地震发生在六月十三日,这与孔成自杀的时间不谋而合”,那么,这行字的书写者是谁?他写这行字的用意何在?小说又一次留下了一个关键的空缺。作者采用一种真实的逻辑推理的方式展开文本的建构,却在文本逻辑建构即将成型的时候,由于文本的空缺造成逻辑与现实的断裂。按照小说的叙述,孔成在自杀之前曾连杀七人,然而小说后来的叙述却告诉我们这七个人并没有死,“我采访了孔成的七个被害人,让他们站在各自的角度,回忆一次杀人过程”,而且,这七个人里面居然包括小说中的案情叙述人也就是孔成的同学兼朋友唐松和董云;然而,在他们的回忆中却无一例外地缺失孔成杀人的关键性细节,“……他向我走过来时,杀机已经完全从他塌陷的眼睛中显露出来……”,这是唐松的回忆,但一个省略号却掩藏或抹去了事实的真相。正如小说接着写道:“在唐松和董云巧妙而富有文采的叙述中,他们忽略了如何机智地躲避杀身之祸从而逃生的重要枝节,我们无从知晓孔成使用什么凶器来实施谋杀”,在这里,叙述者自己揭示出了空缺的存在,但“我”却没有继续就空缺的补充做出任何努力。
这种情况在小说《谐振》和“者说”系列中也俯拾皆是。办公室里主任、刘半仙等人屡次提出要给“我”讲一下“我”父亲的事情,但却总是没有下文;“我”父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为什么搞得如此神秘?我们终究不得而知(《谐振》)。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和清晰的逻辑推理,林展新的死因始终没有水落石出,而叙述者“我”却在小说的结尾宣布事实的真相已经大白,实在让人不知所以然(《聒噪者说》)。这一缺失性的文本建构,将读者常规的阅读习惯进行了无情的肢解,它使读者填补空缺的想法和可能演化成一种荒诞,将一切积极参与的意识和理念无情地置于嘲笑的对立方阵之中。
文本空缺的存在使北村的小说在结构上难逃琐碎与迷离的宿命,我们只有发挥想象的力量才可能领会他小说的旨意所在,这无疑对传统小说追求结构的完整构成了强烈的挑战与暴动。
三、小说情节的纷纷扬扬
暴露叙事与文本空缺最终导致了北村小说情节的纷纷扬扬,它们完成的既是对读者阅读期待的一次成功伏击与挫伤,也是作家本人煞费苦心劳作成果的轰然倒塌。小说《劫持者说》写的是一个“追踪”强奸犯的故事,原本是警察马林追踪罪犯牛二,而作为追踪者的马林却莫名其妙地成为别人的追踪对象,他老觉得自己背后有人,油坊里的朱三竟然把马林当作偷油贼绑了起来。而牛二与朱三居然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是否是同一个人?到底谁是强奸犯?这始终是个迷,因为牛二枪杀了朱三,而他自己也自杀于“刘记客栈”。小说虽然暗示是村长——即朱三在刘巧的屋子里鬼混,但朱三的身份在此却发生了迷离的歧义,因为据胡鲶的父亲回忆村长早在五三年就死去了。小说的文本就是这样,不仅人物与事件扑朔迷离,而且时间也出现了停止、倒退与交叉。钟表店里的表和牛二的怀表都无缘无故地停了,他们也不愿意为找回时间付出无谓的代价——金钱;牛二甚至觉得这里的情形“与一九五三年的情形相类似”,“有些时候,人们会在一刹那以为自己到过这个地方,遇上过同样的情景,说过同样的话”,时间仿佛变得毫无意义。这种时间的犬牙交错直接使小说的情节像雪片一般到处纷纷扬扬,即使被读者侥幸逮住也会顷刻融化消失,无从把握。小说文本像是一些生活与侦探经历碎片的粘合,这些碎片把相距遥远的人和事连接到了一起。充斥在文本之中的事件,既看似真实,相互之间又产生了梦幻似的交叉和重叠。于是,真实与虚幻,梦境与生活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起,并且互相之间亲密地交谈着,捉着迷藏。而小说中人物的身份也在这种游戏般的叙事中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换,他们彼此之间既互相佐证,又互相解构。因此,当读者满怀欢喜和侥幸地认为对文本的叙事已经建构起了一个基本框架时,叙述者稍做手脚便使其砰然粉碎,让他们费尽心机的努力顷刻间化为乌有。
而《聒噪者说》则进一步凸显了语言的表述与明确表达之间的悖谬。小说通过警探“我”对一个死亡案件的调查展开,聋哑学校校长林展新(其实他是专案组组长)死时手中拿着一本《哑语手册》,他是为了调查神学教授朱茂新的历史问题而来的,而直到死,他对教授的情况仍然一无所知。在小说中,我们一方面被各种“聒噪”的言说所淹没,关于这个案件及其相关人物谣言四起,所有的事情仿佛一堆被揉碎了的材料,在小说当中任意地粘贴组合。处于不同时间的人物在同一个时间里碰面交往,令人匪夷所思,这便导致了前后情节的相互解构,解构成了文本建构的一种手段,解构也成了文本本身的思想主体。另一方面,小说又以一种“打哑语”的方式使读者无处下手,找不到进入的路径:林展新对朱茂新一无所知,而朱茂新所有的家什和文章在一场无缘无故的纵火案里被烧成了灰烬,唯一可能提供关于林展新思考与精神生活证据的是那本《哑语手册》,但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它的印刷充满了错误。至此,语言交流的艰难和困境暴露无疑,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的可信也变得摇摇欲坠。文本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有逻辑的生活空间中,每个人似乎又都是关键点,但随着文本情节纷纷扬扬的展开,我们发现个体信服的生活逻辑却演变成一种难以诉说的荒诞。每一次力图梳理清楚的过程都预示着整体推理上的失败。这一情节结构的建立,使我们清晰洞悉在一个充满偶然、琐碎与神秘的纷乱世界里,即使是自认为拥有主体意识的个人,也无法完全沟通,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孤独的存在。我们往往会遭到自己倍加推崇的语言残酷而有力地袭击,语言的所指和能指之间时常会出现指涉的模糊甚至错位与撕裂,给原本凌乱而神秘的世界增添了更多的不稳定。小说《谐振》、《孔成的生活》等在情节上亦是如此,神秘纷乱,让人一头雾水,无法摸清头脑,文本建构的真实离预想的真实愈来愈远。
北村小说文本建构的这些特征,使其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一功绩是作为文本试验的先锋来进行解读和建构的,而解读和建构本身所构成的隐性文本性思想内涵又是北村所极度渴望的。这一状态是对当下本真生活的文本投射,这一投射更多的应该看成是平面化生存状态背后的深度精神探索。
参考文献:
[1]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 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P.34
[2] [3]北村:《玛卓的爱情》[Z],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 P.54,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