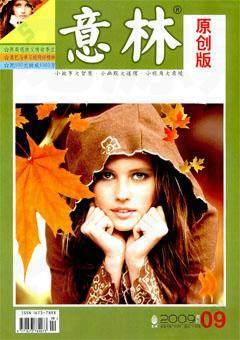行云流水一孤僧
2009-07-06孙君飞
孙君飞
翻看《围城》,读到两句话:“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留学生不知道苏东坡、黄山谷,目间只有这一对苏黄。”
苏曼殊对于今天的许多读者而言,已经日渐陌生了,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是最受留学生追捧的文学对象之一.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逝去了便不会再来的奇人。
苏曼殊原名戬.后改名玄瑛(亦作元瑛),曼殊是他的法号,但他在法号前加一俗姓,半僧半俗,天下少有。苏曼殊生于1884年.广东香山人。但他的出生地在日本横滨,其父是茶商,早年在日本经商,娶妾河合仙氏,据传却又与河合仙的妹妹生下苏曼殊。这段隐秘的家史,苏曼殊至死不知。
6岁时,父亲将河合仙和苏曼殊带回国。由于不容于正房.他们备受歧视,甚至一个下人都可以毫无顾忌地鄙夷他们。无奈之下,河合仙只身返回日本,年方12岁的苏曼殊也只能到广州城中的六榕古寺削发为僧。这成为苏曼殊一生的痛或幸,让他在佛门内外孤独飘零,辗转不定。
六榕古寺的长老赞初大师十分喜爱天资聪慧的苏曼殊,为他所取法号也包含深意,“曼殊”即文殊之意,代表吉祥,此即《维摩诘经》之所谓文殊师利也,赞初大师对新来的小沙弥寄托了无尽的希望。后者又在著名翻译家庄湘的指导下熟练掌握了英语。在六榕古寺中,他的机智灵光一如既往。每部经书,他都过目不忘。
15岁时,苏曼殊欲留学日本.亦欲东渡寻母,却没有盘缠,只好每日随乳母在广州街头卖花.以此攒钱作为路费。在留学期间.表兄林氏每月仅资助苏曼殊食宿费10元,他的生活异常清苦.尽管费用紧张,苏曼殊仍利用假期游历泰国、斯里兰卡等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903年,苏曼殊在回国前.留诗赠友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他到的第一站是上海,当时正值“苏报案”发生不久,他毅然在章士钊等人办的主张革命的《国民日报》就职。他接连发表一些诗文,鼓吹激进思想,还用文言文写现代小说.揭露社会黑暗,并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成为最早将雨果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人。
1903年冬天,《国民日报》停刊。苏曼殊生计断绝.离沪远去.离开朋友,苏曼殊的境况更加凄凉。他没有固定职业,四处流浪,有时以教书为生,有时靠卖文过活,有时寄食于寺院,有时求贷于他人,有时则“穷饿不得餐。拥衾终日卧”。
数年后,重返上海的陳独秀一次与朋友在一家酒馆用餐。谈话间,闯入一个眉目清秀的和尚.正是苏曼殊。他虽着僧装却不戒酒肉,后经陈独秀等人劝说而改穿西服。苏曼殊一改过去的沉默寡言,高谈阔论,而且结交甚广.除男性朋友外,更有女性朋友,可谓“美人如玉剑如虹”。
此时的苏曼殊立下大愿.要学习玄奘,做“白马投荒第二人”。他游历印度、锡兰、越南等国,遍寻佛经,译介了八卷《梵文典》,在《天义报》上发表,弥补了中国佛学史上的一大空白。事前.陈独秀向苏曼殊提供《梵文语法入门》等三种英文参考文献,极大地帮助了他的翻译。《梵文典》发表时,陈独秀又以熙州仲子的名义为之题诗。
出家后的苏曼殊并未四大皆空,与尘世绝缘,仍旧托钵于革命和文学之间,时而工作,时而化缘,来往于革命同道和文坛友人之间。他曾在湘水效仿贾谊作赋凭吊屈原,也曾在泛舟时吟唱拜伦的《哀希腊》,歌哭无常,并翻译《拜伦诗选》,家国之痛依然。
《弘一大师永怀录》中的《忆弘一法师》一文称:在太平洋报社里有两位出色的画家,一个是当时已做了和尚的苏曼殊,再一个就是未来的和尚李叔同。李叔同的画作用笔雄健遒劲,而苏曼殊的画作多取材于古寺闲僧或荒江孤舟,意味颇萧瑟孤僻,然而后人对苏曼殊评价甚高,认为他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开放转型的先驱。
苏曼殊既是“革命僧”、“诗僧”、“画僧”,又是多愁善感的“情僧”。他为初恋情人赋诗:“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谁为采芙蓉?”1909年.他在东京一场小型音乐会上结识了“调筝人”百助,在诗中写道:“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据说,苏曼殊东渡寻母后。定有一门亲事,但未婚妻早死.令他万念俱灰,他归国后不是回到苏家的深宅大院,而是重新回到青灯古佛前,开始了第二次出家生活。苏曼殊病危期间,写信给好友萧纫秋,信上画有一个鸡心图案,旁注“不要鸡心式”。众人不解.萧纫秋沉思良久,说:“苏和尚大概知道已不久于人世,所以嘱托我为他买一块碧玉,他要带着去见地下的未婚夫人。”于是。他在广州买了一块方形的碧玉.托人带到上海。圆寂前的苏曼殊已经三日不饮不食,仿佛在等待什么。当方形碧玉接到手中时,苏曼殊将其放至唇边轻轻一吻,欣然一笑而逝。此前,他还计划写一部百回长篇小说,每回附一张插图,并已绘成30张,以此纪念未婚妻,可惜未能将书出版。
在苏曼殊的小说中,他不仅称“爱的深处就是忧伤”,乃至毁灭.还称:“爱就够了,我们还要什么?”
其实,苏曼殊的特立独行、癫狂无度乃天真烂漫、淳朴清亮的天性使然.历尽坎坷而不谙世事。他爱抽雪茄,大嚼牛肉,喜啖摩尔登糖.没钱买糖,则敲下自己的金牙“易糖而食”,也曾指着洋油灯大骂.这些孩子气的行为使他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备受朋友们的宠爱,但也累了他,伤了他。他曾经生吃鲍鱼直到腹痛生病,章太炎在《曼殊遗画牟言》中回忆苏曼殊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到了晚上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苏曼殊圆寂后,陈独秀方才醒悟:“照这样看来,当曼殊是傻子的人,他们还在上曼殊的大当呢,曼殊的贪吃,人家也都引为笑柄,其实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恶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
1918年5月2日,苏曼殊果真由于肠胃病,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病逝,年仅34岁。临终前,他留下“佛衣藏我,以塔葬我”的嘱托和“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的八字遗言。孙中山闻讯后,万分惋惜.直赞苏曼殊“率真”;续范亭以“革命伟人”、“高僧”、“前贤”赞他.章太炎则以“厉高节”、“抗浮云”赞他。革命团体光复会追认他为“文化导师”,而曹洞正宗第四十六世传人圆瑛大师承认他是阿罗汉。柳亚子这样哭他:“鬓丝禅榻寻常死,凄绝南朝第一僧。”一位南社诗友在挽联中这样对他进行概括:“曼殊本是多情种,一领袈裟锁火焰。”
朋友们将苏曼殊葬在他的另一个重要的精神故乡杭州西湖,在他的墓前矗起一座石塔,上镌“曼殊大师之塔”六个大字。苏曼殊之墓与南朝苏小小墓南北相对,与鉴湖女侠秋瑾墓隔水相望,“明月夜.曼殊坟”,西湖又添一景致。柳亚子写诗悼念道:“孤山一塔汝长眠,怜我蓬瀛往复旋。红叶樱花都负了,白雅桂子故依然。逋亡东海思前度,凭吊西泠又此缘。安得华严能涌现,一龛香火礼狂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