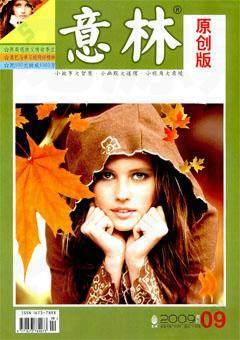无用之物方有大用
2009-07-06夏雪戌
夏雪戌
他的职业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一名教授,三尺讲台让他很受用,与学生的交流让他很愉悦。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拥有许多奢侈的生活习惯,比如写字只用万宝龙笔,他戴百达翡丽表,拎LV包,用萬宝龙限量版钢笔,抽库阿巴雪茄,用登喜路、都彭和大卫·杜夫烟具,他不但有房有车,还有专职司机。虽然他有着在普通人看来过于奢侈的生活,却绝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位收获颇丰的学者。他掌握了十多种语言,除了英、法、德、日、荷兰、西班牙等常见语言外,还包括梵文、巴利文、阿维斯塔语、尼瓦利语、婆罗钵语、古孟加拉语、古伊朗语、古藏语、和阗语、回纥语等稀奇古怪的语言。他是中国最年轻的印度学、佛学、梵学专家。他的名牌服装和万宝龙笔、名表、专职司机都使他看起来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者。但他又实实在在是个学者。
他就像一个谜,既忠于钱又忠于文化。
他,就是季羡林教授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先生。
梵文巴利文是一个非常冷僻的专业,钱文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专业还要从他高二那年说起。当时就读于上海华东师大一附中的钱文忠,他的历史老师郝陵生喜欢在每节课前介绍点学术界的情况。有一次,他说梵文研究很重要,但是似乎学的人很少。季先生年岁已高,再没有年轻人去学,恐怕这门学问在中国要绝了。钱文忠听了以后,就自己找书看,然后便给当时已72岁的季老写信,希望能拜他为师学习梵文。钱文忠很快收到了季老的亲笔回信,为此他深受鼓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梵文巴利文班,新中国成立以来只招过两次学生,1984年,钱文忠就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主修印度学,副修伊朗学、藏学,成为季羡林教授的关门弟子。季教授的最后8个学生大多中途改行,坚持到底的只有钱文忠一人。
“冷”到不能再“冷”的专业,钱文忠却乐在其中。他一直在印度古代佛教语言和西域古代语言研究这个极其冷僻的领域里坚持着。钱文忠研究梵文完全是出自自己的爱好,带着浓厚的兴趣去学梵文、读梵文经典、研究梵文,其中多的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快乐。钱文忠的“聪明”是公认的,当年他以外语类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北大。但他却很用功,他几乎不在3点以前睡觉,没有在7点以后起床。他奉行季教授讲的“一个人真的要把一个事情弄好了,是要聪明人下笨功夫”的原则。
“梵文是没有什么实际效益的,虽然现在很多人把它说得很重要,但那也只是学术意义上的,不能为稻粱谋。尤其是经济效用,更是谈不上。学问、专业是我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从经济上来讲我完全不需要它。这个东西无用,但有时候无用之物方有大用。”
所以钱文忠一直践行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支撑钱文忠的这种“奢侈”生活和学术研究的当然并非教授的那份菲薄收入,进入复旦前的下海经历让他在经商赚钱方面得心应手,他是北大青鸟的独立董事,还亲自打理着几个公司,所赚的钱足以供养他“玩”学术以度余生。
就像于省吾先生说的那样:钱文忠是有学问的人当中有钱的,有钱的人当中有学问的。可往往我们只看到他风光的一面,却看不到他为风光所付出的。正像他自己所言:要有很大的牺牲,我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各种形式的交换为基础的。现在你看到一些人很成功,但没有看到他付出多少,我付出的有些东西是很多人不一定敢付出的。尤其是在你还不知道你能得到什么的时候,你是否敢于付出。
恰恰是钱文忠的这种生活态度,成就了今天他在无用的梵文学术研究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