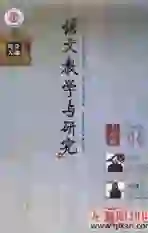不露声色中激情已经远去
2009-07-02金立群
看了《玉米地》,就想起了《红高粱》,因为看上去有几分相似,写的都是不合理法的性关系,写的都是大自然中的性行为。或许有的读者会因此觉得这篇小说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自然,《玉米地》很可能难有《红高粱》那样的经典价值,但是它却绝非某种小说套路的简单模拟,而是颇具微言大义的风范,于不动声色中揭示了时代精神的变迁。
应该说,人的本能欲望之于生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两篇小说的共同点。但是这种本能欲望必然受到文明、道德、礼法的制约,也是两篇小说主人公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中说过:“文明是服从效益需要(ecoAnomicnecesity)的法则的,因为文明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大量心理能量必须从性欲中节省下来。”因此要充分施展和宣泄自己的本能欲望,就必须克服各种功利的因素。在《红高粱》中,这样的“克服”以及由“克服”所展示出来的那种生发欲望的生命力,是何等震撼人心,生命力甚至可以强大得弃生命本身于不顾的程度。就从细节描写上来看,高粱地的火红一片如“汪洋的海洋”,其所酿之酒令男男女女血脉喷张,皆使人心醉神往。
《玉米地》中的男女主人公自然也有他们的壮举。他们最大的壮举倒未必是在玉米地里完成的,而是在城市立交桥的暗影中——如果他们能不顾射来的灯光一如既往沉醉在自己的性爱中,那么他们就是《红高粱》里激情男女更加有种的传人。然而他们落荒而逃。他们有自己的欲望,他们也渴望宣泄,但是和红高粱里的英雄相比,他们身上总透着一股软弱:
“刚把裤带解开,两道汽车的灯光刷地照过来,他们只好赶紧把裤带系上”——他们为什么不能对着汽车骂一句呢?
“汽车竟停下了,一个男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大声呵斥道:干什么呢?你们是狗哇!可把高山和春河吓坏了”——于是他们只好离开城市去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交欢之所。
因此《红高粱》中的高粱地是生命中不期而至的缘分,象征了反抗;而《玉米地》里的玉米地却是事先安排的退路,象征了爱欲对文明从精神上已经做出了妥协。因此在《红高粱》里,我爷爷我奶奶钻高粱地充满了对一切束缚与危险的藐视,而《玉米地》里的主人公钻玉米地却里外透着一层怯:“大概觉得老是顺着钻不太保险,就挤过玉米棵子,横着钻。”
所以这篇小说最后的情节发展并不让人觉得突然。女家收了男家的彩礼,就此“闪人”,男主人公虽然号称要一直找下去,却也终于又出去打工,重归平静生活了,就如同开始声称半年即可重回赛场的刘翔,其实估计是永远也回不去了一样。
时代不一样了。人的主体精神在日益蓬勃的市场大潮中渐渐萎顿了。但是这种萎顿却并非以一种否定的状态出现,而是在貌似肯定中被抽去了脊梁骨。在《红高粱》诞生的年代,性与本能欲望还处于“非法”状态,却有着无可遏制的力量。今天,性与本能欲望早已泛滥成寻常之事,却失去了内在的豪迈之气。
评一篇小说,真的不能就事论事,就好像我们看荣格的名言“性格决定命运”,不仅要看它本身说了什么,还要看它实际上没说什么——没有说“财富决定命运”、“道德决定命运”、“信仰决定命运”、“教育决定命运”等等。同样道理,评小说也需将所论对象和其它作品进行比较,以显现出其隐义与旨趣。即如这篇《玉米地》——作者于不露声色中,已经细腻地勾勒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变迁。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将它和《红高粱》做更细致的比较,就可看出,作者并没有重复前人已经走过的路——他的小说同样包含了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智慧。
金立群,文学博士,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传播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