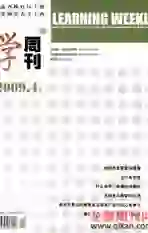此中有真意 欲辩不能言
2009-06-20单君萍
单君萍
摘要:陶渊明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但进入了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一样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他所开创的田园诗,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他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建筑了一个精神的家园,这个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生厌的话题。
关键词:仕与隐;安贫乐道;崇尚自然
陶渊明又名元亮,世号靖节,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梁钟嵘说:“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这句话,颇有见地地表明了陶渊明的人和诗。朱自清也曾说过:“中国诗人里影响最大的似乎是陶渊明。”由此可见,陶诗在我国诗史上是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的。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家庭,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东晋王朝已面临瓦解,人民的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等都使社会环境愈加混乱污浊。由于受传统儒道思想的熏陶,又受家族环境的影响,他因而有着“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截然不同的志趣。当他带着“大济苍生”的愿望踏人仕途时,社会的现实却不容他的理想、志向有发展的机会。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济世的宏志无法施展,而且不想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给予其深刻影响的老庄思想和隐逸的社会风习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可见,“道之不传”的理想幻灭使他转向躬耕自给、自劳、自娱,以求心灵的宁静与淡泊。此后,他又为彭泽令,就在他上任八十余日之时,逢郡都邮来巡,属僚告之应束带进见,他长叹到:“我不能为五斗折腰。”并即日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自己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向归田之路,也给后人留下了其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
《饮酒》(其五)是陶渊明众多“归鸟”诗篇中最能体现诗人回归自然、回归性情、保持真我思想的诗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作者游目骋怀,参透自然,却故意把自然“真意”说得如此飘缈朦胧,其实稍加玩味,便不难发现真意是什么。秋菊自开自谢,保持一份洁白淡泊;南山自古及今,保持一份肃穆庄严;太阳朝升暮落,保持一份秩序宁静。自然万物,各随其分、各安其道、消长生息、穷通演化,莫不自自然然、实实在在。飞鸟投林的描写,更是充分强化了这一天地观念。像天地万物一样,飞鸟早出晚归,远近觅食,有困顿劳碌的疲惫和紧张,也有安顿休息的轻松和愉悦,有呼朋引伴的热闹,也有失群掉队的孤单,该去则去、该回则回。一切随顺自然,和山林、夕阳、南山、秋菊、东篱构成了一幅天然纯美、自然静谧的图画。可以说,这只小小的归鸟,这只与同伴同飞、与山林同眠、与夕阳同行、与自然同道的小鸟,还与诗人同心,正是这种天人合一、人鸟同道赋予了陶诗以深刻的哲学内涵。
陶渊明的诗表现为一种质朴、平淡和自然之趣。但这种自然,不是粗率浅露,而是在平淡中寄托深致的情韵,如玉隐石间、如珠蕴蚌腹,在一种浓郁的山林气息和天籁梵音中给人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安养。所以朱熹曾言:“陶渊明诗,人皆说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而这份豪放,恰恰在于他“固穷”的德操,在于其澄莹宁静的心态下那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开朗与豁达,也一如其人名号“靖节”二字。诗人回归田园、崇尚自然,这里“自然”指人质朴真实、率性而行的本性。他无法忍受官场对人本性的扭曲,追求“本我”、“真我”,不一味趋同,以求保存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价值,从字里行间我们不也体味到他济世不得的痛苦与回归田园的无奈了吗?
古代出仕是文人志士必然的价值取向。在封建专制独裁统治下,他们只能在无条件服从与维护自身尊严、保持独立人格的矛盾中苦苦挣扎。除了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都曾流露过归隐的心绪,只不过陶渊明比较明显,且付诸实际行动罢了。陶渊明晚年作过大量诗,“猛志”一词出现多次,这表明显然有一股济世的热流贯穿于他的一生,其平淡自然的诗风始终未能掩盖此股热流的跃动,看似恬淡的归隐并不意味着痛苦的消失,而是象征着苦难的加剧。“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归去来兮”、“忆矣乎”、“胡为乎遑遑欲何之?”这些句子表明诗人在惆怅悲苦中饱受折磨。
纵观陶渊明的一生,他深受道家以“道法自然”为根本宗旨的影响,要求人性反璞归真。进而实现和谐、纯朴、安宁的美好社会和人生。老子的贵柔守雌、谦下居后、无为不争。使身处“魏晋风度”的陶潜终于顺应了人生的天性,冲破世俗,投身自然、纵情山水。然而少年时代所受家庭的熏陶和儒经的影响,又使他怀有兼济天下、大济沧生的壮志,他又遵从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出世、人世的准则,然而,他未能大济苍生。也未能独善其身,晚年还要靠乞食为生,这是一个封建社会下正直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