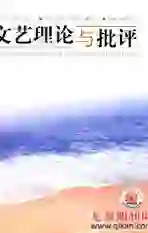论刘庆邦小说中的民俗系列
2009-06-18陈英群
陈英群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文学起源于劳动,是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历史生活的,自然与民俗结下了不解之缘。民俗文化凝聚了一代又一代民间百姓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艺术才能和思想情感。自古以来,不少文人墨客的创作都曾受惠于民俗文化,从而写出了流传于世的不朽佳作。一些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作家,深深地受到民俗的浸染和熏陶,自觉不自觉地在作品中融入了民俗色彩,打上了自己思想情感与个性特色的印记。刘庆邦正是这样一位带有鲜明个性的优秀作家,在其乡村题材的小说里,无不倾注着他特有的乡土情感。孩童时期耳濡目染的乡村民俗,带给作家无穷无尽的回味,引动着其创作的思绪和灵感。刘庆邦在描写其故乡的世态人情、风土习俗以及生活方式时,娴熟地将乡间民俗的描绘同刻画人物和推动情节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幅充满诗意的乡村风俗画,使得其乡土小说凸现了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
一
在传统社会中,婚姻被当作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自古以来,青年男女的婚姻程序大都遵循着周代即已确定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这六种从议婚至合卺过程中的礼节。随着时代的变迁,“六礼”的程序在不断发生变化,婚姻程序总的演进趋势由繁至简。相亲、相家、订婚、结婚,这是大多数乡村青年男女所要经历的婚姻程序。
相家这一相传很久的民俗,在农村一直延续至今。对于女方来说,若是自由恋爱,心甘情愿要嫁的另当别论;若是红娘牵线,大多都要走一回相家程序,除非知根知底等特殊情况。相家,是女方父母为了女儿的前途、命运和一生的幸福在婚姻上把握的第一关。在豫东平原,相亲之前要先相家。《相家》中的女孩子染已到了论婚嫁的年龄,她担心母亲听信了表叔的“吹大气”,不明就里地让她贸然去相亲。其实不然,只有母亲真正对女儿的亲事上心,她不为媒人的如簧巧舌所动,准备亲自前往男方家相家。母亲做着手上的准备工作,补了一双棉袜,做了一双新鞋,还借了一身适合相家时穿的褂子;其内心的准备则不为他人所知,人还未出门,梦里的相家已经去了好几次。按照约定时间,母亲走着去了21里外的男方家里,最终做出了不让女儿跟人家相亲的决定。刘庆邦以高超的创作功力,妙笔生花,将母女亲情融入相家这一乡村风俗之中,准确细腻地传达出母女连心的微妙情感世界,展现出特有的乡间生活氛围里那份自然动人的魅力。
在择偶方式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传统社会中必须通过的第一个婚姻程式,婚事大权掌握在双方家长手里。随着社会的进步,“相亲”的主角大多已由双方家长换成男女当事人。虽然很多农村青年的婚姻还是经媒人撮合而成,但相亲已成为大多数男女当事人必须亲历亲为的一道程序。刘庆邦饶有兴趣地以小说的形式涉笔“相亲”这一婚俗,在多篇作品中娓娓述说了几个不尽相同的相亲故事。《闺女儿》中的女孩子香15岁,《红围巾》中的小姑娘喜如虚岁才15,就被大人们拉着相过一次亲。诚然,农村的早婚现象比较普遍,尚未成年的少男少女较早涉及相亲也不足为奇。喜如的相亲是一个无言的结局,她把这次失败归结为没有借到一条红围巾。红围巾确实是某个年代里一件代表着时尚的物品,也是乡村姑娘梦寐以求的奢侈品。相过亲的喜如有了心事,红围巾就是一个最大的心事。少女香心地如清泉般洁净,对世间人事还朦朦胧胧,感觉自己将要成为相亲中的一个角色并不十分好玩,恍惚间童年时扮新娘的游戏依然鲜活有趣。她看上去似乎对大人们的安排多少有一点点抵触,最为担心的是乡邻们知晓她此次活动的秘密。不管是否情愿,香还是跟在母亲身后去了约会的河边。她和同龄的那个中学生隔着些距离坐在绿草如茵的河坡上,两人尴尬地搭讪了几句,生涩地预演了一场本该由成年人做主角的游戏。平日里,勤快的香言语不多,心里常常自说自话,随之笑意就从心底漫溢出来。幸福是什么?香正在感受着。无论相亲的结果怎样,香仿佛已经历了一次人生成年仪式的洗礼,心理年龄陡然增长了几岁,少女的心房有了属于自己的秘密,快乐的生活中平添了些许淡淡的伤感。整篇小说勾勒出极具动感的乡村风俗画,流动着极其悠扬的村野小唱。
若相亲成功,男女双方便可进入订亲程序。在农村很多地区,订亲常常是男方所要面对的一道不能绕过的门槛,大多都要往女方家中送一定数量的彩礼。刘庆邦并没有就聘礼这一习俗的具体操作发表议论,而是不吝笔墨地描写在男女青年之间尚不敢大胆交往的那个年代当事人订婚后的心理活动,丝丝入扣地呈现了此一方对彼-一方深切思念的淳朴感情。在《夜色》中,周文兴心疼未婚妻高玉华在出嫁前要为娘家脱坯盖房的举动,恨不得马上跑过去替下心上人。他不好意思大白天贸然到高家庄帮对象干活,就趁着夜色前去帮着翻坯。周文兴发现高玉华躲在麦秸垛边,哨悄观察,上前想见,却没有喊出声。《春天的仪式》开篇由三月三的庙会人手,温煦的春风与热闹的庙会带给人们无限遐想。年复一年的三月三庙会不知从何朝何代起,一年一度的这个庙会成了乡民们的一个节日。这年的三月三对于女主人公星采来说非同往年,在她的心里陡添了一份期盼。在自由恋爱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环境下,乡村常见的媒人介绍,星采看来还是满意的,她已经开始心系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对象,三月三给了她可以再次看到“张庄那孩子”的机会。刘庆邦不愧是一位描写女性心理活动的高手,如明镜般洞悉了一个青春少女的隐秘情思,把星采表面故作镇定、内心却波澜起伏的微妙心理,一层层剥笋般展露出来,让人读来忍俊不禁。作者不着痕迹地将星采寻觅“那个人”的心思行为溶注进乡间庙会这一民俗之中,使得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故事,点染上特有的乡间风情,吹奏出诗意的乡土乐章。星采置身于庙会欢庆的氛围中,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她极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寻找一个人的身影,而当朝思暮想的那个人显然向她走来之时,她却慌乱得不知所措。小说在此戛然而止,事情的结果倒显得不怎么重要了。
二
婚礼意味着男女当事人正式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闹洞房”则是乡村婚礼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习俗。历来民间有“新婚三日无大小”的说法,婚后三天,宾客、亲友、乡邻不分辈分高低,都可以挤在洞房里逗闹新郎新娘,即使闹得有些过分,新人也不能恼怒。《走新客》中的新娘大银被闹了个人仰马翻,当一个又硬又重的枕头砸在额头上时,疼得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哭着骂了起来,最后落了个“性子太野,不识玩儿”的评价。新郎长星也不怎么同情大银,认为“人家跟咱闹,是看得起咱,说明咱们家在村里人缘好”。《不定嫁给谁》中的新娘子小文儿心情不大好,对人们肆无忌惮地闹房流露出烦躁的情绪。她一直在期待着一个人的出现,那就是曾和她
相过亲的田庆友,正是因为自己当时的矜持,便永远错失了做这个人妻子的机会。《摸鱼儿》中的男孩子春水才十四五岁,身体正处于发育的上升阶段,已有了性欲的萌动,对同龄女孩子替的身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利用高山婚礼上闹洞房时,春水心怀鬼胎地等来了替,浑水摸鱼偷偷摸了替的奶子,拽了替的裤子,第一次实施了对替的身体触摸。春水掩饰不住成功的喜悦,故意让替察觉他做了什么。而替在基本认定是春水对自己的身体侵犯过时,并没有表示出真正的生气,甚至不大忍心拒绝一起去“听房”。在听房的过程中,春水对替的身体进行了更大幅度的探索。春水“想跟高山学习”,替担心“怀了孩子怎么办”,但春水似乎已经得到了替的某种默许。果不其然,此后的一天中午,在一个废弃的瓜庵子里,替装作睡着让春水终于得逞。随后,两个小人儿持续地进行着这种假装睡觉的游戏,直到女孩子替真的怀孕了。春水原本只是想着玩一玩,最后只好把替娶进家门。一对少男少女从婚礼中学习了成年人的行为,过早地对性这个神秘领域进行探索,他们越过相亲、相家、订婚等婚姻程序,直接开始了漫长的婚姻生活。小说《摸鱼儿》笔致从容,情节舒缓,充满着浓厚的乡野气息和村野情趣。
婚礼的最后一项是“回门”,即新婚夫妇同去女家省亲的婚俗。这一婚俗,从女儿方面来说,表示出嫁后不忘父母养育之恩;从女婿方面来说,除感谢岳父岳母恩德外,还有拜会结识女方亲友的交际意思,带有认亲的性质。在农村很多地区都有“闹新婿”习俗,所以“回门”对新女婿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新娘的姐妹们会放肆地嬉闹新女婿。大概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吧,刘庆邦的《回门》中大姐新婚回门时并没有新女婿的陪同,而当地的规矩是新女婿在新婚第一年的大年初二去拜访新娘的娘家人。这一过程称作走新客,“闹新婿”的节目即在此时上演,且男青年是嬉闹新女婿的生力军。《走新客》中的新女婿长星对第一次陪妻子大银回娘家感到发憷,还未前行就已忧心忡忡。原本满身田野之气的大银,在丈夫的调教下已初显女儿家的温柔,很乐意接受长星“算大账”的提议,并应承在丈夫受村人戏弄不堪之时搬兵搭救。长星最初也是想着忍忍了事,但当一个男青年用手掌打了他的脑瓜子时,感到伤了自尊的他以不再给那青年点烟表示抗议,双方对峙陷入僵局,直至大银悄悄搬来大奶奶才解了围。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当晚上大银把受了委屈的丈夫拥入怀中时,触觉到湿漉漉的泪水,便以小夫妻协议的“算大账”的方法来安慰长星。刘庆邦借走新客“闹新婿”这一习俗,含蓄地将一对新婚夫妻床帏隐情曝光,走新客带来的一丝烦恼转眼淹没在“算大账”的欢娱之中,寻常百姓家简单而甜蜜的生活掀起层层诗意的浪花。
三
尽管各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但人的一生大都会阅历无数的人生仪礼内容,若从大的方面看,很多地区都有童礼、婚礼、寿礼、丧礼等几个部分。“既然一个人从降生到成年,都是处于周围民俗事象对他的浸染和熏陶之中,他自己也总是处处摹仿;而且民俗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如此举足轻重,其潜在心理力量如此不可抗拒”。在现实生活中正是如此,很多民俗被人们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历史上有不少的文人,如曹雪芹、鲁迅、沈从文等,娴熟地在文学作品中随笔点化民俗的色彩,为文学宝库奉献出不朽的佳作。刘庆邦的小说,通过豫东平原地方习俗成功地写出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例子很多,几乎涉及了人生仪礼的各个部分。
在人生仪礼的众多活动中,大都寄托着至爱亲朋的美好愿望和祝福。在长篇小说《红煤》中,宋长玉在明金风的母亲生日之际,适时地送上了一个生日蛋糕,使得明大婶儿惊喜不已,此举为宋后来能够娶到明金风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若干年后,宋长玉已富得流油,一次为岳父明守富庆贺生日时,他不仅定制了一个很大的生日蛋糕,还包了一桌十分丰盛的酒席,并委托妻子奉上一万元的贺礼。醉翁之意不在酒,宋长玉得到时任村支书的岳父大人恩准,入党一事顺利解决。很久以来,祝寿礼仪在民间风生水起,大有愈演愈烈的势头。其形式上已融入了西方元素,成为亲友们联络感情的一项重要活动。
生与死分别是人生跑道上的起点与终点,有关人的生与死的仪礼很多。童礼是与孩子出生相关的一些人生仪礼,有着一系列的仪式活动,用来寄托亲友们对新生命诞生的祝愿和希望,这些祝愿和希望无不打上了信仰和宗教的烙印。如有的地区为婴儿剃发时,要在婴儿前脑门上留约一二寸见方的胎毛,家人以借留胎毛来表达望子成龙的殷切希望。在小说《尾巴》中,刘庆邦讲述了一个过去年代时有所见的留胎毛故事。小旺从小就与众不同,他的脑瓜上留有被称作“尾巴”的一块头发。可以说,小旺是被人拽着“尾巴”开始长大的。父母拽他的“尾巴”,表达对他无比的宠爱;父母欢迎且有意让村人们拽他的“尾巴”,他也不是十分反对。直到上学之后,小旺才真正感到“尾巴”带给他的烦恼。同学们恶作剧地拽他的“尾巴”,让他穷于招架。他哭闹着要将“尾巴”剪去,母亲告诉了他留“尾巴”的缘由,“尾巴”关系着他生命的存活。小旺十二周岁生日那天,其父母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把他的“尾巴”剃掉了。且不论“尾巴”是否真的有什么神奇的效用,父母祈求小旺健康成长的良苦用心确实不难理解。
谁不希冀自己的亲人健康长寿呢?但世上毕竟没有长生不老药,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葬礼》的背景在国家经济最为困难的那一年,“我”的父亲突然得了急病撒手人寰,当时连一片做棺材的木板也无处可寻,只好将家中的一个站柜改造了。吹响器就免了,别说没有钱请响器班子,就是有钱请得起,饿着肚子恐怕也吹不响。除此之外,葬礼的各项仪式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我”是长子,负责为父亲摔老盆和扛引魂幡。死者有多少个子女,就可由子女在老盆的底部钻多少个眼,这样死者到另一世界前需喝掉的水会漏掉一部分,不至于喝不完水被拒之门外,成为四处游荡的鬼魂。在送葬的路上要将引魂幡上的纸带一条条撕去,起一种路标的作用,引导死者的魂灵离开家门,顺利上路远行。在《黄花绣》中,三奶奶快不行了,14岁的小姑娘格明被选上来为三奶奶送终的鞋上绣花。格明从未绣过花,但她符合绣花人的三个条件,即家中父母双全、儿女双全、本人是16岁以下的童女。格明推却不掉,只好临危受命,务必要赶在三奶奶断气前绣出两朵小黄花。她感到自己手上的责任重大,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摸索着完成了绣花任务。虽说写的是一件丧事,小说中并没有太多悲痛的气氛,反而透射出些许明亮的光泽。至少在格明的眼里,两朵金黄色的花是那样的光彩烁烁,继而升腾出满屋子的花朵。如果相信灵魂存在的话,那么逝去的亲人应该安心过渡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豫东平原称唢呐为大笛,只有丧事才请
响器班子。《响器》中的高妮天生是大笛的知音,她如梦如幻地循着大笛的乐声而去,“大笛刚吹响第一声,高妮就听见了。她以为有人大哭,惊异于是谁哭得这般响亮!当她听清响遏行云的歌哭是著名的大笛发出来的,就忘了手中正干着的活儿,把活儿一丢,快步向院子外面走去。节令到了秋后,她手上编的是玉米辫子,她一撒手,未及打结的玉米辫子又散开了,熟金般的玉米穗子滚了一地。母亲问她到哪里去,命她回来。这时她的耳朵像是已被大笛拉长了,听觉有了一定的方向性,母亲的声音从相反的方向传来,她当然听不进去”。高妮站在离响器班子很近的地方,如痴如醉地沉浸在时而凄婉时而高亢的乐声中,泪水不由自主地顺着脸颊滑落。她不是为死人感伤,而是为乐曲动容。四五里地外断断续续传来大笛的声音,如仙乐梦幻般萦绕在她的耳畔,牵动着她的思绪,促使她逃脱母亲的看管,奔向大笛响起的地方。大笛的乐声在她的脑海里幻化成无数美妙奇幻的画面,劲风吹过,葱绿的麦田翻滚出金黄色的麦浪,满地的高梁与天边的红霞连成一片,暴风雨敲着鼓点响起来了,漫天大雪飘飘洒洒覆盖了整个大地。高妮仿佛就是为大笛而生,十四五岁的小闺女儿执拗地要学吹大笛,父母的软硬兼施根本无法动摇她的决心。她最终如愿以偿,拜大笛手崔孩儿为师,吹上了大笛,吹成了气候,吹出了阳光灿烂的一片天。
刘庆邦不愧是文学创作领域的一位出色的大笛手,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响器,他通过自己的小说发出了柔美响亮的声音,吹出了一片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学天地。水有源,树有根。刘庆邦把自己创作的根深深地扎在民间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在很多作品中都注入了民俗文化的元素,溶进了豫东平原的民俗事象,点染出特有的家乡风情民俗色彩,塑造出典型的乡村人物形象。“由于民俗是构成民族生活文化史的主体与核心,作家在反映社会生活时,也就必然地在自己的著作中程度不同的溶注进本民族广泛的民俗事象。而反映民俗事象的本质,也常常是检验一个作家和人民关系的微妙尺度”。刘庆邦从事文学创作30年来,始终真诚地面对底层,倾心关注底层,坚持选择自己熟悉并感兴趣的乡村生活为素材,而不随波逐流。不能否认,刘庆邦是文坛一位辛勤的劳作者,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诚实的心,把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民俗现象熔铸进文学作品之中,因而其不少佳作都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