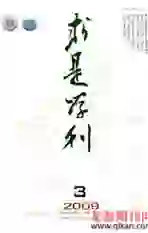职权为什么必须被行使?
2009-06-04于柏华
摘要:在我国的法理学中,法院等国家机关的职权被认为具有“必须被行使”这个含义,理由就是“不行使就是违反法定义务、要受到制裁”。这种解释的背后隐藏了一种独立于法律的事实意义上的国家(机关)观念,一方面只是一种职权的政治学、社会学概念,另一方面又与现今普遍被接受的法治理念相悖。因此,需要一种符合法治理念的国家观,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解释职权的法律性质,确定一种职权的法律概念。
关键词:职权;国家观;法治;次级规则
作者简介: 于柏华(1977—),黑龙江肇东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师,黑龙江大学法学理论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从事法学一般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2007年度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11524053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3-0076-06收稿日期:2009-01-10
在我国,职权(职能)是一个很常见的概念,它通常被看做权力的一种特殊类型,看做人大、法院等公共机构所行使的关于立法、审判等权力。它的特殊性体现在,行使职权的主体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决定该职权的行使与否和行使的方式,其本身包含了责任,包含了对主体自身进行限制的意义。这个常识虽然广为人们接受,但却存有这样的疑问:职权的这种自我限制性含义从何而来?如果说这是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那么从“人大行使立法权”、“法院行使审判权”这些法律规定里,又是如何引申出“必须行使”这个含义的?对此,现有的法学理论只是从职权行使目的的公益性角度给出了一个不够清楚的解释,更成问题的是,此种解释实质上隐含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国家理论,其意味着一种外在于法律的国家观。这与现今世界普遍接受的“法治”理念恰相矛盾,也不符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针。因此,有必要从法治的角度重新界定职权的性质,确立一种法律之内的职权概念。
一、职权概念的既有解释
目前,职权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结合了相关法律规则而得到解释的。依通说,与职权相关联的那些法律规则属于法律规则分类体系中的一种特殊类型,被称为职权性规则。“我们可以发觉一类不同于‘授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的规则——职权性规则。这类规则,对于行为人来说,既需要使用‘有权的表述,也需要使用‘必须的表述。它是权力责任的相互结合,故而称做‘职权性规则。”[1](P80)与前两类规则相比,它的含义是双重的,可以简单地表述成“既有权又必须”,其中的“有权”不能理解为“选择自由”,否则就会导致职权这个概念内部逻辑上的矛盾,而只能解释为“资格、地位、能力”,职权因此也就意味着主体享有一种不能放弃、必须行使的资格、地位或能力。但是从所谓的“职权性规则”自身却不能直接地得出“必须行使”这个含义,例如从“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法院行使审判权”、“交通警察执行交通法规”这些规定直接的文义中,看不出包含有“必须行使”的含义。原因究竟为何,从目前来看,相对来讲尚可接受的是一种“体系解释”。即,尽管从职权性规则本身不能直接得出“必须行使”这个意义,但从与其相关的其他法律规则中却可推论出这个含义。
“‘权力与‘权利是不同的。权力的运用,无须另外的‘保护,只要具有意志和力量即可付诸实现。”“在法律中,正是因为‘权力隐含了‘控制的意思,所以,‘权力和‘职责一词是可以搭配使用的。”[1](P80)并且“权利一词只是与个人利益相联系的,但职权一词却只能代表国家或集体的利益”,“职权一词不仅意味着法律关系主体具有从事这种行为的资格或能力,而且也意味着他必须从事这一行为,否则便成为失职或违法”[2]。所谓的职权不行使就构成“失职或违法”,又是因为“行使职权本身又是一种义务,不能适当地行使职权也就是不能适当地履行职责,这在一定条件下会构成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并引起法律责任”[3](P55)。
不行使及不恰当行使职权的公职人员受到处罚,这是一个可观察的事实,在法律上也是有据可查的。例如,“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或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裁决。警告、五十元以下罚款、吊扣二个月以下驾驶证,可以由交通警察队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6条)。这是一个授予特定主体以职权的法律规则,而必须行使职权的原因,按照上面这个解释,是因为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交通警察必须秉公执法,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人,应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适当处罚,不得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枉法裁决。交通警察违反上述规定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8条)。从后一个条文中可以得知不执行交通法规就要被处罚,进而可以推论出执行交通法规这个职权“必须被行使”。
该解释的成立有赖于这样一个前提,即被授予职权的主体与被处罚的主体是同一的。仍然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为例,其中第86条与第88条所针对的主体在表面上是不同的:86条针对的是交警队这样的团体①,而88条针对的是交通警察这样的个体。除非交通警察与交警队在执行交通法规这件事上具有同一性,否则就不能主张执行交通法规这个职权必须被行使。
这种团体与其成员的“同一性”问题看起来比较容易解决,尽管执行交通法规是交警队的职权,但由于其本身不能采取行动,它的行动只能由其具体的成员来完成,因此不论是交通警察正当还是不正当地执行交通法规,都应被看做交警队自身的行为。也因此,交通警察不适当地执行交通法规而受处罚也就应被视为交警队受到处罚,进而就可以得出交警队及其成员除了“有权执行”以外还“必须执行”这个结论。
如果这个论证是成立的,那就意味着“交警队”是一种独立于法律规则的事实上的存在。反之,如果主张“交警队”是一种依据法律规则而来的法律上的存在,就会出现有权执行交通法规的主体(交警队)与可能被处罚的主体(担任交警职务的个人)在性质上的不同一问题。个人无疑是一种基于自然事实的存在,具有感官意义上的实在性;而法律意义上的交警队则是一种规范性的存在,在一系列规则存在的条件下,某个或某些个人的行为可以被称为“交警队的行为”,其不具有实在性②。也因此,担任交警职务的个人受到的制裁就无法等同于对交警队的制裁,交警队的职权也就不能被理解为出于“不行使就要被处罚”这个理由而必须行使。
因此,只有把交警队理解为一种事实,才能合理地主张法律规则授予该存在以干预社会生活的独断性权力,同时又因为权力行使目的的公共利益性质,而要求其必须正当地行使权力,并以特定的惩罚作为保障条件。将这个结论运用到其他国家机构,该论证所隐含的国家观也就显露出来:国家乃是一种独立于法律规则的事实上的存在。职权概念的现有解释能否成立,最终也就依赖于此种国家观的正确与否。
二、国家观与法治理念
在法律与国家关系问题一般意义的讨论上,通常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保障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4](P32)。其中的国家,从与这个定义相关的解释来看,在表现形态上就是那些具体的国家机关,包括制定(认可)法律的立法机关以及实施法律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而这些国家机关能够从事如此行为的原因,在于它们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或者换句话说,它们是一些拥有绝对支配力量的人实现自身意愿的执行者,“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4](P37)。可以认定,正因为这个“支配事实”,所以国家是独立于法律并制定法律的。其他学者处理法与国家关系问题时在表述上可能有所不同,有的把其中的“统治阶级”换成了“统治阶层”[1](P40),还有的学者把“统治阶级”省略掉。不过就笔者看来,这些说法之间的差别并不像提出者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大,它们仍然都建立在共同的国家观念上,在法律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国家被看做一种独立于法律的事实。国家在制定法律,规范一般主体的行为的同时,也在运用法律手段对自身进行授权并自我限制,因此才会顺理成章地得出职权必须被行使这个结论。
此种国家观与法治、法治国家理念的相容性是成问题的,从这种国家观出发,法治就意味着国家制定出良法并自觉遵守之,而这又依赖于两个条件:其一,国家自身要具备足够的制定“良法”的理论和实践能力,还要具备较高的道德素养从而能够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其二,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社团)与国家相抗衡,从外部保证国家不至于胡作非为或背信弃义。不可否认,从社会史的角度看,西方国家的法治生成过程里确实体现出了这两个条件,该种法治理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事实,是一种关于法治的起源的社会史理论,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原因在于,从该理论的视角出发,“法治”只是国家慈悲的结果或迫于外在压力妥协的产物,而并不是国家行动的条件,起根本性作用的不是法律而是力量,这与法治的“规则之治”的含义恰相矛盾①。
能够与法治的“规则之治”这个含义相契合的国家必定不能是支配事实意义上的,而只能是一种法律之内的、其权威来自法律而非力量的国家。这并非是用理念来裁剪事实,而是在“还原”事实。国家这种存在本就不是如同物理性存在物一般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其到底为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主体的人基于特定目的的意义赋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范围,当主体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及相应的价值诉求发生变化时,国家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②。在当代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如果不否认“法治”(the rule of law)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诉求的正当性,认同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应从法律获得这一命题,那么一种法律之内的、通过法律规则组织起来并以法律规则为行动条件的国家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职权概念的含义也要结合此种国家观重新被界定。
三、“国家”的法律意义
法治意义上的国家观重点在于法律上,此视阈下的“国家”并非一个与某种实体有着对应性的概念,它只是在描述一种状态,即,在特定法律体系和法律规则存在的条件下,某些个人的行为具有了公共权威的性质,可以被视为“国家”(政府)的行为。因此,“国家是什么”要依赖于法律规则及其体系之性质的说明。
在对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观进行系统化解释的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与英国法学家哈特的法律理论。
(一)凯尔森:国家与法律的一元论
凯尔森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任何试图将国家实体化的理论,并进而主张国家和法律一元性。“国家作为一个法律上的共同体不是一个和它的法律秩序分开的东西,正如社团并非不同于它的构成秩序一样。若干人之所以形成一个共同体,只是因为一个规范性秩序在调整着他们的相互行为……共同体不过是调整个人相互行为的那个规范性秩序而已。”[5](P204-205)所谓“国家行为”只不过是特定法律规范归属于个人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意义),国家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法律规范所构成的法律秩序。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就转换为法律效力的最终来源问题。这个问题引发了凯尔森的规范体系的阶层理论,在体系内每一个法律规范的效力问题均可以通过向上回溯的方式得到证明,作为回溯的终点的则是“基本规范”[5](P130-132)。“基本规范”以诸如“宪法应当被遵守”这样的“当为”规定为内容,而至于为什么“应当”,则是被预设、不容追问的问题。
凯尔森明确地将国家置于法律之内予以考察,将国家问题转变成法律问题,从而开启了一条从规范性的角度理解国家性质的智识之路,这是其贡献。但其理论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陷,根本性的问题在于,由凯尔森的知识论立场及相对主义价值观所决定的基本规范的预设性质[6](P45-52),使其至多仅是说明了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应当)的纯粹性[7],“这种同一性学说具有定义-分析的意义,但绝没有法哲学-政治的内涵”[8](P183)。该法律理论是以彻底牺牲法律规范的内容与目的为代价来换取逻辑上的统一性,因此没能解释法律及国家的实际性质。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为了贯彻其法律一元论,任何一个“真正”的法律规范都被理解成规定制裁的规范,那些关于国家机关职权的规范也同样如此。“必须是两个不同的规范:一个规定机关应对国民执行制裁;另一个则规定,当第一个制裁并未被执行时,另一个机关应对第一个机关执行制裁……第二个规范使执行第一个规范所规定的制裁,成为第一个规范的机关的法律义务。”[5](P66-67)对法律规范的这种理解只能具有一种纯粹学术认知的意义,“为了换取令人愉悦的统一性……其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扭曲了不同类型的法律规则所具有之不同的社会功能”[9](P53)。
(二)哈特:以法律体系作为存在条件的国家
哈特在对待实体意义的国家观的态度上与凯尔森并无不同,“‘国家这个表达用语,并非指某种天生超出法律范围之外的人或事,它乃是用来指涉两件事实:第一,领土上的一群人,生活在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之下,此政府是由一套法律体系及其特有结构(包括立法机关、法院及初级规则)所规范;第二,政府拥有某种程度上定义模糊的独立”[9](P277)。因此,理解“国家”的性质的关键也同样是在法律体系的性质的解释上。
哈特在解释法律规则的效力来源的时候,提出了作为法律(规则)体系基础的一种特殊的法律规则——承认规则(a rule of recognition)[9](P123)。承认规则直接或间接地为所有的法律规则提供了“法律效力”上的证明,进而具备了鉴别何者是“法律规则”的功能。“承认规则”具体指哪些法律规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被称为承认规则的法律规则都必然具备两个特点:1.在一般情况及个案中确定特定社会中法律规则的范围;2.它自身的法律效力并不是来自其他法律规则的赋予,而是来自“事实”。
就第一个特点而言,在现代社会中,“承认规则”所指称的往往不止一个法律规则。它一方面包含了以“议会制定的就是法律”这样的规定为内容的法律规则,从而在一般意义上界定了该社会法律规则的范围;另一方面还可能包含诸如“新法优于旧法”这样的法律规则,在个案中确定了可被适用的法律规则的范围[9](P123-124)。至于这些作为法律体系基础的承认规则自身的法律效力来源问题,哈特既没有用某种事实上有支配力的主体来回答,也没有“预设”它的法律效力。而是把问题导向了规则的生效条件,或者说规则的存在需要满足的条件。
我们说,在英国“进教堂应当脱帽”是一个规则,而如此“断言”则源自两个事实:首先,普遍存在着一些规律性的“进教堂脱帽”的真实行为;其次,从事这些行动的人也认为应当如此,这种内心的态度也是通过“人们批评进教堂不脱帽的人”这个事实表现出来的。这两个事实就构成了一条规则的生效条件,我们可以据此主张存在着一条“进教堂应当脱帽”的规则,而不会说它只是纯粹规律性的习惯或个人的自律要求。
与此类似,作为规则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法律规则的“效力”(或者说“存在”)问题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被我们“认识”。与其他规则相比,法律规则的特殊性体现在:不要求每一个法律规则都必须具备这两个生效(存在)条件,而只要求其中的“承认规则”满足此条件即可[9](P141-145)。正如同一栋楼房的存在,只要求其第一层建立在地面上即可,而不要求其他楼层也要建立在地面上。这也就涉及了法律规则所独有的体系性性质。
哈特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律规则: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初级规则课以义务,针对人的行为提出限制性要求,如“故意致人死亡的,处死刑”、“公民生命权不受侵犯”;次级规则授予权力,针对法律规则予以确认、改变和执行,如“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因此它们也被称为义务性规则与授权性规则①。法律规则就体现为“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相结合”这样一种体系性性质,换句话说,作为法律规则的一种类型的初级规则,当其被次级规则所授权的机构或个人确认、改变、执行时,即已成为了法律规则;当存在着明确的“承认规则”时,改变规则、裁判规则也就具有了法律的性质。这也正是法律规则与其他类型规则相区别的一个明显特征。
承认规则作为次级规则中的一种类型,来自“官员”们的实践行为,从哈特的表述来看,“官员”指的主要就是“法官”。它为所有的法律规则提供了最终的并且统一的效力证明,其他的法律规则的存在无须诉诸事实,只需满足承认规则所提供的鉴别标准即可,进而承认规则使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所有法律规则形成一个有序的统一整体(法律体系)。在此有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法律规则一定要表现为如此这般的体系性性质,为什么不能像道德一样是分散的、进而所有的法律规则都体现出被接受的特点?其二,作为其他法律规则基础的承认规则来自那些被称为“官员”的人的实践活动,而“官员”又是由法律规则(改变规则、裁判规则)的授权而存在的,改变规则与裁判规则的效力(存在)又最终取决于承认规则,这是否意味着一种隐蔽的循环论证?
对于第一个问题,哈特提供了明确且有说服力的答案。哈特最初作了一个简单社会的假设,从简单社会的规则状况及其缺陷入手,引出了法律规则作为“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相结合”这个结论。但这更多的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分析-综合),并没有说明法律规则为什么必然是体系性的。有说服力的主张则在于其提出的“最低限度自然法”。哈特从五个与人相关的无可置疑的明显事实(人的脆弱、近乎平等、有限的利他主义、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理解和意志的力量)出发,有力地论证了作为一种体系性存在的法律规则对人而言的必要性[9](P247-253)。正是由于人的这些与生俱来的特质,使其不仅需要规则来初步规范、限制彼此的行为,更需要呈体系化的规则(法律规则)来满足人的更高、更复杂的要求。人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弥补缺陷,必然要求关于规则的确认、执行、改变的规则,当后一类规则出现时,这些规则以及由其而被确认、改变、执行的规则合在一起就具有了不同于其他规则的名称——法律规则。
第二个问题牵涉到法律规则之间发生关联的关系样式的独特性。对于那些可通过观察得知的事实来说,它们之间如果发生关系,这些关系必然是因果式的,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为因者在前,为果者在后。如“下雨”与“地湿”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而法律规则之间关系与此却不相同,首先,法律规则作为“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在时间上初级规则在先,但初级规则本身无法被称为法律规则,只有当出现了确认、改变、执行初级规则的次级规则时,它们合在一起才会被冠之以“法律规则”的名称。其次,在承认规则与包括改变、裁判规则在内的其他规则之间,也存在着相同类型的关系。承认规则的存在是典型意义的法律规则的标志,当通过观察某一社会中“官员”们的一贯行为,而确切地认定他们普遍性地遵循相同的鉴别应被适用的规则的范围标准时,我们就可以肯定“承认规则”的存在,进而宣称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典型意义上的法律规则(体系)。如果某一个社会中,尚看不出有明确的“承认规则”,我们只能说该社会中存在着非典型意义上的法律。一个社会革命后、被占领或新组建等时期就是明显的例证[9](P153-158)。
尽管哈特本人并没有把国家理论当做其理论重点,但客观上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观提供了典范,具有较强的实践解释力。法律规则中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在社会功能意义上的区分是其国家观的理论前提,所谓“国家”,需以公共机构(国家机构、政府机关)的存在及受其规整的特定地域的人群的存在为前提,而公共机构的存在又需要以特定的次级规则的授权为前提①。依此,公共机构依据次级规则得以存在,并依据次级规则的授权得以为该地域的人群界定行为的法律标准并维护这些法律标准的运作。
四、作为一种法律概念的“职权”
哈特的法律理论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法律理论论辩的核心议题之一,当然,也并非是无缺陷的理论[6]。但对于本文的论述范围而言,其已经提供了足够充分的理论依据。只要我们承认基于作为主体的人及其生存环境的特质而来的法律的“最低限度自然法内容”,那么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次级规则与初级规则就是所有成熟的、典型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结构要素②。以此为立足点,可以对“职权”的法律意义作出如下解释③:
第一,并不存在与职权相对应的义务。就规范目的而言,初级规则针对的是人的行为,进入法律规则视野的行为必然是涉他性的,这些行为意味着发生在多方主体间的一种关系。初级规则对关系中的主体行为予以限制,由此便形成了主体间的一种新的应然关系。这种应然关系往往以“权利-义务”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说,经初级规则认定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经常具有相关性。但这个结论却不能适用于次级规则,次级规则针对的是“法律规则”,它的本意是赋予特定主体排他性资格,以“确认、改变、执行”其他法律规则,当相关主体表现为“国家机关”这样的性质的时候,此类资格就可以表述成“职权”。这类规则就其规范目的而论并没有直接涉及任何行为(关系),更没有确立任何应然的关系状态,当然也就不存在“权利-义务”对应的问题。
第二,对不适当行使职权的主体的处罚是初级规则的要求,不是次级规则的应有之义。在本文第一部分讨论过的那个例子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88条很明显是以主体的行为作为对象的,其规范目的是为了避免滥用职权行为,属于一种初级规则。它不能被理解为对该条例第86条(授予职权的次级规则)在规范结构或者规范目的意义上的一个补充规则,原因在于,可能被处罚的只有作为个体的人,而交警队或交通警察不可能被处罚。这两个条文使用相同语词表述了实质上性质不同的主体,对此需要结合职权的第三个特点来说明。
第三,次级规则属于一种“构成性规则”(关于“调整性规则”与“构成性规则”的区分,见John R. Searle,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版, 第33~42页。有的学者认为所有的法律规则都具有“构成性”的特点。参见陈景辉:《合规范性:规范基础上的合法观念——兼论违法、不法与合法的关系》,《政法论坛》2006年第2期。不过这与本文的观点不冲突,差别在于说明的重点不一样。也可以说,笔者是在承认所有的法律规则都具有或多或少的“构成性”[或者说“人为性”、“规范性”]这个大前提下,区分其中的“调整性”与“构成性”法律规则。尽管哈特本人并没有明确地使用过“构成性规则”这样的概念,但从其将次级规则理解为法院等机关的存在条件上,可以将次级规则等同于构成性规则。),它是“职权主体”的存在前提,次级规则所赋予的职权不可能被所谓的“职权主体”(例如“交警队”)放弃。诸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6条中的法律规则,构成了“交警队”的存在条件,所谓“交警队”就意指着某些个人依照包括86条在内的一系列次级规则的组织与授权执行交通法规等行为的事实。当担任交警职务的个别主体背离了86条,其行为就不能视做“交警队”或“交通警察”的行为,其可能承担的责任或处罚与后者也就没有任何归属关系。正是基于这个理由,职权不可能被“职权主体”放弃,放弃职权的就不再是“职权主体”,职权“必须”被行使。
参 考 文 献
[1]刘星. 法理学导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沈宗灵. 权利,义务,权力[J]. 法学研究,1998,(3).
[3]郑成良. 法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张文显. 法哲学范畴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5]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6]陈景辉. 法律的界限——实证主义命题群之展开[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7]中山龙一. 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J]. 外国法译评,2000,(3).
[8]G.拉德布鲁赫. 法哲学,王朴译[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9]哈特. 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M].台北:(台湾)商周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李宏弢]
Why Authority Must Be Performed?
——Defense for the Legal Significance of “Authority”
YU Bai-hua
(Law School,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In our jurisprudence, there is a connotation concerning courts and such offices whose authority “must be performed”, due to the reason that “if not performing it, it is against its legal duty and will be punished.” There is a state (office) concept behind this explanation which is independence of law”. On the one hand, this is a kind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 on the other, it is against the generally accepted idea of rule-by-law. Therefore it calls for a national concept in accordance with idea of rule-by-law, and a re-explanation of the legal nature of authority should be based on it, which lead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al conception of authority.
Key Words: authority; national concept; rule-by-law; secondary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