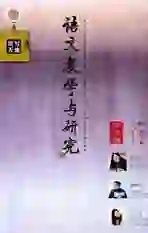惟妙与惟肖
2009-05-25叶彬
叶 彬
模仿的极致,是惟妙,而不是惟肖。
惟妙,一种减法,减去肤浅,减去累赘,减去繁复;
惟妙,一种加法,加上独到,加上创新,加上光芒。
钱钟书曾在《宋诗选注·序》中,对于宋人与明人学唐诗,有过一段著名的话:“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惟肖而不惟妙,像唐诗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
所以,当你想要模仿一个春天,你只要模仿一朵盛开浓烈的杜鹃花,绽放在逐渐结成绿野的山头,你甚至可以找到春的心脏脉动。
当你想要模仿一名品茗者,你只需几枚落叶作香茗,一朵百合作杯盏,一只温暖的手掌作红泥小火炉,轻啜一口,你甚至可以品到整个世界的芬芳。
当你想要模仿一支民间乐队,你只需举起手中的五月麦芒,十月稻穗,为竖琴,为琵琶,让花喜鹊指挥乡间音乐,你甚至可以听到河流的歌唱和农民的欢庆。
你需要极其敏感的嗅觉,嗅到你所欣赏的物、人、事的本质的精淬,然后融入自己的内心,化为自己的财富;你需要极其独到的眼光,窥测到其外表后的灵魂高度,思想深度,然后提炼、酝酿,去构成自己的一份气质;你需要极其锐利的思维,深入到一缕月光的内心,一朵桂花的幽柔,一片叶子的呼吸,然后借风飞翔。绝不是东施效颦,绝不是沐猴而冠,而是那海棠,“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香”;而是迈克尔·杰克逊,改良了在纽约街头流行的舞蹈,神奇地创造了太空舞步;而是著名影星霍夫曼对自己大声说“你不是卓别林”!
任何追随崇拜和盲目的模仿,都是失去自我的迷药。当小沈阳只用酷似的模仿想要一招吃遍天下时,当太多人迷失在欧美时尚、倾倒在韩流里,光芒就这样殒落,个性就这样模糊,你的生命轨迹就这样时隐时现,试问你的人生价值,只是去重复别人的脚印吗?
一幅写意朦胧的泼墨山水画,还是一张清晰可辨的风景照片?惟肖还是惟妙?答案很清楚很明确。去收集山水之灵气,去聚集日月之精华,去展开自己富有魅力的触角!
你若是那诗人,去取得两分易安的婉约,两分稼轩的豪放,一分老庄的淡泊,剩下的留给自己的想象;你若是那音乐家,去取得两分贝多芬的狂热,两分阿炳的凄怆,一分莫扎特的动情,剩下的留给自己的思考!
叶彬,浙江华维外国语学校学生。
如果你今年二十二岁了,但还在模仿别人,那你就完了。
模仿似乎是人类的本性,甚至可以说是很多生物的本性。看看动物世界吧,小鸭子一个个排成队地跟在母鸭子的屁股后面,从划水的速度到伸脖子的节奏,活脱脱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于是,初生时的模仿在生命的长河里划下一条温柔的弧线,鸭子们是这样,人亦是如此。所以,女孩子会在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穿上那大得不合脚的高跟鞋,再笨拙地往嘴巴上抹上浓浓的口红,偷偷在镜子前摆上几个自认为是大人的姿势。我们总是在试图模仿父母的样子,因为那是我们渴望达到的境界。但是,我们所能模仿的只是他们穿着的样子和讲话时的口气。他们那一个个因为工作上的不顺而难以入眠的夜晚,还有那一声声因为生活中的无奈而发出的长叹,这都是儿时的我们所无法理解的。如果有一天,当我们在模仿他们的日子里突然加入了这些思考,那么,恭喜你,小朋友,你已经不是在模仿他们了,你已经长大。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回想原来的自己,那些似乎只属于父母间的想法,那些我们曾经无法理解的行为和决定,慢慢地在模仿的日子里渐渐变为习惯。当那一天来到,我们从模仿他们到变为他们,过去的某些回忆也就那么的好解释了。
所谓的青春期其实很短,有些东西突然间想清楚了你也就长大了,回不去了。所以,那些模仿完父母开始模仿别人的日子其实也不长。当然,这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选择在充满幻想和躁动的青春期里多待几年,于是他们今天模仿安娜·卡娜琳娜恨不得明天就去赴死,而后天又决定学习藤井树把自己的感情画进谁也不知道的卡片里。最终,他们都在模仿的日子里一去不复返了,再难看到自我,也难看到明天。所以,末了,是成为顾城还是海子,那只是个死法的问题。然而,大家都承认,青春期是痛苦的,既然如此,何不早点结束它呢?王小波不就是在青春岁月里彻底结束了自己的青春期,成为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日后也就成就了特立独行的王小波?所以说,与其盲目地模仿那些不切实际的幻觉,还不如模仿最本真的自我,或是模仿理想中的那个自己。模仿别人是没有止境的,只有开始崇拜自我了,才可能给别人一个模仿你的机会。
模仿的日子就是生命的每一天,永远不会停止。但至于模仿谁,为什么而模仿,那就不一定了。
苏也,武汉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