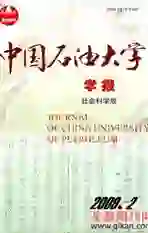思想焦虑与书写愉悦
2009-05-22陈小林
陈小林
[摘要]出于对《红楼梦》影响的焦虑,《儿女英雄传》通过儿女、英雄的叙事内容及严谨结构力图论证在社会秩序内建构自我的必要性,但它所沉迷其中的戏拟传统、建构自我的书写愉悦反而从秩序和自我两个方面质疑了它本身的论证。
[关键词]《儿女英雄传》;《红楼梦》;思想焦虑;书写愉悦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2-0086-(05)
以往的批评者对待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的态度堪称两个极端:一方面,论者对它的思想内涵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贬斥,另一方面,它的艺术成就却得到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赞叹。这种评价表面看来既公允又全面,可惜却忽视了作为主体存在的文康和作为整体存在的《儿女英雄传》,因而势必“难解其中味”。
笔者试图探讨思想内涵与书写策略在《儿女英雄传》里所表现出来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出于对《红楼梦》“影响的焦虑”,文康创作了一部关涉儿女和英雄叙事的《儿女英雄传》,他希望在两个层面上实现对这种焦虑的消除——是力图论证“自我”(指小说人物形象,也指现实社会的人)理应且必须在秩序内得到建构,从而削弱《红楼梦》的叛逆思想对现实秩序所构成的巨大破坏作用;一是力图在《红楼梦》之后为《儿女英雄传》争取历史地位,从而实现自我价值。可当文康沉迷于戏拟小说传统、建构自我形象(指小说人物形象,更指作者文康)的书写愉悦之中时,他的后一努力质疑了前一努力的必要性,《儿女英雄传》也得以成为一部难以简单评价的小说。换句话说,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恰是以一种迂回的书写策略一方面拉近了《儿女英雄传》和《红楼梦》之间本来会更远的思想距离,另一方面使得《儿女英雄传》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中国小说史,从而吊诡地验证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句古训。
一
研究者普遍重视《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的比较,但一味通过揄扬后者来贬抑前者的做法不足为训。与其简单复述“《儿女英雄传》不如《红楼梦》思想深刻”这一人人皆知的事实,倒不如追问:文康如何利用《红楼梦》创作了自己的小说,以便能够消除《红楼梦》影响的思想焦虑?答案是:对“情”重新进行定义。
(一)“情”的重新定义
《红楼梦》“大旨谈情”,这个“情”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主体人格意识的任情,即自由心性;一是作为生命存在方式的情性,特指爱欲(狭义之情,指男女性爱和爱情)和爱心(广义之情,泛指以爱为本原的亲情、友情、同情等人的美好情性)。前一内涵立足于自我,强调自我和秩序的分裂,并要通过这一分裂来强化个体自我的“真”;后一内涵则包括了性的意蕴,《红楼梦》尤其重发泄“男女之真情”。“情”的这两层内涵对秩序都是一种挑战,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为消除《红楼梦》这一思想的影响,文康采取了两种改写策略:
首先是指鹿为马,亦即采取儒家的阅读眼光,从根本上否认《红楼梦》的“大旨谈情”,把《红楼梦》拉入“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序列。在那篇伪托观鉴我斋所写的序文里,文康认为“曹雪芹见簪缨巨族、乔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载福、承恩衍庆,托假言以谈真事,意在教之以礼与义,本齐家以立言也”,“《红楼梦》,其显托言情、隐欲弥盖其怪力乱神者也”,所以他感慨“《红楼梦》至今不得其人一批,世遂多信为谈情,乃致误人不少”。在小说正文里,文康又将自己塑造的几个人物形象与《红楼梦》的人物形象逐一比较,然后用激烈的批评语气说道:
“曹雪芹作那部书,不知合假托的那贾府有甚的牢不可解的怨毒,所以才把他家不曾留得一个完人,道着一句好话。燕北闲人作这部书,心里是空洞无物,却教他从那里讲出那些忍心害理的话来?”(第三十四回)
这是文康读出来的《红楼梦》,基于此种读法,文康在那篇序文里宣称他的小说是“格致”之作,以与《红楼梦》的“修齐”争胜(在儒家思想序列中,“格致”处于最先的位置)。这一读法典型地流露出文康对于《红楼梦》“情”的思想的焦虑,当然也体现了文康消除此种焦虑的努力。
其次是偷梁换柱,亦即以“理”和“礼”置换“情”,取消“情”的上述自我和性的两层内涵,牢牢地将“情”定义在秩序许可的范围内。在“缘起首回”里,文康开宗明义,借帝释天尊之口畅论他心目中的“儿女英雄”和“天理人情”:
“这‘儿女英雄四个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两种人、两桩事:误把些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儿女。所以一开口便道是‘某某英雄志短,儿女情长,‘某某儿女情薄,英雄气壮。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
文康确信并且希望读者也确信,儿女真情和英雄事业出自天理人情,也必须在天理人情的统摄下才能实现、才有意义,换言之,自我和秩序是统一的,个体自我的“真”应该且必须在秩序内进行表达。在文康看来,儿女和英雄是统一的,儿女英雄和天理人情也是统一的,而这个统一就在于“没得一毫矫揉造作”,亦即“真”。所以文康在别处又借何玉风之口议论道:
“大凡人生在世,挺着一条身子,合世界上恒河沙数的人打交道,那怕忠孝节义都有假的,独有自己合自己打起交道来,这‘喜怒哀乐四个字,是个货真价实的生意,断假不来。”(第十七回)
文康没有舍弃“真”,却视“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天性人情”,这表明他要在自我和秩序(伦理秩序、家国秩序)的狭缝间实现双方的“共赢”——自我得以健康地成长和完满地实现,秩序也能够达到稳定与和谐。无疑,《红楼梦》对自我的强调被文康适度削弱了。
剥离“情”的性内涵的议论则出现在小说第二十六回,叙述者在这一回中解释何玉凤不知红匣子里装的就是宝砚和雕弓,说何玉风“本无那些无来由的私意,叫他从那里用那些不着己的闲心去呢?这却合那薛宝钗心里的‘通灵宝玉,史湘云手里的‘金麒麟,小红口里的‘相思帕,甚至袭人的‘茜香罗,尤二姐的‘九龙佩,司棋的‘绣春囊,并那椿龄笔下的‘蔷字,茗烟身边的‘万儿,迥乎是两桩事”。显然,文康有意识地把作为婚姻象征符号的宝砚、雕弓与《红楼梦》里作为私欲象征符号的各类饰物区别开来,由此批评《红楼梦》,以取消“情”所包含的性的意蕴。
(二)改写的叙事呈现
《儿女英雄传》对《红楼梦》的改写呈现于小说文本,则是具体围绕叙事结构和叙事内容而展开。通观整部小说,《儿女英雄传》的儿女、英雄叙事被精巧地安排为五个段落:第一回至十二回叙安骥在十三妹的帮助下与父母团聚,并娶得娇妻张金凤;第十三回至二十回借安学海寻访故人之女揭开十三妹身世之谜;第二十一回至二十八回叙弓砚佳缘;第二十九回至三十六回是龙媒正传,叙安骥在两个妻子督促下及探花第;最后四回讲述整个家国秩
序的恢复。整饬的叙事结构从形式上对应着文康要论证的观点,即自我应在秩序内建构,一如叙事需在严谨的结构内展开。
倘若深入到各个段落便会发现,儿女英雄们不仅要在小说严谨的叙事结构内腾挪,更要依凭自我的“本真性”在“理”和“礼”所代表的秩序内行动,从而臻至“他化自在天”的人生境界,即自我和秩序“共赢”的自由境界。
第一个段落将传统侠义小说惯用的“侠士救美”模式改成“侠女救美”故事,“侠女”自然是化名十三妹的何玉凤,“美”则既指张金凤,也指过于女性化的安骥公子。单就这个故事本身看,巧合的确过多(譬如华忠突然生病,十三妹恰好听到骡夫的谋划,还有那掉落的铃铛和草帽也太凑巧),但三位主角符合“天理人情”的真性情无疑成了小说之所以这样写的最好理由,借用书中何玉凤的话,“这便是你二人一个孝心,一个节烈所感,天才牵引了我来。正不是一桩偶然的事”(第八回)。安公子的孝心表现在一知道父母有难,便可抛弃博取功名的机会,不顾危难,千里送银;张金凤不委身淫僧是其节烈,两人得救理固宜然。十三妹见人落难,不辞“杀了一晚”,救人性命,所以第五回回目有“侠女重义更原情”之说。另外不可忽略,小说详写十三妹救安骥时如何解开绳索、如何用弓搀起走不动的对方、又如何在杀死老和尚之后瞬间耳热脸红,也提到安公子因衣服稀烂而“宁可失仪,不可错步”的细节,如果不是为了表达小说人物及作者对“礼”的过分关注,大可不必如此。
揭开十三妹身世之谜是小说第二个段落的重头戏,这可视为对公案小说的戏拟,不同的是安学海查访故人之女不关涉办案,而是为了报恩。作为对十三妹救安公子的呼应,安学海最后“设局赚侠女”,用一套有关孝道的激烈说辞挽救了已有死志的十三妹。这八回情节可谓关键,就安学海而言,是“认定天理人情抛却功名富贵,顿起一片儿女英雄念头”(第十四回)而采取了行动;对十三妹来说,则既是她向“何玉风”转变的契机,也使她跨入“他化自在天”的境界有了可能:身世之谜的解开意味着何玉凤更加的“真”,她由此能够进一步领会“儿女即英雄,英雄即儿女”的要旨,以获得了新的伦理生命,而惟有领悟这一玄机,她从侠女到贤妇的转变才无需怪讶。
接下来的两个段落转向才子佳人主题的叙述,这个主题最适合与《红楼梦》对读,也最能体现文康力图把自我情感约束在理和礼的秩序范围内的书写策略。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戏曲的借鉴同它对才子佳人小说戏曲的批评一样醒目,所以《红楼梦》叙述了一系列的浪漫爱情故事,提到了一系列作为爱情信物的饰物,但在“情”和“淫”之间,《红楼梦》似乎难以做到严格区分。《儿女英雄传》交代说“从这二十一回起就要作一篇雕弓宝砚已分重合的文章,成一段双凤齐鸣的佳话”,这句预告才子佳人故事的话头显然大打折扣,除“双美事一夫”模式多少可见才子佳人故事的痕迹之外,“双凤齐鸣的佳话”与才子佳人故事乃至《红楼梦》都存在差异,最大差异就是“情”在弓砚佳缘这出戏里所占戏份大大少于“理”和“礼”。传统才子佳人故事固然讲“理”和“礼”,却从不曾忘记“情”的张扬,而《红楼梦》简直是要以“情”反“理”、以“情”反“礼”了。但《儿女英雄传》的“情”被控制在理和礼的范围内,作为婚姻信物的雕弓、宝砚以其公共性质显示了与《红楼梦》里手帕、香囊等私密信物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弓砚佳缘似乎是由周围的热心人按照“理”和“礼”促成的,当事人之前并无私欲。小说先让何玉凤已故的父母托梦,意味着有了父母之命,接着写张金凤的“灿舌如花”如何令何玉凤“顿悟良缘”,表现何玉凤战胜狭隘自我的过程,最后不厌其详地描写“宝砚雕弓完成大礼”的情景(第二十八回);即便是婚后,小说也不忘写双凤如何操持家政,如何督促夫君向学并及探花第。这和才子佳人故事“一见钟情一传诗递简—偷期密约一洞房花烛”的四部曲模式显然有较大区别。总之,自我情感在《儿女英雄传》里是符合“理”和“礼”的,自我被要求和秩序结成统一体,这既不同于《红楼梦》的情感充沛,也与才子佳人故事侧重“发乎情”而只点缀似地表现“止乎礼”迥异。
作为对儿女英雄们的回报,小说第五个段落讲述了整个家国秩序的恢复,安骥被任命为山东观风整俗使,双凤各有身孕,邓九公以九十高龄生得二子,安学海在山东重演了《论语》中的场景,甚至连谈尔音这样的贪官也悔悟了(这可与第二十一回“回心向善买犊卖刀”对读)。简言之,儿女英雄们在秩序内完满地实现了自我。
显然,出于对《红楼梦》影响的思想焦虑,《儿女英雄传》试图通过对“情”的重新定义证明作者所要证明的观点,即自我理应并且必须在秩序范围内得以建构,小说的确从叙事结构和叙事内容两个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正如笔者将在下文分析的那样,文康并没意识到,他的这一努力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被他自己的另一种焦虑及由此而生的书写给抵消了。
二
马从善的序文推测文康的创作动机是“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这大有深意:创作一部虚构理想家庭的小说固是“抒其未遂之志”——通过幻想安慰“垂白之年重遭穷饿”的自己,创作小说这一行为本身岂不也是“抒其未遂之志”?——不能立德立功,不妨立言以求被后人追忆。问题是:在《红楼梦》之后,这一立言何以可能?《儿女英雄传》在许多地方仍走不出《红楼梦》的艺术藩篱,但在为自己及小说争取一定历史地位这一心理焦虑的驱使下,文康至少在叙事方式上有自己的独特性——这恐怕也是论者对其艺术赞赏有加的原因。
(一)戏拟传统的书写
从《儿女英雄传》的内容看,文康无疑非常了解传统的小说和戏曲,也关心流行的最新小说,过于了解小说传统有时会束缚小说家的想象力,但对于一个爱拿小说惯例开玩笑的小说家来说,这样的了解“多多益善”。在《儿女英雄传》里,戏拟传统的书写愉悦不仅让作者沉迷其中,也会使读者因阅读的愉悦而时时露出会心的微笑吧。
如上所述,《儿女英雄传》至少戏拟了三大小说类型的传统:侠义小说、公案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在长篇说部里,如此广泛的戏拟比较少见,它所带来的书写愉悦令人感同身受。戏拟小说传统不同于小说类型的合流,类型合流的小说文本仍可分清主流和支流,仍可归属于某个已有的小说类型,戏拟传统的小说文本则无所谓主从,很难再将它纳入它戏拟的某一个传统。这意味着,高明的小说家可以通过戏拟小说传统来创造传统。《儿女英雄传》的难以分类及其最终被视为儿女英雄小说的开山之作,道理即在此。
同时,《儿女英雄传》对小说评点传统也有大量的机智戏拟。小说评点虽是针对一部具体的作品,但从形式上看,它和小说的正文是分开的,一般也不是小说作者本人所写。文康的卓异之处在于,他本着戏拟的态度,利用叙述者的声音将小说和小说评点交织起来写,以小说正文纳小说评点,以自我评点
代他人评点,《儿女英雄传》由此获得一种别样的叙事风格。譬如第二十九回让“说书的”就作者安置那个长生牌的文字进行点评,在设身处地地为作者设想了几种法子之后,“说书的”评论道:“大约那燕北闲人也是收拾不来这一笔,没了招儿掳了汗了,就搜索枯肠,造了这一片漫天的谎话,成了这段赚人的文章!”这表面看来是讥讽,其实是作者点破自家伎俩的狡诙之笔,章法颇为新鲜灵活。
当然,这些进入正文的评点更多的是对小说情节安排、穿插之佳的点评,如下面的这段话:
“这部书前半部演到龙凤合配,弓砚双圆,看事迹,已是笔酣墨饱;论文章,毕竟不曾写到安龙媒正传。不为安龙媒立传,则自第一回‘隐西山闭门课骥子起至第二十八回‘宝砚雕弓完成大礼皆为无谓陈言,便算不曾为安水心立传。如许一部大书,安水心其日之精,月之魄,木之本,水之源也;不为立传,非龙门世家体例矣。燕北闲人知其故,故前回书既将何玉凤、张金凤正传结束清楚,此后便要入安龙媒正传。”(第二十九回)
这自是叙述者在评点小说结构,但似乎更应视为文康在向读者全盘托出他的创作思考,读者由此更易体会小说的结构之妙。
文康以自作小说评点的方式加强了与读者的直接联系,同时也告诉读者:《儿女英雄传》只是一个精心构造的小说文本,除了虚构行为本身,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的,这使《儿女英雄传》达到了传统说书体叙事所追求的真实情境。
(二)建构自我的声音
如果说戏拟传统是文康乐此不疲的一种书写策略,那么在传统说书体叙事模式里翻出新鲜花样也可以说是文康追求书写愉悦的又一个体现吧。翻新不仅仅为了体验书写的愉悦,它也是文康借以消除对《红楼梦》影响的心理焦虑的手段,显示文康建构作者的自我形象的努力。有论者认为:“《儿女英雄传》所体现的小说观念,至少有一点是倒退的,那便是向说书体的复归。”这一看法不能让人信服,笔者认为《儿女英雄传》不是向说书体的简单复归,毋宁说是对传统说书体的一种提升,如果不是采取说书体叙事模式,《儿女英雄传》“可看可说,能够雅俗共赏”的优点不可能形成。当然,《儿女英雄传》的这一优点是对《红楼梦》影响的心理焦虑的产物。《红楼梦》属文人小说,精致复杂,虽称“雅俗共赏”,终究不能通于里耳,更无法做到“可看可说”,即便是摆在案头,文学修养不高的读者也难以领会,《儿女英雄传》虽说具备文人小说的结构技巧,整体叙事风格却是大众化的,风趣易懂,可读可听,容易引发读者的兴味。一言以蔽之,通过运用说书体叙事,文康显然要在《红楼梦》之后“另张艳帜”,实现为自己的立言追求。
立言就是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声音,而在小说文本层面,文康又巧妙引入各种声音,利用这些声音的有趣交织来建构自我。传统说书体叙事只注重说书者和听书者的交流,但在《儿女英雄传》中,说书者和听书者的交流固然仍是虚拟说书情境的关键手段,作者、说书者、书中人物之间的交流则似乎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作者形象。
在“首回缘起”里,文康仿照《红楼梦》为《儿女英雄传》编造了一个文本史,但与《红楼梦》不同,作为作者(即“作书的”)的燕北闲人多次现身于文本(“曹雪芹”这个名字只在开头和结尾出现过),叙述者(即“说书的”)频繁插入的喋喋不休的“闲话”经常打断叙述的进程(《红楼梦》的叙述者很少直接出面干预叙述)。笔者以为,“作书的”和“说书的”都是文康的化身,文康利用叙述者和小说人物的声音(“作书的”基本上处于被说的地位)建构了两个自我形象:一个是“一生也不曾作得一个好梦”、只能惨淡经营小说艺术的焦虑者(对《红楼梦》影响的焦虑),一个是沉迷于讲述故事的愉悦之中的说书人(也即沉迷于书写愉悦的文康)。
“作书的”原本理应是小说文本世界的说者(小说文本由他创造),但现在他成了被说的对象——被“说书的”说,也被小说人物说。当说者被说的时候,说者的形象(也就是作者文康的一个自我形象)得以建构。不同于传统的说书体叙事,《儿女英雄传》的人物不再被禁闭于小说的叙事世界,他们会因为担心让“说书的”和“作书的”为难而采取或放弃某些行动,这是“作书的”被小说人物说。譬如第九回,十三妹要离开能仁寺,她向张金风说的第三个理由竟然是“好让那作书的借此歇歇笔墨,说书的借此润润喉咙”。又如小说第二十一回解释安家人没在邓家庄留宿的原因,就让褚大娘子说体贴自己的辛苦“这还都是小事。这回书再要加上写一阵二十八棵红柳树的怎长怎短,那文章的气脉不散了吗?又叫人家作书的怎的作个收场呢?”这种笔墨新颖别致,突破了传统说书体的模式,可以说是文康的夫子自道——提醒“列公”体会作者的匠心独运,建构一个虽然惨淡经营却不乏创新勇气和创作才气的自我形象。而更多场合是“说书的”说“作书的”,意在评论小说作者的叙述技巧,这些评论在建构作者的自我形象方面作用不小,譬如下面的这段话:
“只可怜那作《儿女英雄传》的燕北闲人,这事与他何干,却累他一丸墨是磨灭了!一枝笔是磨秃了!心血是磨枯了!眼光是磨散了!从这书的第四回‘末路穷途幸逢侠女起,被他没日没夜的磨,磨到第二十八回,才磨得‘宝砚雕弓完成大礼。……不亏这等一磨,却叫他怎的夜磨到明,早磨到晚!”(第二十八回)
一个“磨”字,可谓道尽创作之苦,也提供了一个煞费苦心去“消这闲岁月”的“闲人”形象——这中间自然浸透着文康对于自己诸事无成、“家道中落”的喟叹。这里,文康要利用叙述者的声音向“列公”倾诉他的创作艰辛,有点自我解嘲的味道,读者从中看到一个为消除心理焦虑而全力以赴的小说家形象。
“说书的”是小说文本中最活跃的一个角色,他自由地驱使小说人物,愉快地与“列公”(听书者)交谈,深有体会地赞扬燕北闲人的苦心孤诣之处,他不必像燕北闲人那样“守着一盏残灯,拈了一枝秃笔”,“出那身臭汗”,他轻闲而愉悦,只需把现成的故事讲述给“列公”听,他可以发表一通关于“吃醋”的“迂腐之论”(第二十七回),也可以“忽然想起一个笑话来”(第二十四回),他可以在紧要关头极有耐心地插入额外的闲话(第六回),也可以用“著书的既不曾秉笔直书”作为理由而不说闺房琐事(第三十一回),甚至可以暂时抛开故事与听书的人一起训诂一个词语(第四回)。总之,他总可随时出现在他愿意出现的地方,随心所欲地讲述他愿意讲述的内容。如果说“作书的”代表了文康苦于创作的一面,那么“说书的”则代表了他乐于创作、沉迷于书写愉悦的一面,这岂不是正好一道建构了一个深谙创作甘苦的作者的自我形象?
以上分析了戏拟传统和建构自我在《儿女英雄传》中的体现,这两种方式都有新颖之处,保证了这部小说能在《红楼梦》之后进入小说历史,甚至能构成传统本身,换言之,文康对《红楼梦》影响的心理焦虑是有所消除的。但当文康朝这个目标行进的时候,他的行进方式不自觉地质疑了他要力图论证的“自我理应且必须在秩序内建构”这个观点:首先,通过戏拟传统(实即轻视秩序)来显示小说叙事的独特性,这意味着秩序并不是非遵循不可,秩序的无上权威至少是被动摇了;其次,通过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巧妙偏移,文康建构了鲜明的自我形象,这难道不说明自我的建构不在严谨的秩序内也能够实现?事实上,文康吊诡地使得自己消除焦虑的两种努力既互相契合又相互抵消。
综上所论,《儿女英雄传》所包含的意图和策略之间的相符及分歧情形需要仔细辨析,这是在评价这部小说之前要慎重面对的问题。这与其说是本文的结论,倒不如说是本文的态度。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