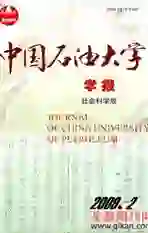“神灵音乐”、“人伦礼乐”的变迁与音乐理性回归之始
2009-05-22孙旭辉
孙旭辉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厘定,是学术界较为缺少研究热度的一个问题。以传统音乐观念及理论为考察对象,从中抽取传统音乐本身社会角色演变的痕迹,在描画这一流变轨迹的同时挖掘深层次的哲学、美学支撑,是切入的主要思路。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变革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神灵音乐”向“人伦音乐”的转变,即上古神灵崇拜意识下的神性音乐到先秦、两汉儒家“礼乐”观;其二,魏晋六朝以“声无哀乐”论为代表的音乐理性的建构,以及由此对原始儒家“人伦音乐”的革新。
[关键词]音乐;神性;人伦;理性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2-0075-(06)
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历史已经很长了,近年来,这一研究更是呈现蔚为大观的景象,其范围涉及传统音乐技术、音乐表意符号、民族及地域音乐资源的开拓以及新的音乐考古资料的发掘等。这些已有的成果和积累使人们有了进一步反思和总结的意识和理论基础,同时,也促使人们发现了崭新的研究思路生发点。而对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厘定,就是其中之一。学界对此问题尚且缺少研究热度,笔者尝试以传统乐论为资源,梳理其中蕴含的音乐社会身份流变之迹,同时,在描画这一流变轨迹的同时挖掘更深层次的哲学、美学支撑。
一、“神灵音乐”的起点
“神灵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起点,源自上古社会有神论与自然哲学的杂糅。神性与宇宙自然的杂糅是上古时期音乐的基本样态,反映出上古时期初民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的多样化和变动性质。自然哲学维度的渐至明朗决定了“神灵音乐”将最终走向原始儒家的人伦礼乐。“神灵音乐”的特征可概括如下:
首先,“神灵音乐”具有强烈的娱神职能。上古神灵崇拜及神化世界的观物方式,衍生出“万物有灵”的观念,认为世界物象都处于潜在的神灵意识支配之下,从而也决定了上古音乐的娱神特征。生民与自然之间充满了人类原始时期浓重的自然神崇拜气氛,以及无所不在的“万物有灵”观念。“万物有灵”的自然宗教意识,使生民视野的周遭世界在静谧之中充满了灵动和神秘,成为流动、变化、循环不已的“神灵化”空间。“乐”则携带着“音”、“声”、“乐”,以“巫”或其他类似的自然宗教仪式,成为先民寻求与宇宙旋律应和的合适中介,以致将宇宙变成一个发出音乐的宇宙,把音乐变成了宇宙的摹本和代表。《易传》有所谓“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之说,“荐”和“享”就显示了初民对音乐所具有的通神和娱神作用深信不疑。又如: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蹉,凶。
这里,人事与天象形成了对应,“辰不集于房”、“日昃之离”等都具有了一定的隐含意义及预示作用,而初民首先的反应,便是“奏鼓”、“鼓缶而歌”等,神的意志与人的观念通过音乐相互沟通,形成一致。
“乐”的娱神和通神作用,使初民将对“神”的敬畏和膜拜部分地转移到了“乐”,这种由“神”到“乐”的移情,使上古之乐成为初民寻求与神灵化自然融合的方式之一。初民由此实现了在“乐”之中的神性栖居,“乐”也获得了超出音乐自身意义的价值。“乐”为娱神即为观念中人和神的沟通而存在,实际上意味着音乐被赋予了神性的品质,被神性所规定。在此意义上,音乐是作为初民神灵崇拜的中介而存在的,其意义首先在于成为神性的外化体现,音乐的本性蒙蔽于上古时期强大的神灵崇拜氛围中。
其次,上古时期的观物方式除了“万物有灵”论以外,也包含着原始朴素自然观的萌蘖,“自然”的域界趋于多样化。其中重视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与音乐相比类,也成为上古音乐观念的又一走向。人们逐渐开始从自然方面探讨音乐的起源,以自然的属性来界定音乐的属性。自然因素的上升,意味着对“乐”的神性因素的祛味,为乐论进一步向人的敞开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在上古“娱神”之“乐”与春秋战国儒家重人的“礼乐”之间,自然之乐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对自然物象这一感觉对象的把握,决定了音乐的角色及其变化。起初,初民直观地感受到天地自然之和是自己生存的理想状态,以“乐”完成与宇宙旋律的对应,如同宗白华先生所言:“中国的广大平原的农业社会却以天地四时为主要的环境,人民的生产劳动是和天地四时的节奏相适应。”其后,人们审美心理中对自然的感知发生变化,开始从自然神学观念转向将自然视为和谐有序的生存环境与认识对象,更多地认识到音声变化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又在音乐的社会功能问题上提出“省风”和“宣气”的新主张,为中国传统审美经验中的“比德”模式埋下了伏笔:
天子省风以作乐……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
对神学意义之天的怀疑,引发了深层美学精神中人本意识的萌发,这为中国音乐美学乃至审美文化中的自然主义品格的初露端倪提供了审美经验的深层支撑。
上古时期音乐观念是基于其“自然”观之上形成的,而其自然观又融合着宗教与物理的双重涵义,从而决定了此间音乐观念的双重性质,即兼具神性与宇宙自然性。这使上古浓郁的原始宗教氛围,始终保留有自然的因素,自然甚至可以成为祭祀等原始宗教活动的目的所在——人们希望以宗教的方式达到与宇宙自然节奏的和谐一致,实现自身力量的想象性延伸,获得个体安全感并安慰自身心性。如果说自然既是原始宗教崇拜中的神性的“自然”,又是初民试图去认识并与之相融的物理的宇宙自然,那么音乐就既是神灵崇拜的宣泄,又是对未知物象世界的好奇流露。
二、“人伦礼乐”的内核
以原始儒家道德本质主义为标杆的礼乐思想的逐步确立,成为这一阶段中国传统乐论的主要特征。经由儒家道德本质主义的规范,传统音乐获得了与西周时期接近的“礼乐”的内核,由先秦至两汉,礼乐观成为指导个体行为和群体价值的必备途径:对个体而言,礼乐是达到“君子”人格的必要修身方式;对群体而言,礼乐又是实现儒家“德政”政治理想的关键因素之一。以先秦儒家礼乐观的音乐理论为起点,到两汉时期,传统音乐作为个体及群体实现价值目标的途径,逐渐进入政治和日常社会生活的主流。
始于孔子而以《乐记》为高峰的先秦儒家“礼乐”音乐思想将音乐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联系紧密,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现实指导特征。具体可由以下三个方面阐释:
首先,“礼乐”思想是儒家整体音乐观的基础。礼乐结合相生,指导着个体修身与人格的完善。儒家乐论中,乐与礼密切相关,成为强化礼制的重要手段。儒家之礼依据以“仁”为核心的政治和社会伦理,礼乐统一即理与情的统一,以理节情。礼辅以乐,乐受礼的制约和引导,诗、乐、礼完整统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及其包含的政治、伦理因素成为乐和诗的唯一评判标准。而主张“为政以德”的“德政”观无疑是原始儒家礼乐思想
的最集中体现。《论语》中对“德政”之政治理想的渴盼为数甚多: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对曰:“荀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可见,在原始儒家那里,统治者具备良善道德是保证实现“德政”的前提。而这又涉及到了儒家礼乐观的第二个层面,即个体君子人格的培养。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儒家对个体修身的重视可见一斑:对于“为人谋”者,儒家提倡“忠”;对于“与朋友交”,则提倡“信”,且还强调了“习”的重要。忠、信、习成为儒家崇尚的“君子人格”的典型特征。在第二则材料里,儒家确定了个体修身中《诗》、礼、乐的顺序,即只有从最基础的《诗》习起,继而上升到理智居上的礼的阶段,并最终达到游刃有余的乐的层面。如果说《诗》是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基础,“礼”是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保障,那么“乐”便成为其最终的目标和境界所在。
其次,“乐教”论是儒家整体音乐观的现实目的。“乐教”论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主张通过潜移默化式的音乐审美过程,来实现个人的自身修养,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融入儒家之“仁”的内核。涉及社会层面,“乐教”论主张“移风易俗,非乐莫属”,即认为音乐对社会风尚而言,是有效的教化工具,为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孔子认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认为音乐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个体可以通过音乐艺术的欣赏与审美,获得审美自由与精神愉悦,促进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培养的完成。同时,这种个体获得的审美自由与精神愉悦,又帮助其从理性的道德完善和修身行为中解脱出来,使之变成自觉的行为。这种对道德本质主义的促进作用正是儒家无比强调音乐的原因所在。
最后,“中和”思想是儒家整体音乐观的审美原则。孔子强调“以礼节乐”、“以乐释礼”,同时提倡情感与音乐之间的和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声以为节”,从而达到“质”与“文”的和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孔子乐论中的“和”主要是对内容与形式、情感与形式在音乐中的结合比例的回答。孟子则更进一步从“心性”即音乐的内在根据出发来讨论“和”,“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认为主体对音乐的审美感受是相同的,提出共赏性的“‘独乐乐不如‘与少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荀子将“乐”作为人由恶之本性向善之化性转变的途径,“和”也具有了道德、伦理的意味。“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这个标准正是对“礼”的律规的强调。《乐记》进一步指出,“中和”应以“一”为本,要求“审一定和”,“乐由中出,礼自外作”,达到儒家所希望的稳定有序的理想社会与和谐的审美理想。
原始儒家“礼乐”观的音乐美学思想强调音乐对人的情感的陶冶、培育以及音乐外在社会功用的探讨,引领了音乐与社会政治及伦理的统一,使之实现了在社会政治、伦理维度的价值飞升;同时却遗忘了音乐本身的意义,音乐自性在先秦儒家乐论思想中处于失语状态,其言说被美善统一、礼乐统一的伦理和政治言说所遮蔽,导致了工具化的倾向,形成音乐审美意识形态价值、音乐文化角色地位的加强和其自身内在意蕴失落之间的悖论。
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强烈诉求是两汉时期的一大社会现实,这种诉求意识继而转变为对复兴“礼乐”的强烈渴盼,于是将明晰的社会政治及伦理制度与明晰的艺术相对应,并相信“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论也随之固化为伦理性而非审美意义上对音乐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的思考,伦理维度上对音乐的阐释空前膨胀,稀释着音乐本身的原初之美,也反向宣告了音乐向其自身理性回归的必要性。
这一过程与儒家独尊地位的制度化、形式化互为表里。汉武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董仲舒所倡立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宇宙一道德本体论模式,适应了调整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的需要,以至于取代汉初的黄老之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导致了两汉思想和学术的调整,其直接结果,便是经学和谶纬之学的兴起。谶纬之学是儒学在学理场权威化形式诉求的名例。两汉末世兴谶纬之学,“宣布图谶于天下”,在人事与“天(自然)象”之间以强力寻求同构和对应,包含着极其浓厚的天人感应色彩。而董氏的“以德配天”完成了儒家礼制伦理对“天”的异名替代。在这一过程中,谶纬之学起到了“正当性预置”的作用,即以“神”和“天”的天然正当性,弱化来自理性意识的警觉,所以,“人事”与“天象”的对应,实质上仍是人事对董儒礼制伦理的顺应。
在这种正当性权威力量的辐射之下,两汉乐论成为王权绝对化和儒学定于一尊在艺术上的反映:
……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
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文之喜怒。乐以象天,礼以法地。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故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佚,节其奢靡也。
以音乐理性的丧失为代价,原始儒家开启的音乐朝向社会主流地位的挺进,在两汉时期得以确定。在两汉这样一个文明继续确立、理性继续外扬的时期,“礼乐”惟有获得儒家价值标准的认可,才可能合法地存在并繁荣,于是,几乎没有任何自觉意义上的颠覆与反叛,“礼乐”就以顺从的姿态,进入儒家文化的权力世界,建立起自己在道德、文化以及审美意识形态上的主流地位。然而,值得怀疑的是音乐在审美意识形态之下的这一工具化、附庸化过程使之获得了主流社会身份,同时也遗失了音乐自身的理性与意义,一组矛盾由此形成。
三、音乐理性的萌蘖
由先秦道家音乐美学开启并在魏晋六朝完成的音乐向其主体精神的回归之路,是音乐在“礼乐”由先秦儒家肇始并于两汉得以固化的同时,所遵循的另一条演进线索。先秦道家音乐美学把“道”即宇宙的生命节奏和自然规律的本体化作为音乐的本体,侧重于对音乐形上意义及其与“自然之性”的人生境界的对应;同时把音乐本体的“道”与人生自由境界的追求联系起来,主张超越各种有限的事务、情感束缚和功利桎梏的艺术与人的精神的自由解放,从而成为音乐回归“自性”的起点。
老子有关“道”的论述和“大音希声”观点的提出,奠定了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基调。他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其特点是“无”,但“无”不是纯粹的一无所有,而是无规定性、无限定性,也即无意志、无情感。老子的“道”不仅是宇宙的本体,也是其理想音乐——“大音”的本体。所谓“大音”,即“道”的声音。既然“道”无具体规定性、无限定性,超越了人的具体情感意志,那么,“大音”便不同于“一致之声,偏固之音”。同时,“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_,“道”先天地而生,是“万物
之所然,万理之所稽”,处于“无”时的“道”才是“道”的本身,而“道”进入“有”的状态,则成为“道之华”。具体表现在音乐美学中,“大音”即至美不变的“道”与纷繁的音乐现象的统一,“大音希声”。
庄子的音乐思想,可归结为由“至乐无乐”出发的“天乐”、“天籁”观。“天籁”,“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而“一阴一阳之谓道”,因而“天籁”正是无限的、自由的“道”。“天乐”是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也与“天籁”同意,成为其最高的音乐境界,即顺应“道”与天和的音乐。庄子严格区分了作为“道”的音乐与“形色名声”之乐,即“天籁”与“人籁”。他认为真正的音乐是以自然之性为旨归的“天籁”:
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无言而心说,此之谓天乐。故有焱氏为之颂日:“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包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
而“钟鼓之音”与“形色名声”的音乐,即“人籁”乃“不足以得彼之情”,是“乐之末”。
庄子还强调适性之乐,表现出对在后天规范和机巧中“丧已于物”的不屑。进而,庄子将“天籁”作为提升心灵、净化自我、坐忘-心斋-物游的一种境界,在聆听“天籁”中“游心于物之初”,妙悟其道,实现生命旋律与天地自然旋律的和谐一致,到达人生的澄明之境,成为“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泛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的“圣人”。
作为庄子思想核心的“自然”,无疑是顺应“道”之常性的“自然”。庄子提出“道”是“自然”、“无为”的,是“自本自根”的。然而,他所确立的是依于宇宙本体又超越它的更广阔的人生本体论,因而“自然”在庄子处,就具有了形而上的人生境界和处世方式的涵义。“圣人”之境界是“自然”,是“不违常性”、“心与物游”,是合乎天德的、天人合一的本体境界。庄子建立起反抗文明、归属自然的人性本体论,从而为音乐确立了指向自然人性的哲学依据。音乐自身理性的获得,即其主体性地位在传统审美经验中的确立,由伦理性艺术转化为审美性艺术,则在魏晋时期。蕴涵于魏晋名理学之中的“自然”,是这一时期主体价值学说及天人关系的逻辑起点。“自然”之理,即指“天地气化,盈虚损益”的常理。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名理学把“自然”视为比“名教”更为本质,包含着对宇宙本体、天地法则、天人关系的认识;同时,又以“名教出于自然”来协调儒、道,从中体现了独特的审美价值标准。正始时期的玄学家也认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元康时期魏晋人的天道自然观念,主要体现于郭象的“独化”说,其核心内容是认为宇宙万物都“独化而足”,事物本身就是其产生与存在的根据。所以,魏晋士人所指的“自然”,已转化为是主体意识觉醒之下的本性之“自然”。天道自然的本体意识与顺应自然的性命原则,成为魏晋自然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
与个体价值的觉醒相一致,魏晋形成了文学艺术与审美的主体精神。这一时期主体性的确立突出表现于以下方面:首先,以主体之学取代两汉谶纬学说,将谶纬对“天”和“神”,以及董儒礼制规范、伦理纲常的“正当性预置”,转化为对关注生命个体的热情。魏晋风度经由汉末人物品评,最终形成了六朝时期的人物品藻,认为人只是世俗中的现实之人,而非对天作出感应的人,于是重视人的任情所为、风度、才性,远胜于两汉确定的伦理、节操。人学主题的另一项内容,则是感伤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感伤主义始于汉《古诗十九首》,是对人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的一种体认,也是人反观自身的一种把握。与春秋战国相似,从汉末到魏晋是一个“失范”的时代。战乱、瘟疫、地震的频繁发生,无疑都潜在地加深了人们的颠沛流离及生命无常之感,并内化、扩展着主体内心世界的体味。《古诗十九首》一建安悲怆一正始之音一隐士悲歌,感伤主义情调沉淀在六朝审美心理结构中,这一切扩充着音乐的情感范围,也完善发展了先秦乐论中关于音乐本源的思考。魏晋乐论对音乐独立意义的强调以及音乐理性的获得,分为两个阶段:
(一)音乐理性表现之一:悲情意识
与悲情意识对魏晋时期主体自觉的意义相似,魏晋音乐美学思想对悲情意识的敞开,也从一个角度标志着音乐对自身理性的诉求,体现了魏晋乐论在音乐的本源问题上与儒家的差别。
先秦儒家主张音乐要以声表情,“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然而,基于其“和同”思想,儒家乐论并非对所有的情感因素都认可,而是强调喜、怒、哀、乐诸种情感的相互协调,达到“和”的境地。正是出于这种理解,儒家提出其二元音乐价值论,即将音乐现象划分为“雅乐”与“俗乐”,其崇尚的“雅乐”除了内容方面的政治、伦理考虑之外,便是在音乐各元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上要符合“平和”、“和同”的标准,“郑卫之音”之所以被其斥为“淫声”,也正是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汉代乐论同样在主张音乐源于现实对情感的表达的同时,反对悲情在音乐中的流露,提出要节制情感,尤其是悲哀之情。所谓“大乐无怨,大礼不责”是也,先秦至两汉儒家乐论在音乐本源问题的有限情感论特征可见一斑。
然而,在魏晋这个鲜活的时代,随主体意识的觉醒,悲情一维却突兀而率真地闯入了音乐领地。魏晋士人狂放的长啸、清歌等包容丰富的情感含量的“声”和“乐”,就是这一主体精神的直观表现。以悲情反乐教,可以说是魏晋时期个体性觉醒的显著标志。以前的魏晋乐论研究多是从形式方面说明此间音乐自性的获得,而较少从悲情一维人手。笔者认为,尽管魏晋所完成的对音乐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释放”以突出形式为主,强调“乐之为乐”、“文之为文”的意义,但音乐之独立,必然包含有内容上以及对被表现对象的彻底敞开。很难说某种只以一种风格为荣而拒斥其他的音乐是成熟的音乐;同样,也很难说一种对音乐的表现对象持畸形理解的乐论是成熟的乐论。正是包括内容及形式两方面,魏晋之“乐”才真正获得了艺术独立性质。
(二)音乐理性表现之二:“声无哀乐”
嵇康更进一步对儒家乐论提出质疑和反驳。这种质疑与反驳,集中体现在他对儒家“声有哀乐”观的质疑以及对音乐“和”的形式的强调上。嵇康区分了“心”与“物”即主观与客观,认为音乐的本体不是情感,而在于体现自然之和的声音:“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它与哀乐情感是不相关联的两个领域:“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两者有名实之分,即“心”与“物”之别。“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为主,则无系于声音”,“声音”只有“善恶”即审美意义上的美丑之别,不包含情感上的哀乐判断。虽然音乐中可以存在主观情感向外在音乐的移情现象,而且这构成了音乐本身便具有情感的心理原因,但音乐并没有情感,即“声无哀乐”,而非传统儒家将主观情感等同于物的客观性质的“声有哀乐”论。
这样,嵇康便与传统儒家对音乐的本源问题有了不同的回答。
“声无哀乐”这一否定背后又是有所肯定的,这个肯定,即是让音乐成为它自身,音乐除了是乐音的运动形式,便什么也不能说明。嵇康在音乐体用之间的划界终止了先秦以来乐论将音乐功能等于音乐本身的“以用为体”的传统。
嵇康还进一步把“和”或“平和”作为音乐的本体。“声音有自然之和”,“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强调音乐自身形式结构、节奏旋律的和谐,即他自己所说的“宫商集化、声音克谐”。同时,“和”更指一种超越各种情感、局部现实及有限感官的形而上之“和”,指那种超越“偏固之音”、“一致之声”而无限敞开的自由平和的境界。
嵇康所谓“和”的境界,与玄学家追求的“无”相一致,以玄学家之“无”,嵇康进一步扩充了传统的音乐本体“和”的内涵。玄学与道家思想密切相关,“道者,无之称也”,从两汉至魏晋,玄学完成了对经学的反拨,也实现了道家哲学的复兴和发展。嵇康正是以糅合“道”、“无”,沟通道、玄的“和”的观念,实现了对音乐形式一维的强调,从而在魏晋时代发出了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以及音乐自身发展均弥足珍贵的“声无哀乐”的呼声。
魏晋音乐悲情意识的复苏以及嵇康对音乐自身价值的探讨,表明了魏晋时期音乐理性的形成,两者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奠定了音乐理性的皈依之途。前者从主体意识自觉的角度,对儒家“礼乐”观以“礼”节情、以“礼”节“乐”提出质疑,援悲情人乐,正是音乐脱离礼制仁义、回归个体丰富情感表达的标志。而“声无哀乐”则非反对援悲情人乐,而是主张主体的悲喜之情与音乐本身的疏离,即音乐只是音乐自身,而不能天然地附带主观情感,但作为悲喜情感的触媒,音乐依然向悲情意识敞开着。
四、结语
传统乐论经历了从上古神灵崇拜意识下的神性音乐到先秦、两汉儒家“礼乐”观,以及落实到魏晋六朝“声无哀乐”论启发的音乐理性的萌蘖;开始了从审美意识形态之乐向赋有音乐理性的音乐本身回归。中国音乐美学观念在神性与理性之间徘徊。同时,传统乐论中表现出的音乐社会身份的流变,也遗留了一组矛盾关系:审美意识形态下音乐主流地位以其音乐理性的丧失为代价,而音乐理性的获得之时也意味着其淡出社会主流逐渐边缘化过程的开始。而作为音乐从神性向自身理性皈依的核心,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自然”的意义也从外在自然转化成为了主体内在性情的自然。与此同时,音乐的社会位置反而从主流、中心而逐渐边缘化、民间化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首先,中国文化作为乐感文化的乐感,在其后延续着的发展中,以音乐之外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实现着音乐与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间的通感。这种渗透和融入使音乐隐居于书法和绘画中,无疑弱化了音乐的艺术主流地位,使其成为了边缘状态的“隐士”。
其次,音乐丧失了“礼乐”包括社会政治以及个体心理两个方面的现实性依托,“礼乐”作为主流艺术的神圣光芒黯淡下来。
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改造受容而成的禅宗,都吸收了音乐的形式。“援乐入教”以及中国宗教多择名山而居的特征,使音乐由朝堂转入了寺庙山林。而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的主静、内心化特征,决定了音乐在宗教内部丧失主体性而被边缘化的命运,即音乐被吸收进入宗教之后也相应被剥夺了其自身主体性,宗教音乐仅仅作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而存在,而未获得超越宗教整体意义之外的自身意义。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