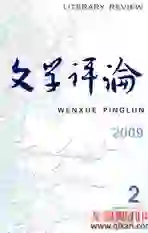论汉文化的“诗言志,歌永言”传统
2009-05-13王小盾
王小盾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诗言志,歌永言”是关于古代仪式语言的命题,原指从读诵到歌唱的发生学关系。其背景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分工传统,即巫师掌祝诵、瞽蒙掌歌舞的分工。它后来发展为知识分子(代表读诵)与乐工艺人(代表歌舞)的分工。诗、赋等作家文学文体正是通过分工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亦即通过讽诵和“不歌而诵”的路线建立起来的。中古时期,随着外族文化的传入,大批同屈折语相联系的音乐流传于中土,形成歌不永言的风尚,也造成了声诗传统和曲子传统的对立。作为声诗传统的代表,宋代出现了强大的反对“歌不永言”的思潮,也出现了苏轼等人“以诗为词”的创作风尚。这一思潮的实质,是强调文人在音乐文学创作中的决定地位,强调以夏变夷、以文化乐等汉文化的雅正传统。但它同时也说明:必须考虑到汉语的特性,从诵与歌之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古老的“诗言志,歌永言”理论。
一“诗言志,歌永言”的本来涵义
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诗言志,歌永言”也许是最重要的命题一至少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命题。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一文中,曾经称它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现代学者则从文学功能的角度,或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的角度,对这一命题作过反复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诗言志,歌永言”云云讲的是诗歌教学,亦即讲诗乐在思想道德性情方面的陶冶作用。其中“诗言志”一语则指诗歌所表现的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但它“只是阐明诗歌政治教化方面的意义,还不能说是对诗歌艺术的审美性把握”。这就是说,在人们的理解中,“诗言志,歌永言”是一个伦理美学的概念威是一种关于文学功能的主张。
以上这些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战国以来,人们的确从功能的角度、文体的角度阐释过“诗”与“志”的关系;汉以来的学者且就此作了进一步解释和发挥。例如《礼记·孔子燕居》载孔子语云:“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毛诗《关雎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按照这些说法,“诗”尽管是和特定的声音(“永歌”)、特定的动作(舞蹈)相联系的,但它指的是表达心志的一种历史文献,和《书》、《礼》、《易》等并立。
不过,有一个问题却是应当细究的:以上种种解释,说的都是《诗》成形之后的事情;它们是否符合《尚书·尧典》的原意呢?看来并不符合。因为在原来的记载中,人们谈论的并不是文学问题,而是诗、歌、声、律之间的递进关系: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显而易见,这是存在于仪式之中的事物关系。仪式之乐是用于通神的,所以这里说“八音克谐”,“神人以和”。根据民族学资料,较原始的祭祀仪式往往葆有图腾崇拜成份,亦即习惯作装扮成动物的舞蹈,所以这里说“百兽率舞”。总之,参考《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下两段话:
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
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可以判断,“教胄子…直而温”云云,并不是讲思想道德性情方面的陶冶,而是讲“乐德”方面的学习,即学会对仪式语言、仪式音乐作风格把握。而“诗言志,歌永言”云云,讲的是仪式表达,也就是以“致鬼神”、“和邦国”、“悦远人”、“作动物”为目的的表达。这里既不存在作为历史文献的诗歌,也无须表现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
其实,理解“诗言志,歌永言”这句话,最关键的环节是确认“诗”在其产生之初的本来内涵。马银琴曾经论证:在周初及更早的时候,“诗”指的是用于谏刺的讽诵之辞,“歌”指的是用于颂赞仪式的歌唱之辞。《诗经》作品中的“正”“变”二分,可以理解为颂赞之辞和怨刺之辞的二分,其本质则是仪式乐歌和讽谏之辞的二分。换句话说,被郑玄称为“诗之正经”的那部分作品,它们本来就是用于仪式上的记诵、祝祷和颂赞的;相反,从“诗”字最早的用例看,也从它的字形结构(从言从寺,即从言从持)看,“诗”代表的是规正人行、使之有法度的言辞。由此可见,“诗”和“歌”的区别,在西周初年,乃相当于国子之辞和乐工之辞的区别。从《周礼》“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这句话看来,“诗”是“乐语”,是一种朗诵的言辞。
事实上,“诗”之古义,也就是诵辞。《汉志·六艺略》在《诗》小序中说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在这里,“诗言志”的“诗”,被明确解释为“诵其言”。
“诵其言谓之诗”这句话,似乎被过去的研究者有意忽略了;但理解它却并不是难事。因为,如果我们把诗看作一种语言艺术,那么,朗诵便是最重要的艺术语言。按古人的理解,所谓艺术语言也就是非日常的语言,而在所有非日常的语言(各种形式的歌唱和朗诵)当中,朗诵最接近日常语言,是最容易被人理解的语言。由于这个原因,朗诵在通神仪式中得到广泛应用。从民族学资料看,这种语言包括记诵,即讲述史诗,壮族称“末论”;包括念诵,即吟读经文,羌族称“木吉卓”;包括祝诵,即经咒,在布依族中有“解帮经”、“祭祀经”等项目,也包括告诵,即主持仪式时的宣示和面向神灵的通告。根据《周礼》,国子们所学习的仪式“乐语”,有兴(起兴)、道(道古)、讽(背文)、诵(吟诵)、言(宣告)、语(答述)等品种。而从满族的《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看,仪式朗诵用于还愿、背灯祭、跳神、祭祖宗、换锁、跳舞、送净纸等项目,是巫师最重要的技能。
另外,种种资料表明,“诗言志”的“言”字,也是仪式朗诵的产物,代表一种“乐语”。根据语言学资料,这种乐语既有直言宣告的特点,又有激荡发声的特点。在甲骨文中,“言”字与“告”字形近,用为祭名,即告祭。徐中舒等人解释说:“甲骨文告、舌、言均象仰置之铃,下象铃身,上象铃舌,本以突出铃舌会意为舌。古代酋人讲话之先,必摇动木铎以聚众,然后将铎倒置始发言,故告、舌、言实同出一源,卜辞中每多通用。”这就是说,“诗”和“言”都指仪式上的艺术语言,其间差别只是泛称(泛指诵辞)、专称(特指直言宣告之乐语)的差别。
综合以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尚书·尧典》所说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段话,应当作如下理解:
什么是“诗”?诗是心志发为朗诵;
什么是“歌”?歌是把朗诵的声调加以延长,
什么是“声”?声即曲调,是对歌声的模仿-
什么是“律”?律即乐律,是对曲调加以调和。这段话讲的是仪式上的语言和音乐,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文学和音乐。“诗”、“歌”、“声”、“律”这四种事物,是处在同一个逻辑平面的事物,而不是文体、表演这两个平面的交叉。“诗”、“歌”、“声”、“律”所处的逻辑平面,也就是仪式表演。正是从仪式表演的角度,才可以看到朗诵、歌唱、乐曲、乐律这四种事物的依次递进。因此,“诗言志,歌永言”应是一个关于艺术史的命题,而未必是美学或文艺学的命题。其核心意义是:通过读诵、咏歌、奏曲、定律这四者的关系,来说明音乐文学事物在发生学上的关系。
二诵和作家文体的形成
以上论证表明,“诗言志,歌永言”是通过仪式朗诵而建立的概念。这意味着,“诗”之所以成为一种文体的名称,是同朗诵相关联的。
“诗”和朗诵的相关,缘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巫祝的传统。《周礼·春官》说以乐语教国子、以“六诗”教瞽蒙,事实上便讲到了这一传统及其赖以建立的某种古老的分工。此即在各种远古仪式上,巫师掌祝诵、瞽蒙掌歌舞的分工。这一分工,也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与乐工艺人的分工。《诗经》作品中的“正”“变”二分,隐藏了仪式乐歌与讽谏之辞的二分。这意味着,“诗”与“歌”的分别,乃反映了国子之辞与乐工之辞的分别。如果说仪式乐歌是属于瞽蒙的表述方式,那么,仪式朗诵便是属于巫师、国子及其它知识分子的表述方式。《诗·大雅·蒸民》说:“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大雅·崧高》说:“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小雅·节南山》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讠凶)。”这些诗句,反映了早期诗人同朗诵的内在关联。
在先秦时代,“诗”之所以具有“诵”的涵义,原因是士大夫们主要用诵的方式来传述诗。我在《诗六义原始》一文中曾经论证:“六诗”中的“风”和“赋”,分别指的就是本色的讴歌和使用雅言的朗诵。“风”主要是民间的行为,“赋”则主要是士人或乐师的行为。如果说“风”的对象是民间歌谣,那么,“赋”在很大程度上便意味着采取风歌的素材,而改用雅言来传诵。这也就是《汉书·艺文志》引刘向所说的“不歌而诵谓之赋”。“不歌而诵”,在春秋期间成为广泛流行的外交方式,形成了“赋诗言志”的风尚,而其结晶,则是“赋”这一文体。《汉书·艺文志》说:“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就是说:赋产生于“学诗之士”把他们所专长的吟诵(“诗”)变成了新文体,亦即赋。因此可以说,“诗”的传统也就是朗诵的传统;中国作家文学的产生,其标志便是作为新诗的辞赋的产生。
从汉代记录看,文人的讽诵之法有很大的势力。《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少年之时“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汉书·王褒传》则说:王褒侍太子之时,须“朝夕诵读”种种文辞,而太子则“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诵似乎是当时最重要的学习方式,所以《汉书·东方朔传》说东方朔“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诵也是传述民歌的一种技能,所以《汉书·礼乐志》说武帝立乐府,所采赵、代,秦、楚之讴皆用于“夜诵”,又说哀帝时乐府给祠南郊的人员中有“夜诵员五人”。特别是,汉代人喜欢在对比的意义上谈论诵和歌,例如《东观汉纪》说:“熹平四年正月中,出云台十二门新诗,下大予乐官习诵,被声,与旧诗并行者,皆当撰绿,以成《乐志》。”在这里,“习诵”既和“被声”对立,又和“旧诗”并行,诵显然被看作文人传述诗的主要方式。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各种文学作品为五类,其中四类是代表诵的“赋”,末一类才是代表新歌的“歌诗”。为什么说“歌诗”是新歌的代表呢?只要对《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8家歌诗加以考订,就可以知道其中道理:“歌诗”是同赋相区别的,它是用于歌唱的文学,是服务于宫廷礼仪的乐府歌辞;“歌诗”又是同“六艺略”中的“诗”、“乐”相区别的,它是采用当时的流行曲调(而非周代古曲)的音乐与文学。概括起来说,它是在古代雅乐传统影响下形成的汉代特色文学,既包括为建立祭祀、燕飨礼仪而创作的新歌诗,也包括按古代采诗习惯辑编的传统歌诗。
《汉书·艺文志》所载28家,其中前8家是“颇造新哥”的作品,后20家是“颇杂讴谣”的作品。从前一部分看,汉代歌诗是由帝王、朝臣、贵族制作的。它之被称作“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说明,在当时人看来,“诗”是属于上等人的文体。这一看法,是对先秦人的诗观念一“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观念——的继承。但人们在这时却加了一个修饰词,称之为“歌诗”。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诗”的音乐性质变了:上古是诵辞,汉代是歌辞。这样一来,《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的诗、赋两分,同《尧典》时代的诗、歌两分相比,就成了性质不同的两组关联词。我们知道,这是由时代变迁造成的,其间关系可以用以下一图来表示:

通过这份图表,可以理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大问题:
(一)在中国韵文文体形成史上,有一个基本对立,即朗诵和歌唱的对立。它是依靠巫师与瞽蒙的分工,或者说知识分子与乐工艺人的分工,而建立起来的。
(二)这一对立在不同时代均有其表现。在周代,它表现为“诗”与“歌”的对立,在汉代,它表现为“赋”与“歌诗”的对立。作为对这种二分传统的继承,在魏晋南北朝时,有“诗歌”(徒诗)与“乐府”的对立;在唐代,有“声诗”(诗而声之)与“曲子”(因声度词)的对立。
(三)作为一种文体的“诗”,便是在这一对立过程中形成的。它最初表现为巫师的仪式诵辞,亦即表现为对日常语言的美化——所以说“诗言志”。后来,它表现为土大夫们所熟悉的一种语言艺术,所以在周代用于讽谏,并由此产生了某种制度或制度理想,这就是《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谓“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杜预注:为诗以风刺),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以及《国语·周语上》所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韦昭注:献诗以风也),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当乐工把讽谏之诗采入仪式,配为音乐的时候,也就有了被称作“变风”、“变雅”的仪式乐歌,这也就是下图第三阶段的“歌”;

换句话说,当“诗”和“歌”完成了它们的分立与合流的过程之时,“诗”这一文体也就产生出来了。
(四)从以上角度看,“赋”是“诗”的流变。班固《两都赋》说:“赋者古诗之流。”李善注:“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这两句话的涵义是:作为文体的“赋”,来源于作为“诗”的一种传述方式(朗诵)的“赋”。可见“诗”和“赋”都是因为同“歌”相对而呈现其特质的。它们的区别在于:“诗”在内容上不同于“歌”,是巫师或士人之辞;“赋”在形式上不同于“歌”,是把“歌”的内容改用朗诵的方式来表述。因此,赋意味着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当这种专属于士人的创作方式独立
出来之时,赋也就成了专属于文人的一种文体。
(五)到汉武帝建立乐府,那些用于仪式的新乐歌,便用两种方法制作出来了。如前文所说,一种叫作“颇造新哥”,另一种叫作“颇杂讴谣”。虽然制作路线不同,但它们都模仿了作为周代仪式乐歌的“诗”的形式,所以叫做“歌诗”。也就是说,“歌诗”一名标志了“诗”这一文体概念的形成。
总之,在汉代产生了两种作家文学的文体,一是赋,二是诗。刘向、班固等人所建立的“诗赋略”,可以看作对这种文体运动的总结。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两种文体是经由不同的路线形成的。赋来自对民歌的整理,也就是把方言文学变成了雅言的文学,或者说典范的文学;诗来自对仪式语言的运用,也就是把巫师文学变成了士人文学,或者说把面向神的文学变成了面向人的文学。因此,《汉书·艺文志》所显示的“诗”与“赋”的对立,是一种源于上古的对立,具有文化传统的意义。
三中古音乐创作的两条路线
“诗言志,歌永言”的路线,亦即从语言文学转变成音乐文学的路线,其结晶是被称作“诗之正经”的那些作品一“不歌而诵”的路线,亦即从音乐文学转变成语言文学的路线,其结晶是包括“变风变雅”、“失志之赋”在内的那些怨刺作品。这两条路线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语言文学为依归的。从第一条路线转移到第二条路线,原因是出现了“周道寝坏”这一历史事件。
到汉魏之际,又出现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就是以“铜雀台”为名的新的乐府机构的建立;与此相应,以“清商”为名新的俗乐进入了宫廷。上述两条路线的对立于是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即表现为“因声造歌”、“因诗成调”二者的对立。按当时的乐府音乐主要有三宗,一是来自“汉世街陌谣讴”的“乐章古词”,二是“晋宋以来,稍有增广”的“吴哥杂曲”,三是“魏世三调哥词”。《宋书·乐志》对这三批音乐作过以下评论:
凡此诸曲,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调哥词之类是也。
这里便说到了两条路线的对立:其一是“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的路线,用于改造“汉世街陌谣讴”和“吴哥杂曲”;其二是“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的路线,用于发展“魏世三调哥词”。前者继承了“诗言志,歌永言”的传统,后者则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
为什么说“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属于新的文化呢?这是因为,正是从“魏世”——准确地说,从曹氏建铜雀台之时(建安十五年)——开始,一系列莉所未有的新事物产生了:在传统的以弹唱相和为特征的“弦歌”之外,产生了“歌弦”,即歌与乐完全配合的乐歌;在传统的歌舞之外,产生了“大曲”,即由艳、曲、趋、乱结合而成之曲,亦即器乐、歌乐、舞乐混合编组之曲。这样一来,“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就不仅有了基本条件,而且有了迫切需要——于是成为风尚。从音乐史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一场大变动的先声。一百年以后,出现了一场席卷整个北部中国的大动乱。来自西方和北方的若干民族,先后在中原建立起了近二十个政权。丝绸之路空前活跃,西域地区的歌舞通过佛教流传、商业贸易以及战争、进贡、王族婚嫁等不同途径进入中土。中国于是出现了大批新的来自非汉语地区的艺术歌曲,出现了对新型汉语歌辞的呼唤。这样一来,在唐代便出现了李清照所说的“乐府、声诗并著”的局面。这里的“声诗”,指的是“诗而声之”,亦即按采诗人唱方式配乐的歌辞;这里的“乐府”,指的是乐工之辞,亦即按因声度词之法创作的“曲子辞”。它们实际上在新的形势之下展示了两种文化传统的对立:前者代表了“诗言志,歌永言”的传统,即先诗后乐的传统;后者则代表了另一个传统,即先声后辞的传统。
关于这样两个传统的对立,唐代人作过许多表述,例如孔颖达《诗大序疏》:
原夫作乐之始,乐写入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乐器有官徵商羽之异,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人。是乐本效人,非人效乐。但乐曲既定,规矩先成,后人作诗,谟摩旧法,此声成文谓之音。
元稹《乐府古题序》:
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旬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田亡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调以配乐也。由诗而下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对于“声诗”、“乐府”这两种传统,孔颖达表述为“乐效人”、“人效乐”的分别,元稹则表述为“选词以配乐”、“因声以度词”的分别。孔颖达是初唐人,是从经学角度讨论辞、乐关系的,他的立场是“诗言志,歌永言”的立场;但他已经指出了一个新传统的存在。元稹与此不同,明显是从“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的“乐府”角度来讨论问题。这表明:在中唐之时,“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的“歌、曲、词、调”,已经成为音乐文学的主体,成为新的风尚了。
为了理解元稹的理论,我们有必要谈谈“曲子”。曲子也就是隋唐五代的流行歌曲。是经过乐工伎人加工,有调名、有固定曲度的音乐作品,它也不同于前代的相和歌、清商曲,而吸收了来自胡乐的曲体因素和节奏乐器的因素,具有结构规整、节奏鲜明的特点。它的数量很大,《教坊记》著录盛唐教坊小曲278曲,《唐会要》著录天宝大乐署所订曲名253曲,南卓《羯鼓录》著录盛唐羯鼓之曲131曲,《乐府杂录》著录中唐曲名13曲。据初步统计,隋唐五代所传新乐曲,可考者达一千之数,其中有传辞者近二百五十曲。花蕊夫人《宫词》所谓“太常奏备三千曲”,并非虚言。
曲子赖以生存的音乐文化土壤,人称“隋唐燕乐”。隋唐燕乐区别于此前清乐的特点,是汇聚了多种音乐成分,包含了丰富的旋律——特别是来自西域的热烈奔放的新旋律。这批旋律进入中土之后,向使用汉语的人群呼唤新词,造成因声度词的风尚。其成果,从音乐角度看,是造就了强烈的“曲子”观念和“拍”的观念;从文学角度看,是造成了见于《云谣集》、《尊前集》、《花间集》、《乐府诗集·近代曲辞》等曲子辞集的一批迥异于传统五言体、七言体的长短句诗,是造就了被后世称作“词”的新文体;而从文化角度看,那么它便意味着,一个新的传统——诗不言志、歌不永言——在这时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了。
四“诗言志,歌永言”思潮在宋代的复兴
把“诗言志,歌永言”称作文化传统,认为它同“因声以度词”之法的冲突是文化传统的冲突,其中的道理,在宋代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在宋代出现了一连串响亮的声音,其主旨是反对以诗就乐的“曲子”传统,而主张歌以永诗、声以依歌的“永言”传统:
(一)公元1067年,北宋神宗即位,王安石以翰林学士兼侍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身分,在政治上、文学上发挥重要影响。其“诗言志歌永言”理论云:“古之歌者,
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
(二)神宗元丰二年(1079),太常礼院主簿杨杰上言大乐七事,首先一事即所谓“歌不永言”:“盖歌以永诗之言,五声以依歌之咏,阳律阴吕以和其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然后神人以和也。若夫歌不永言,声不依咏,律不和声,八音不谐,而更相夺,则神人安得和哉?……伏请节裁烦声,以一声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且诗言人志,咏以为歌,五声随歌,故日依咏;律吕协奏,故日和声。先儒云: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非人效乐——此之谓也”。
(三)南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飨明堂,国子丞王普倡言雅乐歌辞复古,云:“盖古者既作诗,从而歌之,然后以声律协和而成曲。自历代至于本朝,雅乐皆先制乐章而后成谱。崇宁以后,乃先制谱,后命词,于是词律不相谐协,且与俗乐无异。乞复用古制。”据记载,这番言论得到普遍响应——“寻皆如普议”。
(四)绍兴十九年(1149),王灼在成都碧鸡坊妙胜院编成《碧鸡漫志》。此书卷一论歌辞之始,云:“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
(五)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间(1154-1157),吴曾编成《能改斋漫录》。其中评论“开元天宝间君臣相与为淫乐”之事云:“明皇尤溺于夷音,天下熏然成俗。于时才士,始依乐工拍担之声,被之以辞。句之长短,各随曲度,而愈失古之‘声依永之理也。”
(六)公元1162年,孝宗即位,朱熹的讲学事业也进入盛期。《朱子语类》卷七八记其关于“诗言志,歌永言”的解释说:“古人作诗,只是说他心下所存事。说出来,人便将他诗来歌。其声之清浊长短,各依他诗之语言,却将律来调和其声。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调了,然后做语言去合腔子,岂不是倒了!却是永依声也。古人是以乐去就他诗,后世是以诗去就他乐,如何解兴起得人。”《晦庵集》卷三七又载其答陈体仁书信云:“诗之作本为言志而已。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
以上这些说法,如同齐声呼应,形成一个来势凶猛的思潮。这一思潮并且有逐步增强的趋势——如果说北宋时期它主要属于雅乐理论,那么,到绍兴十九年以后,它便进入词曲学而成为俗乐理论。从文化角度看,它们反映了11世纪、12世纪之交华夏正统观念的兴盛,而从音乐角度看,它们有明显的动机,即反对渊源于“胡夷里巷之曲”的“今曲子”——王安石称作“今先撰腔子后填词”,王灼称作“以词就音”的“今乐府”,吴曾则称作“夷音”和“拍担之声”,认为它盛于唐明皇之时。综合这两方面,可以说,宋代的“诗言志,歌永言”理论,既有现实的目标,也有深刻的内涵。其目标即是对隋唐燕乐曲子之风尚,以及沿袭此风的“雅歌都废……尽新声”(柳永《玉山枕》词中语)的局面,提出反拨。其内涵则在于:作为“夷音”、“里巷之曲”的对立物,它是华夏传统和文士传统的象征。由此可以探知“诗言志,歌永言”思潮得以产生的缘由:表面上看,它是强调人声在音乐中的地位,反对“烦声”和“乐工拍担之声”;而究其实质,是强调文人雅士在音乐文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诗与声的孰先孰后,在宋代人的看法中乃代表“才士”与“乐工”的孰先孰后和华夏传统与戎夷传统的孰先孰后。
宋代这种“诗言志,歌永言”的理论,是明显有别于唐代的主流认识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音乐文化的形势变了。唐代是“乐府、声诗并著”的时代,而到宋代,“乐府”、声诗两者则产生了分离。其中一个表现是声诗自高身分,不用“今曲子”之歌调。据统计,宋代声诗(诗体歌辞)约有三千首,所借之腔仅《阳关》、《竹枝》、《柳枝》、《小秦王》、《瑞鹧鸪》、《木兰花》、《鹧鸪天》等少量流行曲。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旧声”和“新声”的分离。苏轼所谓“新声坐使旧声阑”,《乐府余论》所谓“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竟赌新声”,李清照《词论》所谓“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说的都是这种情况。旧声即唐代曲子,多为短调小令;新声则是词家所作新歌,多为长调慢曲。柳永《乐章集》载词二百余,三分之二以上是慢调长词。各种词律词谱书所载唐宋词调,其间在篇制上也有明显对比。这一点,反映音乐风尚有了很大的改变,已进入“蓄意新词轻缓唱”的时代。
实际上,最根本的改变是:到宋代,旧声的乐调退出知识层的日常生活。词之曲谱基本上失传,变质成为依调填词之范式,知识阶层遂同词乐日渐隔膜。正因为这样,在南北宋之交,随着词乐旧声再次沦丧,“诗言志歌永言”思潮从雅乐领域进一步侵入了词曲创作。张炎《西子妆慢序》、《意难忘序》对这种情况的表述是:“因填此解,惜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有善歌而无善听……倾耳者指不多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好乐之词家采俗乐创制了新声。从姜夔的情况看,其创作方法主要有四:一是采大曲旧声,二是采乐工新曲,三是采他人歌谱,四是“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唐圭璋《宋词纪事》所载故事,大多是歌唱乐工“新声”、“新腔”的故事,少数是歌唱词家“新翻曲”的故事,而歌唱唐代旧乐者百无一见。这也就是说,“旧声”和“新声”的区别,可以理解为无曲度和有曲度的区别。与之相对应,在宋代词学史上遂出现了新的分野——词家(或日唱诗家)和曲家的分野。词家是无曲度可以遵循,仅依文字谱作词的人物;曲家则是善“度曲”,能制“新声”的人物。杨缵《作词五要》说:“自古作词,能依句者已少,依谱用字者百无一二。”这说的是宋代词家日见其多、曲家日见其少的情形。
宋代词史上的苏轼现象,正是说明上述情形的好例。关于苏轼,李清照有一个著名的批评,云:“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尽管关于这句话的内涵有很多争议,但如果采用词家和曲家的分野标准,那么它是容易理解的。它实际上是说:苏轼等人只能采用唱诗的方法唱词,而不擅于曲家的“唱曲”。苏轼也认为自己“讴歌”“唱曲”皆不如人。
从各种记录看,苏轼的确是擅长“以乐去就他诗”的词家,比如被认为对倚声作词下过很深功夫的“檗括”,即是以乐就诗。“檗括”也就是将一篇作品改成体制不同的另一首诗词。表面上看,“麋括”往往依调,颇像因声度词,但其实质却不是这样。苏轼《哨遍·为米折腰》词序云:“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乃取《归去来》词,稍加蘖括,使就声律,以遗(董)毅夫,使家僮歌之。”又《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词序云:“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
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巢括,使就声律,以遗之。”可见苏轼所作的只是“使就声律”——使之协合文辞格律,其辞则由善歌、善琵琶的家僮“歌之”。这种作法,仍然是唱诗家的作法,属于“诗而声之”。
苏轼的“巢括”作品,此外还采用了声诗的方式。例如他所作的《挽歌》,改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而成,即把五七言诗改为七言八句,改毕交郭生歌唱。据《东坡志林》,它是“每句杂以散声”而歌的。这明显是声诗式的歌唱,有腔调而无固定的曲调。
研究者往往认为:苏轼懂音乐,喜欢唱诗,李清照等人对他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但“懂音乐”是一回事,能撰曲是另一回事。苏轼所做的那些音乐工作——考证古乐、撰写琴歌、审订格律、歌咏笙箫磬笛、研究《阳关曲》之迭与不迭——所涉及的其实都是书斋“音乐”或声诗传统中的音乐,同流行的曲家创作有很大距离。另外,正如苏轼的“巢括”一样,依王维《渭城曲》之字声作《阳关曲》,其实属于填词;“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其实属于吟咏;而作《减字木兰花·维熊佳梦》、《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南歌子·师唱谁家曲》等交付歌唱,则属于以先诗后声之法唱诗。王水照说苏轼的创作意识是“主文不主声”,是重视“吟诵腔吻”;认为他并不“以应歌为填词目的”,相反,目的在于“改变词附属于音乐的地位”。刘石说这种“以词为余事、为小技小道的轻词意识”,是埋藏在苏轼思想深处的意识”。这些判断是正确的。
总之,宋代的“永言”理论,在本质上是排斥新俗乐的理论,是依据某种典雅文化观而建立的理论。它是在唐乐旧声衰退、宋代新俗乐初兴这一音乐文化背景上产生的。苏轼也是秉承这一文化观的人物。他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用独特的创作方法对古来的声诗传统作出了响应。
五“诗言志,歌永言”理论的文化本质
宋代理论家们排斥“今曲子”,排斥新俗乐,却并未全面否定音乐;他们用以取代曲子和俗乐的是吟诵音乐。当旧声乐调退出知识层的日常生活之时,在宋代出现了另一种风尚,即文人吟咏的风尚。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宋代声诗理论强调“声依永”。苏轼说“乐声升降之节,视人声之所能至,则为中声,是谓声依永”,意思是:作为音乐理想的“中声”,产生于以乐声依从吟咏。沈括说:“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由此可见,宋代的文人吟咏既支持了声诗理论,也为声诗增加了新的内容。
一般来说,吟咏是表述“文”的艺术,其抑扬舒促依从字声,歌唱是表述“声”的艺术,其旋律和节奏依从歌唱者的习惯。沈括批评“今人不复知有声”,说他们“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其实这种“不知有声”的情况是通俗歌唱的常态,准确的说法是“只知有声”。郑樵《通志》卷四九《乐略·正声序论》说过:“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正是这种只求声新的情况不被重视文辞的人们所容忍,才产生了对吟咏、对声诗的呼唤。
在唐代,以声诗代表吟咏的情况并不突出,因为那是一个“溺于夷音”的时代。曲子不仅是流行的音乐方式,而且是流行的音乐。文人诗作遂往往以采入曲子的方式而成为声诗。到宋代,这种情况改变了,“旧声”消失,诗人乐曲于是变成诗人吟咏。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曲子之调经过器乐加工,而吟咏之调只是人声。所以宋代的声诗多是人声之诗。它们既可以称作“吟唱”(无固定腔调),也可以称作“咏唱”(有固定腔调)。从以下记述可以知道,当时人正是把这种吟咏和“歌”一体看待,称其为“声诗”的:
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
黄裳《演山居士新词序》:“演山居士闲居无事,多逸思,自适于诗酒间,或为长短篇及五七言,或协以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舞蹈以致其乐。”
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凡引、操,吟、弄,虽主丝竹,其有辞者皆可以形之歌咏。”
陈旸《乐书》卷一百十九:“琴之为乐,所以咏而歌之也。”
《宋史·乐志·诗乐》:“宋朝湖学之兴,老师宿儒痛正音之寂寥,尝择取《二南》、《小雅》数十篇,寓之埙龠,使学者朝夕咏歌。自尔声诗之学,为儒者稍知所尚。”在宋代人看来,吟咏和歌唱之别,可以比拟于声诗与曲子之别。因此,倡导声诗,可以理解为倡导吟咏——亦即按“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传统,恢复以诗及其字声为本位的歌唱。
宋代的唱曲,正是一种和吟咏相对立的方式。一方面,唱曲之法流行于都邑巷陌,即《东京梦华录序》所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其法为歌妓所擅,亦即李扁《品令》所谓“唱歌须是,玉人檀口,……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这也就是当时人心目中的词曲“本色”,通常的说法是“叶律”,“使雪儿、春莺辈可歌”。从这一角度看,唱曲有别于士大夫之传统,是属于乐工妓人的语言艺术方式。宋代人批评苏轼等人“非本色”、不协音律,其实是说他们的创作未符合艺伎歌唱之风格。另一方面,“唱曲”是一种接受了方言或外来语影响的因声度词,因此,它在形式上有别于主流形态的诗歌,多为长短句,多用仄声韵。例如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记载:“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Ⅸ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这段记载说的就是“唱曲”。其特点在于:所唱为“吴俗岁祀”之歌,流传在使用方言的地区;其歌有“音律”,亦即有曲调;词随曲调唱为长短句,属因声度词;词用仄声韵,即促声结句,有别于汉语诗曼声唱诵的习惯。这四个特点是相互联系的,它表明,唱曲所代表的是一种非汉语雅言的传统。
在《碧鸡漫志》卷一,有“元微之分诗与乐府作两科”一节。作者王灼是反对这种分科之法的;这一态度恰好表明,声诗理论与“乐府”理论,其区别应当理解为两种音乐文化传统的区别。声诗派主张按汉语雅言诗歌的传统歌唱,此即“歌永言”的传统;乐府派主张按“胡夷里巷之曲”的传统歌唱,这包括“胡语”的传统和方言民歌的传统。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这是“诗言志歌永言”理论同“因声以度词”理论的最本质的区别。
换言之,从实践的角度看,“歌永言”理论与“乐府”理论,反映了宋代音乐文学活动中两个彼此对立的倾向。永言派主张歌永言、声依咏,实质上是维护搞藻之士的艺术习惯和音乐趣味,其依据则是由齐言平韵诗所代表的汉语诗歌曼声唱“字”的传统;“乐府”派主张随曲度,实质上是尊重新的音乐文学的本色方式,其依据则是由燕乐兴盛所造成的异域之“声”的丰富。在唐代,这种对立曾经表现为诗而声之(包括采诗入唱)的“声诗”与因声度词的“曲子”的对立;但人们尚能通过齐言、杂言的对比感受它。到宋代,对立更加细腻了,因而容易被研究者忽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撰曲”、“以诗度曲”、“麋括”、“着腔子唱好诗”等方式看到上述对立的存在。一般来说,“撰曲”、“以诗度曲”属于“乐府”派唱曲之法,“檗括”、“着腔子唱好诗”属于“永言”派唱诗之法。而关于词由“填实和、泛声”而来的说法,例如《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所谓:
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却
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这其实也是永言派的理论。因为它实质上主张维护齐言平韵诗的体貌,用和声来软化新声对于旧诗体的冲击。
总之,“诗言志,歌永言”这一命题在中国艺术史上的意义,主要是代表了一种同汉语习惯、同文人雅士之生活趣味相联系的文化传统。洛地先生强调“以文化乐”,认为中国歌唱的特点是“文体决定乐体”,亦即“依字声化为乐音旋律”,“以旋律传辞”。其学说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反映。尽管此说反映了宋以后“词唱”和昆曲之唱的若干特征,但我们却不能以偏概全,否认另一种传统——歌不永言、文不化乐之传统——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后一种传统,中国的语言艺术,包括各种因声度词的歌唱,也包括在佛教转读影响下形成的新的吟诵风尚,就不会有如此丰富的内容;而“诗言志,歌永言”理论,也会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个贫乏的伦理美学的主张。
责任编辑张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