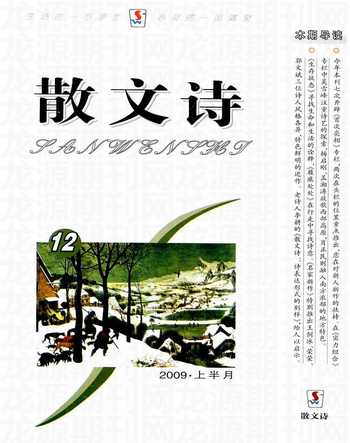故乡
2009-04-29早子
早 子
星光下的村庄
黑夜在眼皮上奔跑。村庄在睡梦中奔跑。
一片星光的思维在这个时候,酝酿着收获的讯息。
没有人听见它们奔跑的声音,那些精灵们的舞蹈显得神秘而安详。在黄土塬上,在一片蒿草中间,蕴藏着时刻都要被戳破的秘密。
村庄的秘密,一碗水的秘密。或者草地里兔子吃草的秘密。
星光下的村庄,在这个时候,你的安静总是带着丝丝孤寂。
我已不如三年前,再也无法倾听到星光下蛤蟆的叫声、蟋蟀的振翅声。而满眼的星光再也没有多年以前那么寂静。
这是命中注定的章节,字体瘦小。
低声与沉默中,飞低的星光是一群禁闭的鸽子,它们在村庄的屋檐上来回踱步,呓语甚至怀疑。而我多年来远离村庄,在陌生的城市一如既往地用脑力掩住眼睛做人,什么事物都模糊地替代了村庄夜晚里的星光。
一个人背负着孤独和泪水,享受着灯红酒绿,享受着城市的乌烟瘴气。可是,每当夜晚如期降临,我的思绪便被打开,充斥着噪音,遥远而难以割舍的思念,总是在这个时候多想自己是村庄里一丝狭小的星光。
踩着无目的的思念,在星光中,我的眼前是多年来一直徘徊的村庄的夜晚。
我走在照耀着村庄,也照耀着城市的星光中,我的内心有众多疑问。但是又仿佛没有一丝波澜。
一直以为星光可以像你一样沉默,千年如此,照耀着这座朴实、勤劳的村庄。
清晨
清晨是一丝阳光照耀下黄土坡边绽放的花朵,它的纯洁在此刻显现慈祥的面容。
我的母亲在清晨把青菜摘了回来,脚步声中我听见柳树在夜晚被狂风击打过的伤痛,而那些麻雀却早已在大地上捡拾了一嘴的露水。
偌大的黄土地,浓缩在这个小村庄里。土地深处流动的血脉在第一滴露水中遭遇了一场甜蜜的爱情。牛在早上出去,踏着我的睡眠,一片草地上蚂蚁们勤劳地背着阳光来回踱步。
若我的睡眠在梦境中一直长久地下去,没有目睹牛羊吃草的情景,直到那些阳光和风把我的被子掀起。
我也没有在清晨安排好大好时光,清晨是一片花海中央出水的女郎。
她的歌吟从渐渐展开的黄土地上,蔓延而来。村头的杨树成为新的聆听者,慢慢地,慢慢地村庄里喧嚣起来。
柳树尖角:半袋子洋芋
洋芋或者是半袋子温饱,一锅滚沸的井水。这是甘、陕交界的土地上随处捡起的故事。
它们的传说还在干旱与饥荒的年月流传。
只有一条沟底的溪流。默默无语。它比岁月更老,比人们的眼神更深邃,比一条大江更让人臣服。
这是甘、陕交界的黄土地上,一些从地里挖出来的歌曲,在阳光下被急速地传唱,阳光稀疏,一座座贫瘠的村庄在歌声中苏醒,一个个七尺的汉子在歌声中挺起了脊梁。
粗大碗对着太阳,壮身板扛着铁犁。
这些朴实的意象让我折服,让我振奋。他们在粗犷的歌声中,身形魁梧,在一片片绿色的梯田上,汗水与洋芋渐渐成熟。
我感到幸福,在柳树尖角的田地里,阳光是美丽的真实和幸福。
柳树尖角村庄的早上,半袋子洋芋的幸福是上天对这片干旱与贫瘠土地上人们苦难怜悯的大爱。
牛在沟里
“牛在沟里……”我告诉父亲。
牛是这片土地上勤劳的双手,它使父亲手中握着的鞭子一声声打着空气,却始终没有打在它的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这片土地上的人对牛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信任和爱。尤其是清早,当一阵阵牛铃铛的声响传来,总能听见村子里的人相互谈着这牛又壮了,看来最近的草料好呀。
黄牛喜欢在沟里吃草。它低头的瞬间,时光就过了。它从小时候一直陪着父亲,后来它的孩子又是我在沟里的玩伴。
很多和我同龄的孩子小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早上起来将牛赶到沟里,一起在泉水边抓蛤蟆,手里拿着一个小镢头挖上一把柴胡。
童年的时光就这样过了。
我长大了,牛却老了。它再也没有到沟里去过,拖拉机已经在缓慢中驶到了它曾经引以为傲的田地,剥夺了它一生的成绩。
现在,不知道牛还会不会在沟里出现,我想它们应该是可以更自由地在小溪边吃草、晒太阳了。可是,那一声声“犁沟,犁沟”却消失在了历史的尽头,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雪落在屋顶上
白色的精灵,口齿清晰。它白色的语言是屋顶上一大片、一大片的负重。
一个夜晚过去了,雪落在屋顶上。
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一丝的讯息。来得这么快,这么轻柔。
我在早上发现了它们。淡淡的寒气是这个季节最好的诉说。
远处的黄土塬沉寂在它白色的身底,看不清面目。而抬头红色的瓦檐却消失了,让白色的被子盖在了身上。
我对雪有太多的感情,甚至很多记忆也还在许久以前柳树尖角的雪里。
雪的到来。意味着寒冷与新年。
其实有些理由是无法被雪的轻盈所冲破的,因为,深邃的故事总是在夜晚的煤油灯下,才能谈起。
雪的降临是对冬天的慰藉。我想我可以在这样安宁的环境里享受一点点内心的孤寂。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就这样坐着,坐成了一个年成的结束语。而一段优美的时光已经在不远处翘首期盼。
雪落在屋顶上,落在村庄难以察觉的孤独上。无法改变的彻骨寒意让春天在人们的心里愈加神圣:雪落在屋顶上,母亲的眼睛忧郁而悲伤。她的女儿此刻在上海依然没有收到她亲手缝制的冬衣。
雪落在屋顶上,听见一炉子煤火在寒夜深处静静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