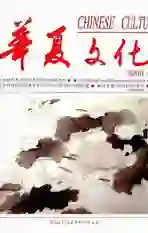关于“汉学”的反思
2009-04-29李江辉
李江辉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认识的逐渐深入,兴起了许多热潮。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生活对现实的补充和调节功能,反映了人们对传统的态度逐渐回归理性。在弘扬民族精神、构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特色,同时和谐地融入世界文化大家庭中,成为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在这些潮流中,国内的“国学热”,国外的“汉学热”尤为令人瞩目。
“汉学”主要有三种含义:
一是与“宋学”相对,专指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潮流,即“乾嘉汉学”,也称“朴学”。这是对清代经学家好儒信古,治经注重字句和名物训诂考据,反对宋儒空谈义理,推崇汉儒朴实学风的概括。清代汉学重考证,崇尚以汉儒章句训说经典,用汉儒注书条例研究群书,发展为以考据为重点的学问,包括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简牍学等。
二是国际汉学,指国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一般采纳德国汉学家奥托·弗兰克的定义,认为“汉学就是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欧洲早期汉学起源于传教士,在明末清初逐渐兴盛,开始进入学院成为一门学问,这与乾嘉汉学的形成时代相仿。他们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与人文,特别是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宗教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同时也包括某些“专学”研究,如敦煌学、考古学等。这类研究往往与其所在国家的学术思潮和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还会因为地理上的差异而展现出不同的特色。
胡适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这种启发主要表现在新颖的方法、独特的视角等方面,不拘泥僵化,因而显得内容丰富、观点独特。对于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中国研究就像一面镜子,他们的冷眼旁观,往往会呈现一些为我们忽视的东西。
三是泛指汉民族文化或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近年国内学者呼应国际汉学而提出的,意图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国际化的同时保持民族特色。
表面看来上述三种“汉学”似乎并无关联,但仔细考察近代学术史,却可以发现从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型直到今天,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加深,三者之间隐而不显的联系。
关于清代汉学的形成,近代和当代学者都有所分析。梁启超将清代汉学之名的确立归功于惠栋,认为惠氏治经求之汉唐注疏,“累世传之,惟古是信,惟汉是从,自是‘汉学之目,掩袭天下,而共尊惠氏”,“惠氏祖孙父子,而定宇最有名于乾隆间,以记诵浩博为学,其《易汉学》、《九经古义》、《后汉书补注》等最有名于时。‘汉学之名盖于是创始焉。”(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63页)朱维铮也指出,乾嘉之际的所谓汉学,“本指否定宋学、唐学而恢复贾、马、服、郑一系的东汉经学。”(《汉学师承记·导言》,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页)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清代的汉学不同于汉代学术,是以汉代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刘师培说过:“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著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名。”(《左宜外集》卷九《近代汉字变迁论》)然刘说也只及于汉儒的训诘方法与注书条例,还没有明言这种方法的内涵。章炳麟归纳其中优良的方法为六点,说:“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太炎文录初编》卷一《说林下》)
“汉学”一词作为对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学术的整体概括,其确立与流行源于江藩与方东树之间的争论,他们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汉学商兑》中对将乾嘉乃至清代学术概括为“汉学”的问题进行辩论,并将汉宋之争推向顶点。尽管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以“汉学”称乾嘉学术未必符合整个清代学术发展的事实,但后人在使用“汉学”一词时实际上还是依照江藩的理解来定义的。“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皮锡瑞《经学历史》)清代学者研究范围大都以经学为主,而旁及文字、音韵、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典制、校勘、辑佚、辨伪等。江藩是惠栋再传弟子,惠栋所标榜的“惟汉是从”是吴派治学的显著特点,江藩受此影响,称乾嘉之学为“汉学”,实际是想以吴派的特点来整合整个清代学术。
其实,对能否以“汉学”概括清代学术,历来是有争议的。乾嘉汉学的背景是汉宋之争,有着过分强调考证、忽视义理的倾向,随着乾嘉时代结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纯粹考据无益于身心,国家民族的弊端越发暴露,对乾嘉学术进行反思、改造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从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派别来看,既有以惠栋为首的吴学,还有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前者确有惟汉是尚、惟汉是从的倾向,后者则比较注意运用与吴派相近的考据手段发掘经典的原始意义,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等,表现出与吴派不完全一致的特点。因此,晚清时期的汉宋合流、今文经学兴起正是对乾嘉汉学的补偏救弊,在继承其考据方法的同时,重新挖掘“经世致用”之学,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治学理念得到继承发展。
章太炎、刘师培等重申“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赋予汉学新的含义,并积极借鉴西学,其经学、史学、文学研究融入新式学问,摆脱了乾嘉汉学的繁琐、僵化局面。从“旧学”中发掘“新知”。把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世界汉学大会2007”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章太炎先生称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吴宓先生称国学为中国学术的总体,钱穆先生则将中国文化概括为人统、事统和学统。然而无论国学是什么,无论国学的边界怎样模糊,它的内核始终是清晰的,它也必须成为汉学所关注的对象,并且与汉学相互激荡。”纪先生认为“汉学”或“国学”学科是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传承的内在脉络以及民族文化的内核。但是,清代“汉学”和近代“国学”在历史上都只是一段时期内的特殊学术潮流,并不代表整个传统文化,甚至它们在各自时代也并不被用来概括当时文化和学术的全部。
近代学者国学研究的对象还是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但对学术的态度与清代已有明显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继承明末的“经世致用”思想,借鉴西学,努力做到中西贯通。他们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密切,这种交往建立在真正的学术研究上。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与欧洲、日本汉学界之间相互影响,在语言、文献、观点、方法上互相启发。国际汉学界也吸收了许多清代考据学的方法与成就,特别是在语言、文字、音韵方面,较此前西方的探险式考察、旅行式介绍和基本文献的译介更进一步。二战后的国际汉学中心从巴黎转移到美国,研究兴趣和方法理论均有较大变化。例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研究,就是把“东方”作为西方的文化霸权符号来研究,现实色彩十分鲜明,是二战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典型代表。所以,海外汉学卒质上是外国学,海外中国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本国提供参考。
清代汉学的考据影响了那一时期的欧洲汉学,塑造了那个时期的“中国形象”;而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汉学又在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所谓“汉学”;我们似乎又在根据国际汉学这面镜子所反射的那个“中国形象”塑造着自己,这些都还是有待进一步反思与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