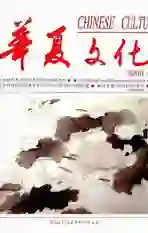从弃医从文到樊迟学稼
2009-04-29梁建洪
梁建洪
“文革”时期有一幅标语:继承鲁迅革命精神,狠批封建孔老二!在这幅标语中,鲁迅是学习的榜样,孔子是批判的对象,二者被对立起来了。抑孔扬鲁有许多原因,如孔子是封建礼教的奠基人以及鲁迅是打破礼教的急先锋等,其中还常常与两件事相联系:一弃医从文,是鲁迅从一个普通留日学生到一位文化斗士的转折点;一樊迟学稼,是孔子不事稼穑、鄙视生产劳动的标志。前者突出了鲁迅的革命性,后者折射了孔子的“反动性”,这是在那个把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的年代很容易得出的结论。
我们能够从弃医从文中理解鲁迅。假如鲁迅没有弃医从文,世间就会多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从老师藤野先生对其放弃医学不解与惋惜的神情中,可以解读出一个优秀学生光明的专业前途。而鲁迅比老师清楚中国的处境,当时的中国需要疗救身体的医生,更需要疗救精神的文士,鲁迅虽放弃了一种社会的需要,却投身于一种国家民族更大的、更迫切的需要。他的选择,体现了国难当头仁人志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如果从弃医从文的角度理解樊迟学稼,则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孔子形象。正如理解弃医从文离不开鲁迅思想转变的社会背景一样,理解樊迟学稼也离不开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孔子的社会理想以及孔子教育的社会功能。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这样的评价同样适合孔子,孔子也首先是一个社会变革者,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诸侯割据,时有混战,百姓痛苦不堪。孔子以天下苍生为念,把改变这个混乱的世道当作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有层次的,最高理想是实现社会“大同”,最低理想是实现天下太平。孔子渴求天下太平,叹息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天下太平的社会理想,反映在孔子与弟子的谈话中。孔子让几位弟子各言其志,对子路的张狂设想一笑了之,对冉有和公西华的仕途爱好保持沉默,而只有对曾皙的理想喟然长叹,深表赞同。曾点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志向,而是描绘出一幅图画:“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几个成年人聚在一起,不是被迫去当兵打仗,不是去服差役,不是去干盗匪的营生,不是组织起来维持社会治安,而是带上几个小孩,去沂河游泳,在岸边唱歌跳舞,这种画面在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东周社会是很难见到的。曾点的这幅和平丽景图,深深触动了孔子,引起了孔子的强烈共鸣。
孔子庞大的思想体系,都统摄于其理想之下。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过,他不能正确评价孔子,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大多数言论无非是教人在一定的场合下举止得当而已。罗素没有看到,在记述孔子言论看似零散的句子和段落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孔子的社会理想。天下无序的状态,归因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君臣角色与关系的错乱,重建道德体系与社会秩序,是实现天下太平的条件。表面上看起来缺乏系统性的孔子言论,其内容主要集中在教导君王如何为政以德、臣子如何侍君以忠、君子如何匡扶正道、个人如何道德自修等几个方面,这些都是社会道德与秩序建构的基本内容。孔子的思想是其理想的展开。
孔子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实践家,他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未能如愿,这并没有动摇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念。孔子深知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是一个有阶段性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推动社会由乱到治的转变,要力行于现在,也要冀希望于未来。孔子的教育活动,是其社会活动的延伸,培养学生继承平天下的事业,是保证其社会理想延续直至实现的逻辑选择。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培养大批弟子,在学术上形成了一个宣传儒家学说、推行儒家主张的绵延不断的团体。这正是孔子的希望之所在,《荀子·法行》记载,孔子谈“三思”时提到“老思死,则教”,就是考虑到死后的事,就要教育后人。事实证明孔子的愿望实现了,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大都游学于诸侯各国,“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为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后来儒学成为中国千年的正统思想,与一代代儒家弟子薪火相传不无关系。
与同时代的古希腊思想家、教育家苏格拉底的思辩性教育不同,孔子的教育具有明显的承传性,这一点反映在弟子对待老师学说的态度上。作为弟子的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学说持否定态度,亚里士多德又是其老师柏拉图的否定者。相反,孔子是名副其实的万世师表,弟子都是其学说的继承者,这是孔子学说能够始终得到传承和弘扬的必要条件。弟子对孔子言行的恭敬和继承态度,可以用颜回的一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来概括。在孔子那里,一个思想上高度统一的弟子队伍,于眼下是推行儒家学说的有生力量,于将来是推行儒家学说的全部希望。
批评孔子不事稼穑,不是现代文人的专利,早在孔子时代就有一位隐士荷葆丈人,当着子路的面含沙射影地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然后就开始耕作;还有一位隐士桀溺也当着子路的面,批评孔子师徒不自量力的社会活动,也是然后就开始耕作。孔子与隐士遭遇,常常与耕作相联系,实际上是百家争鸣时期两种社会倾向的尖锐斗争。隐士们的倾向是消极避世,正如隐士桀溺劝子路所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在隐士们那里,耕作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产劳动,而是一种避开纷乱的社会,隐居山林,追求悠然自得生活的象征,是一种蔑视社会旨趣而关注自然旨趣的展示。与隐士们不同,孔子倡导积极人世,胸怀太平盛世的理想,肩负拯救苍生的使命,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百折不回。鲁哀公向孔子问儒,从孔子的回答中择其一二,就可以看到儒家的形象,用现代汉语可以表述如下:“儒者,爱惜生命以等待人生的机遇,保养身体以准备有所作为。儒者,用忠信作为盔甲,用礼仪作:为盾牌,尊奉仁德而行,抱持道义而处;即使遇上暴政,也不改变他的操守。”
至此,从弃医从文的角度来看樊迟学稼,就很难得出孔子不事稼穑的结论了。在春秋乱世,孔子没有像隐士一样陶醉于人与自然的旨趣,而是肩负起倡行大道于天下的责任。鲁迅弃医从文,是放弃一种小的社会需要而投身于更大的社会需要。孔子骂樊迟学稼,是固守自己理想、忠于自己信念、坚持自己使命的宣言,同样是一种放弃小的社会需要而投身于更大的社会需要。孔子是重视农业生产的,而樊迟要学稼就具有与普通农人完全不同的性质,因为樊迟是孔子的学生,是儒学团队的成员,孔子曾对他和其他弟子一样寄予厚望。樊迟学稼,其兴趣由社会转向自然,说明他对孔子的社会倾向产生怀疑,转而对隐士的倾向产生兴趣,更重要的是,樊迟学稼给孔子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震动,这种来自儒学队伍内部的异样声音,可能会像瘟疫一样腐蚀儒家经邦济世的信念,给儒学的现在与将来带来严重威胁,孔子意识到了这种威胁。怒斥樊迟,是对来自内外挑战的回应。
尽管孔子是封建礼教的建构者,而鲁迅是其拆除者,但从弃医从文到樊迟学稼,可以看到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关注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公共使命感,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统一于大仁大爱。行医治病是爱,但与疗救民族的精神相比就是一种小爱;耕种是爱,但与疗救满目创痍的社会相比就是一种小爱。鲁迅弃医从文,是弃小爱而就大爱;孔子斥樊迟学稼,是止小爱而守大爱,这种大仁大爱,就是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