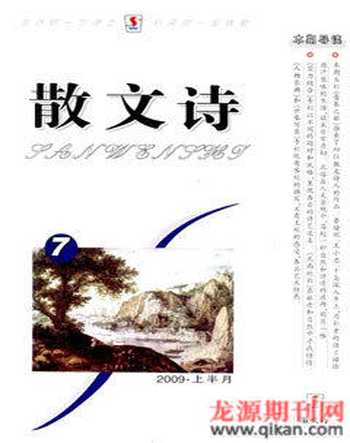理论的理论:当代散文诗理论建构的基点
2009-04-29方文竹
方文竹
一位既写散文诗又搞散文诗评论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征求对他的散文诗评论的看法,我不客气地认为:体的评论当然写得不错,但明显缺少理论的理论。一篇诗论连几个像样的学术名词术语都找不到,尽是些经验式的随想。居然对当代散文诗说三道四。我却不以为然。
我认为。目前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引起笔者的焦虑理所当然。这里,我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我一向认为。理论思维比知识更重要。这是从普遍性说起。具体到散文诗理论。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散文诗批评家是一个不合藉的散文诗理论家,甚至可以说不能称之为批评家。理论思维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逻辑思维,拥有以哲学—-理论的理论——为根基或逻辑起点的知识体系,学理性、学术性、规范性是她的特征。同时,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有着她的源起。如尼采的“强力意志”、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巴赫金的“复调”“对话”、佛克玛等的“后现代”、德里达的“解构”等给文学带来了何等巨大的灵感、冲击与突变。而比较当代散文诗理论界,这种理论思维甚为缺乏。散文诗理论的理论源起是什么。恐怕没有谁说得清楚。
按照文学理论惯例,我将散文诗理论结构划分为三个部分:散文诗理论——散文诗批评——散文诗作品(理论)史。散文诗理论取白散文诗批评和散文诗作品(理论)史的资源并对其进行宏观概括和指导,而散文诗批评和散文诗作品(理论)史推动着散文诗理论的发展,三者相辅相成。同时必须强调,看待散文诗理论三个部分的水平的关键还是散文诗理论,我将其称为“散文诗理论的理论”。“理论的理论”是当代散文诗理论批评的“母本”,一切散文诗的理论批评皆是它的变形与放大。以下我试图梳理一下中国当代散文诗理论地形图,以期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
散文诗史:以学院学者为主体的学者型,如孙玉石、彭燕郊、王光明、秦兆基、李标晶、蒋登科、黄永健、刘谷城等。
散文诗批评:以散文诗作家为主体的评论家型,如柯蓝、耿林莽、徐成淼、邹岳汉、王剑冰、冯明德、陈志泽、空间、蒋伟文、李皓等。
还有两者之间交叉型的。
当然,不是没有突破,没有些微的春色:我们欣喜地看到,黄永健教授拓荒式的工作,他的大著《中国散文诗研究》专立“散文诗本体论”一篇,仅“本体”两字就显示出“理论的理论”的迹象来,其内容有“散文诗本体的形式及其生成”“散文诗的结构~散文诗的审美功能”、“散文诗的文体地位”等等,这些都是对“理论的理论”的靠近,尤其“现代汉语背景”的提出极具学术意味。
以上这些师友都是我所尊敬的。但从发展中国当代散文诗的总体和要求来说,他们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老实说,我们不缺少细读式感悟式经验式的散文诗评论家(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美学传统,但与西方批评相比已显弊端——这一点已有大量论述,且成定论),但一定缺少理论视野宏阔、根基扎实、见识新锐、体系严密的散文诗理论家,或说缺少“批评家的批评家一元批评家”。我们急需像弗莱《批评的解剖》、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等那样划时代的巨著。
当代散文诗理论如果没有学术性,她就不会让自己真正地独立起来,从而获得自己的“身份证”,更谈不上对散文诗创作有什么指导和促进,以此提高散文诗在文坛上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学术性是什么?前已所述,就是理论思维,散文诗“理论的理论”的建构能力。
当然,提出“理论的理论”对散文诗理论批评家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首先是理论思维的能力,如上所述,主要体现在哲学和各门学科的素养(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在知识结构上打通中西文化的壁垒,理论建构的能力及预见能力,美学和文艺批评的知识水平,对散文诗文体特征及散文诗史和现状的熟悉与把握,对散文诗相关文体的知识掌握等等。更重要的是对散文诗文体的专业化追求。我甚至偏激地认为,真正的散文诗理论家应该远离创作实践。要有学究气。我在某种程度上倾心于学院派理论批评家。
目前讨论最热闹的问题,或说在报刊书籍网络口头见到听到最多的问题——什么是散文诗(什么又不是散文诗)以及散文诗与诗和散文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十足的陈旧、老套、狭隘、肤浅、短视、浪费。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更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试想一想,假若散文诗是什么分得很清楚了,限定死了,那会出现什么局面呢?你能为小说、散文下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吗?这里至少缺乏一种美学的态度。我曾提出散文诗的“未完成性”,意即于此。
本文的论点很可能遭到“文本实践论”的批驳,如人们平日里总是主张建立散文诗理论应从散文诗创作实践出发。初看起来这个观点很堂皇,真理在握:一切理论来源于实践嘛,作为处于发展中的当代散文诗来说更应当如此,否则便是空乏无力。但是,这个观点并未抓到问题的根本:理论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和规律性,反过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是更为重要的。同时,理论也可以在理论中发展,甚至可以说,在理论自身中发展的理论是理论中精华的部分,对理论家的主体建构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些。当代散文诗理论的贫乏已成痼疾,她的独立性要求更在于她的自身的先天性不足,她的“理论的理论”显得更为急迫和重要些:“脱离实际”的“理论的理论”将为当代散文诗理论搭起构架。
最后需申明的是,本人的这篇小拙文同样缺乏“理论的理论”,它只不过是一次呼吁罢,意在揣摩一座宏伟大厦的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