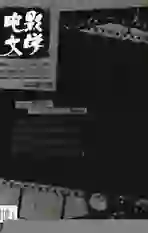李民访谈录(上)
2009-04-19张锦
张 锦
时间:2009年4月23日至7月14日
地点:吉林省长春市,李民家中
采访:张锦摄像:谷鹏周夏
文字整理:平萍照片:周夏本稿审定:张锦
受访人简历
李民,本名王度,男,1918年生于吉林市一个中医家庭。在吉林市读中学时期即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35年10月赴日本留学,1936年4月考入东京日本大学艺术学院攻读文艺创作。1937年7月8日出版了日文诗集《新感情》。在日本发起成立文艺团体“影艺之友”社,自任社长,在东京出版了一期《影艺之友》杂志,1939年1月因共产党嫌疑被捕,1939年5月被判驱逐出境,返回吉林市。1939年9月,离开吉林市到长春的满日文化协会工作,开始参与“艺文志”派的文学活动。1939年底,加入“株式会社满州映画协会” (以下简称满映),开始从事宣传,隨即专事剧本写作。在满映第二年起以“姜衍”为笔名创作了《龙争虎斗》《娘娘庙》《黑脸贼》等多部满映最卖座的影片。同时,继续以“杜白雨”为笔名从事文学创作与评论活动,并组织国都乐剧团,受到日伪更严密的监视。1943年6月逃离伪满洲国,化名“王介人”在北平继续文学创作并入武德报社、华北电影公司工作,同时开始参与共产党的活动。1945年8月赴华北解放区。光复以后回到北京,又被国民党以“伪职人员”抓捕,1948年3月出狱。年底,被送到华北大学学习。在此期间改名“李民”,并沿用至今。1949年后回到长春工作,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在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作为教授离休。
采访大部分采用受访人根据文字提纲自组讲述内容,有关问题很大一部分为文字提纲中的问题。本文为访谈节录,内容顺序与文字做了相应调整。本稿经受访人本人审闼同意。
早年经历与日本留学
张锦:您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是怎样发现自己在文学方面的天赋的?又是怎样开始文学创作活动的?您的教育经历跟您后来从事文艺工作有关吗?
李民:我父亲年纪小的时候家里穷困,没钱读书,被送去做中医学徒,出徒后就在吉林市行医,先在家里挂牌子,待行医有点名气了,就到世一堂坐堂。后来到教育局当财会科长,炒货币发了点财,便科长也不做了,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受的教育,是新旧参半的,新学加旧学。我写诗填词,得到老师的特别夸奖,我那时候很高兴,对旧诗旧词特别有兴趣,像李后主的词我背得很熟很流畅。我的少年时代还跟别人很不一样,我学武。我那时对武术非常迷恋,后来就变成白天上学校学课程,晚上练武。另外呢,我学的东西很杂,还学着画画,学人家变戏法。所以我这个兴趣很广泛,干什么没三天半新鲜,一会儿搞这个一会儿搞那个,为我后来写文章提供不少材料。但是我在学校里面的成绩,国语、英语、历史这三门课程是拔尖的。别的理科我一点都不行。从15岁以后的四年,我就逐渐地转向文艺创作了。我父亲对我搞文学搞学问是特别支持的,他常跟我说的话我印象最深了。他说咱们家有钱,不在乎生活问题,你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你不像他们生活困难,学医的、学工的、学建筑的,都是实用的,一毕业就能就业,他说你不用,你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这是我父亲对我最大的鼓励。
张锦:您少年时代喜欢看电影吗?能否谈谈有关情况?
李民:那是我投稿的一个主要方面。我怎么去看电影?一个是吉林市俱乐部,那里有电影院,我就经常去看电影,对电影兴趣特别大。我看完电影就写个感想文,一篇五六百字,交给影院经理,姓陈。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卖点门票,他就给我发表。还记得那小报上是红色的字印的,我就特别兴奋。他还给我几张电影票,替你发表了还送你电影票。于是一有新片子我必去,写了短文他给我发表,更引起我发表的欲望。
张锦:您后来到日本的经过是怎样的?
李民:依着我父亲的意思就是准备将来上北京读大学。九一八事变以后学校呈现混乱状态,没有秩序,所以有同学说咱们趁着机会升学吧,升到高中去,就那么稀里糊涂也没拿初中文凭就升到高中去了。我念文科,但是高中没毕业,上了两年半。这时有个同学叫张英华的,就是张辛实,他也爱好文学,喜欢电影,他有天跟我说,咱们毕业也没有地方去,不如到日本去留学,这条路日本人放开了,咱们到那里去学习好不好?当时我一想,能到日本,文化比我们高,到那儿学一些东西不错,就这样抱着学习的愿望,我们两个人拿着护照就到日本去了。我们高中同班同学有个叫李长春的,先到日本,他照顾我们。按照他指引的办法我们学日语,然后考进大学。所以我到日本留学没有经过充分的考虑,也没有经过家庭的同意,是张辛实诱导我去的。
张锦:1936年4月您考入日本大学艺术学园文艺创作科,是这样吗?经过是怎样的?
李民:1936年年初,我考入了日本大学。当初为什么选这个呢,因为我就对文学艺术特别有兴趣,它里边有文艺创作科。我入学考试非常顺利,写一篇作文,然后会话,就是和你谈话,他们说你日语怎么说得这么好。这个学校所实行的是美国的道尔顿制,这道尔顿制就是自由主义学习方法,你也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你选科有自由。他里面有文艺创作,有音乐系,有电影系,有戏剧系,还有美术雕刻,这么些科,你一进门就听见地下室的钢琴声不停地响,再往里走,那边舞台上正演戏。旁边往左边一走,一个摄影场,一天到晚在那儿搞电影。文艺创作就是在课堂里学习。我学的是文艺创作,但同时也学电影发达史,艺术概论,戏剧概论,美学概论,音乐概论,这些东西都有,怎么写童话,怎么写小说,这些课程都有。
张锦:艺术学园的学制是怎样的?
李民:三年,艺术学园的学制都是三年。
张锦:张辛实为什么选择电影学习?他们的电影课程您当时去听过么?教学方式是怎样的?
李民:张辛实选的是电影科,没出国以前他就有那个意思要学,但是他不知道日本有这个学校,到那儿以后就选择这一科了。一般都是听大课,很少分科教学,也有分科,你像我们创作系就有创作漫谈,有一个作家领着大伙分析一篇作品,大伙提意见,或者学生自己写一篇上台上宣讲,讲完之后大伙给他分析批判,也给提意见,老师总结,就这个方式。电影也是这样。
张锦:在日本的时候您经常看电影吗?都看些什么电影?
李民:我有时候不怎么愿意去上课,我就去看电影,看小说看电影,就是懒得上课,把论文交了就行。那时候东京的那些电影院我差不多都走遍了。后来我看电影是把电影当课程来品味,来咀嚼,看一看电影的镜头怎么样啊,人物的表演怎么样啊,情节怎么样啊等等,从实践课程、电影批判这方面来看电影。看了很多,差不多欧美的著名电影我都看了,因为那时候这方面在日本很盛行,世界各国的艺术他那个地方都有。包括左翼文学、左翼电影、左翼戏剧全有,日本有个剧场叫筑地小剧场,学习苏联剧场做法,演的都是进步的戏,有时候我也上那儿去看戏。
张锦:能否谈谈您在日本和张辛实发起成立文艺团体
“影艺之友”社的经过,以及后来受到日本人监视和关押乃至驱逐出境的经历?
李民:我到日本后的文学活动没有停止。我和张辛实琢磨着搞个文艺团体,原来没打算出杂志,打算搞一个文艺小社团似的,找几个留学生爱好文学的大家聚在一起,采取漫谈的形式谈谈文艺界情况,搞点文艺评论什么的。后来张辛实提出来是不是搞一个总和性的杂志,戏剧电影文学这些东西都有,这样能够受留学生欢迎,还能办起来。后来我俩合计就组织这么一个,有七八个人吧,这七八个人里就我和张辛实是搞文艺的,剩下那些人都是半拉子,不是专搞文艺的。我们推举出一个姓李的做副社长,张辛实做主编,我做正社长。
影艺之友社就这么成立起来了,出了一期。撰稿人有古丁,我写了篇小说,张辛实写了个剧本,还有别的一些零碎东西,出了这么一期。这一期大概是16开本的吧,那一期有那么四五个印张。但是成立这个杂志社以后就引起警察注意了,警察认为有一个問题,我后来了解到,就是影艺之友的“之友”,他认为你这个“之友”就是团结一心志同道合的人想闹事,他对这个特别注意。重点很明白,都集中在我身上,所以警察就找我,找我态度非常恶劣,有时候我还有人跟踪,我下电车他就跟着我。所以《影艺之友》出了一期就黄了。不久我就被捕了。我一被捕,影艺之友社那些人都跑了。后来李长春通知了我家人,我父亲雇了一位日本律师叫岛博通,最后给我判了个“起诉犹豫”(暂缓起诉),返回吉林。
“满洲映画”
张锦:请谈谈1939年您离开吉林到长春参加满目文化-协会工作的情况。
李民:回国以后我得找点工作,呆着也不行。那时候,我通过一个文友谭莫迦认识了辛嘉,住在他家。他在《明明》杂志当主编,我在《明明》杂志上发表稿子,有散文,有诗,还有论文,我们俩是文友。辛嘉在满日文化协会工作,领工资。满日文化协会,没有具体的工作计划,好像是个什么茶馆似的,有关文学艺术的事情都可以进来活动。有日本文艺界的人活动,也有中国文艺界的人活动。他就是在满日文化协会里当嘱托。
我在满日文化协会做什么工作呢?当时伪满建国大学有个历史教授,日本人,叫大森,他写的日本两千年历史需要人翻译。我在文化协会期间,就做这么一件事,就是翻译这本书,但他没有出版,可能做内部教材。凡有文化界来往,差不多每天都有宴会,我那时天天参加宴会,喝酒,吃好东西,天天玩。
张锦:接下来您加入满映并担任脚本员的经过又是怎样的?
李民:1939年9月份到12月份,我在满日文化协会当嘱托。到12月份的时候,当时有个作家叫古丁的,他是当时伪满的大作家,给我介绍的,我也有这意思。满映当时刚建立不久,挺缺人的,尤其缺比较高一些人才。古丁跟满映有关的人一说,我就到满映去了,没有经过什么上层的介绍,也不认识别人,就到那儿去了。因为满映一看我的论文,一看日本大学学历,专学艺术的,学过电影,所以他们很欢迎。去了当时他们没有把我用在电影的实质地方,把我放到宣传课,在宣传课做一般的人员,就是写电影广告,关于明星的什么什么花絮了,写零七八碎的稿子。有时候领着演员到外面去参加演出什么的,搞宣传方面的杂务,搞这些东西。大概就是1940年末吧。他们知道我能写稿子,写了很多东西,一说就把我调到文艺课去了。
张锦:您当时看到的宣传课是怎样的?
李民:宣传课里边有几股,有3个股长,就是领导关于宣传方面的工作。那个课长姓陈,中国人,叫陈承瀚,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英语呱呱叫,平常说话什么的都用英语说得很漂亮。日本的课长叫长谷川溶,这人是日本的一个二流小说家,他平常上了班就是写小说,一言不发,也不关心电影宣传的事情,他就写自己的小说。陈承瀚呢,叼着大烟斗,说着英语,就是闲谈,也不关心电影的事情。这两个人上着班等于没上班一样,跟没这么个人差不多,都由下边的股长掌握实际工作,我们就跟着在里边打杂。另外就是赵孟原主编的《满州映画》,他那宣传课里边最经常的工作就是每月要出一本杂志,就是《满州映画》。有的时候我也领着演员去灌唱盘,领着演员到剧场演出,也搞这些个宣传的杂务。
张锦:当时主要是哪些演员呢?
李民:季燕芬,季燕芬跟我的关系不错的。我那时兼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嘱托,满映需要歌手没有别人,就让季燕芬去,季燕芬唱得还不错,由我领他到那灌唱盘,去了好多次。季燕芬这演员确实不错。
张锦:除了季燕芬之外还有哪些男演员吗?
李民:别的男演员还真没有谁。不过后来跟季燕芬的哥哥季友梅接触比较多。因为当时文艺课的人和演员接触的非常少。演员主要是跟导演接触,关系近,他有利用价值,跟剧本员隔一层关系。
张锦:那么文艺课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李民:文艺课课长当时是大内隆雄。大内隆雄是日本的左翼人士,是共产党脱党的,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那地方工作。以后他转向了,叛变了。然后他就埋头翻译,什么也不干,就是翻译文学作品。他的中国话不行,说话不行,但是文章他都能看得懂,中国的小说,像古丁、山丁他们的小说他都翻译。上了班就坐那儿翻译文章,一直写到下班,一句话也不说。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人。电影他也不关心,因为他好像不懂电影,也不搞电影,他是文艺课长,就是搞他的文艺翻译,文学翻译。
那时文艺课里边的同事有梁山丁、小说家张我权,还有张辛实——张辛实没有到过宣传课,他是直接到文艺课去的,也是经古丁他们介绍去的,还有北京来的叫王智侠的,沈阳来的一个叫韩护的,基本都是文艺界的一些人员。看那意思就是进满映工作,进文艺课工作很简单,很容易,只要有人介绍就可以进去。
张锦:当时“满映”吸收脚本员的条件是什么?脚本员跟制片厂之间的工作关系又是怎样的?
李民:满映那个脚本员不是把一些个专业的戏剧作家请那去的,不是。他随便找一个搞文艺的,甚至有不搞文艺的也找去了。经别人介绍就到那儿去,就像安排个工作一样,找一个站脚之地。所以乱哄哄的也不坐班,大概是礼拜二、礼拜五两天可以去去,平常呢不去,没什么事,也没有固定的任务,你愿意写就写,你不愿意写就拉倒,没人管。有时很简单地做一些号召,让大家写东西,但是很多人也没写。
另外需要说的就是他那地方脚本,日本人的那个脚本和中国剧本不一样。咱们那个剧本一写就成大块文章,就像写戏剧似的,他那个不是。他那是分场面的,把场面分出来;另外呢,有些地方可以分镜头,加上镜头,可以分出来。比如说这一个场面,他可以分几个小场面,分什么镜头,镜头的转换直接用什么手法,懂的人呢都可以加上。那意思是什么呢,脚本就是处在剧本和导演拍片子脚本中间那个东西。你可以写剧,你可以把导演要求的东西写上,摄影、导演的东西要点要求你可以写上,导演根据你这个脚本再做一下演出的处理。所以,满映的脚本和日本脚本就是这样,没有可读性,拿来一看零零碎碎的,许多场面凑到一起的,因为他主要是拍片子,不是为了阅
读。天上一个月亮下边一个重叠镜头,没什么意思,什么近写、远写、特写,都可以加上。我写这些脚本都加上镜头转换,手法、场面组合,有些特别要求也写上,导演采纳不采纳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他那个脚本员,文学修养不高的人也可以写,因为写出来这些场面,不是供给阅读的,是供拍摄用的。所以往往读起来没什么意思,思想的连贯性也很差,只是供给导演、摄影师用的。但是也可以提出技术要求来,比如说夜景里边,我要求什么样的神秘色彩我可以提出来,要求导演和摄影师按照这个造出这样一个场面,造出这种气氛,你可以提出来,但是导演不一定采纳。也还是个导演主导,导演是一家之主。
张锦:当时满映的脚本员您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李民:文艺课我记得有这么些人:一个叫韩护的,是个聋子,经常写些散文、小说,在报纸上发表,有点小名气。第二张辛实,第三张我权,张我权这个人呢还有些才能,写些个诗歌小说什么的,也写剧本。再一个山丁,山丁是小说家。还一个叫王智侠的,是北京人,这个人悠悠荡荡,没什么学问,也不能写什么东西,就是混事的。但是满映那时候很奇怪,不一定经过选拔,把些作家能人选到那儿去,他好像日本一般公司的做法似的,反正有谁介绍的话,就作为一般的社员,可以参与到里边。到文艺课来也没什么固定的工作,也不是要求你每月要写几个剧本,没这个要求,挺散漫的。还一个叫关枢的,关君蔚,在日本是学林业的,很有些才能,《红楼梦》什么的都读得很熟,也能写两下子,但他写的剧本没见通过。脚本员大概就是这样,满映好像对脚本员的任用和使用,都是马马虎虎的,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
张锦:您在满映第一个创作古装片,能谈谈您在满映开始这一类片子创作的经过吗?日本人是什么态度?
李民:我到那儿以后还认真地写了些脚本。我写这东西有一个极其简洁的机制,就是为什么我写东西要写古装的东西。这什么意思呢,最早一部大概是《娘娘庙》,我的意思就是逃避政治,因为你要写现代东西的话,什么王道乐土啊,什么讨伐抗日部队了,讨伐抗联什么,难免涉及这些东西,写古代东西就没事了。我用“姜衍”那名字,张我权他知道,他说我明白你那意思,你是将就敷衍a我说,我心里话是那样,我就对付了,古代可以随便写,审查上没问题,主要是这么一个意思。这就好像我讲文学似的,讲文学我愿意讲古文,你想你讲现代文章的话底下人听课给你记下来找你毛病,从政治上思想上迫害你,但是你要讲古代文学的话就没这问题了。所以我以后都搞古代东西,或者我搞什么理论逻辑,整这些东西,避免政治的问题,因为我在这方面吃的苦头太大了。
张锦:能否谈谈您创作这些古装电影的情况以及上映后的反响,比如《龙争虎斗》《娘娘庙》《黑脸贼》等。
李民:我写古装片,大概最早是《娘娘庙》。我认为娘娘庙这个传说,在民俗方面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各个地方都有娘娘庙,有庙会。我小时候上吉林北山庙会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有意思,很有意义,增加人们的想像力。起初搞的是什么呢,是描写各个地方存在的娘娘庙的姿态,这个建筑啊,塑像啊,写这些东西,类似纪录片的性质。当然里边带有什么呢,三宵什么云宵什么琼宵的,她们怎么样下界,怎么样活动,带这些故事,当然主要拍摄娘娘庙的建筑,它的建筑风格、雕塑风格。这个片子拍出来后,有的日本艺术家很赞赏,不是赞赏我这脚本,而是认为这片子有一种土气,因为娘娘庙在各地农村,大石桥的啦,吉林的啦,他说照的这些,一看都是很土气的建筑,土气的人物,看完之后觉着浑身都是土。那是很内行呢,他说日本人拍电影讲感觉,讲什么初期的感觉,电影能把这种特殊的感觉给你表现出来,它跟一般的大庙不一样,跟一般的佛教道教庙,跟那庄严宏大的气氛不一样,它这种土气是很特别的。我得到他们表扬啦。
所以我写这类剧本每年得年末奖金都是最高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龙争虎斗》。有部古代小说叫做《五女七贞》,小说写些个女英雄的活动,考状元啦,夺状元什么的,我就把这个改写了。为什么写这些东西?一个政治上安全,另一个这些东西有武斗,武斗的片子受欢迎,再一个就是古装东西上海也有,也很受欢迎,我说满映是不是也可以搞搞这个东西,我就写了这部。这部片子脚本写出以后,是山内导演,我还跟他们一块到吉林,在鞍山采外景我也去了。没有想到,这部片子票房价值这么高,群众这么欢迎。怎么知道呢?有一天上班在文艺课那儿坐着,制片部的部长坐得离我不远。有一个电影院的经理来了,一进门就恭喜恭喜,部长说什么事,哎呀,了不得,你这部片子跟上海电影有同样的票房价值,同样地受到欢迎,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他们在那儿闲聊,我就知道这部片子成功了。当时没有分上下集,导演就把它搞成了上下集。到年末的时候,我记得大概给我500块奖金,当时我每月挣120块钱。
有一次,制作部部长牧野在中银俱乐部开会,日本电影界来了一些人,把我也找去了。他们自己在会谈,因我懂日语,听他们谈。日本人说,哎呀,你可了不起,你继承你父亲的事业,你父亲搞古装片搞出名了,你也搞古装片大获全胜。大伙祝贺他,他厚着脸皮说,是他出的主意,他们家族都是搞这个的。其实事前他根本没跟我们谈什么,他把这功劳揽过去了。
后来有一天找我,说是牧野部长要公出,到北京去参观学习,只让你去。我很高兴,北京我没去过,大邦之地,想看看去。所以我就跟我们文艺股的股长,叫西村的。还有牧野、我三个人,带两个秘书去了。让我想不到的是到北京旅馆之后,牧野拿出些钱来给我。唉,我说这是什么事儿啊,西村说,你收起来,是给你的零花钱。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日本电影界的习惯,拍片子对好导演,对脚本家,或者对演员,有特殊贡献的人,这个经理,董事长有时候就给零花钱。给的钱不少,给我100多块钱,然后西村要钱牧野没理他。
张锦:满映职员制度是怎样的?脚本员的待遇怎样?
李民:职员待遇方面,有雇员、职员,在职员上边才能当股长、课长。像张辛实他们都是雇员,我那时给我提成一个职员,宣传部部长给我写介绍信,写王度职员,我当时想哪个不是职员,都是职员,其实不是,是公司规定算是第二级,就是最次的第二级,倒数第二级。
再有满映那脚本员没什么待遇,就是工资,一个是工资一个是奖金,年终奖金,根据你的贡献有高有低,最低一个月。我在满日文化协会是90块钱一个月,相当于高中教员的最高工资。到了满映以后呢,当时我就提升了,一个月125块,相当于一个中学校长的工资,到我逃亡以前给我提升到导演了,是150块钱工资。
张锦:您在满映时期的电影审查制度是怎样的?这对脚本员有些什么影响?
李民:伪满的弘报处对文艺作品的检查政策,本身是很严格的,不许这不许那的,甚至于恋爱过分了也不行。说得很严,实际上不是每件作品交给他,他都细细地检查,然后给你批准,不是这样,他是马马虎虎的,外松内紧的。怎么回事呢?在弘报处检查这方面,大体检查下就
行了;暗中是警察掌握,这东西让你发表,发表以后警察找你麻烦把你抓起来,他采取这种明松暗紧的办法,所以实际上掌握检查的是警察和宪兵,而不是弘报处的官员。弘报处的官员经常到满映去,到满映一般去看一看,也不说什么就拉倒,好像他不管似的,实际上警察、宪兵背后监督得非常严格,它是这么一种两面政策。
张锦:您到满映的时间是甘粕正彦上任之前还是之后?1939年底您和一批中国作家加入满映,这是否跟甘粕上任有关?
李民:我到满映时候甘粕还没去呢。我是1939年底,这年底张辛实大概在我之后也入了满映。跟甘粕没有关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甘粕是啥呢。
张锦:甘粕正彦启用中国人您觉得是否还有打击根岸宽一的因素?有资料说满映建立初期实权掌握在林显藏的手里,你是否接触过林显藏?
李民:甘粕是跟根岸他俩是矛盾的,明和暗不和。由于甘粕是外行,根岸本身是当过导演,是一个电影企业家,也是电影艺术家,甘粕就是凭他自己的政治权力,排斥根岸的一派。但是他也想自己找一派人,他把八木保太郎他们找来之后,打算领一帮人,大概领七八个人打算代替根岸那一派,结果不成。因为他没有实力,艺术上他没有实力。林显藏不知道,这个名字根本不知道。
甘粕来了以后大删大砍。把总务处长叫山梨的给罢免了,另外一个把制片部部长牧野也罢免了,赶回国去了。人事部长上日本东京物色高级人才,他后来物色了一个制片部长,叫八木保太郎,是日本一流的剧作家,又物色了四五个,都是剧作家,没有导演。他可能给予更高的待遇吧,找来这么四五个人,这些人在日本的学术界都是有地位的,所以他们跟根岸在满映的那批旧人不一样,他们都很高傲的,敢跟甘粕讲价钱。八木保太郎跟我不错,来了以后我们俩关系很近,他说,临来以前就跟我一块来的人说了,把回去的路费准备好,一旦不行的话我们马上就回去,很高傲的。来了以后他代替牧野当制片部长。他的意思首先是认为近藤不够格,因为近藤一条腿,那条腿给割掉了,他说缺一条腿不能到现场指挥,没有资格做制片部部长。但是他说我提出几回——他告诉我的,他说开干部会的时候,我提出了,但是根岸不同意,他说再等一等。满映那个会有一特点,我听他们说的,课长以上的开这个会有一个不同意的,这个事就不通过,要在满映想升官很难的,所有课长都投这个事,没有人反对,才能通过。后来八木就领几个人去,他们确实很有学问的,我一来他们就跟我打交道,怎么跟我打交道呢?因为当时写剧本的里边只有我提出的剧本引起他们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