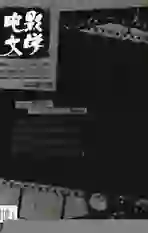后现代的印记
2009-04-19冯岭
冯 岭
[摘要]黄建新在电影里表达的那种对社会流弊和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十分写实的,并混杂着现代主义,但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在市场规律的制约下,他加强了电影中的后现代表达,本文从以黑色幽默的态度来对待现实与荒谬;对文化符号的运用和拼贴;解构精神的阐扬等三个方面来论述黄建新在作品中所留下的后现代印记。
[关键词]后现代;黑色幽默;解构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环境宽松,各种西方文艺思潮迅速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时中国文化的内部,文化心态解放,主体意识回归,而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诉求却面临历史批判和现实利益的冲突。中国艺术(包括电影),需要一次文化的解构,需要消解政治一元话语以及新时期建立的强调人的主体性的理想主义话语。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强调解构权威、消解中心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恰逢其时的进入,催生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这一状况直接导致了艺术上盛行未久的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滑行,正如柯勒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并非一种特有的风格,而是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在某种情景中,这意味着复活那被现代主义摒弃的艺术风格,而在另一种情景中,它又意味着反对客体艺术包括你自己在内的东西。”从整体上说中国艺术包括电影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接受现代主义的洗礼,就发生了转向,成为与后现代主义对话与交融的场域。
中国电影艺术创作者在此时也已感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力,他们从中国文化的特殊语境出发,对于后现代主义加以鉴别与接受。而黄建新就是最早感应这股思潮并在创作上卓有成就的导演之一。他的创作意识和方法主要是基于都市题材的新写实,并混杂着现代主义。把人作为表现中心,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大胆地追踪,对现实主题敏锐的选取、追求艺术表现的个性化和开放性,这些作为热点,被评论者与观众讨论最多。
不过,我们不得不看到,此时,中国电影开始空前地受到市场的压力,为了适应新一代观众,黄建新逐渐削弱现代主义,弱化人文色彩的探索性,淡化政治性,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并线,转向“后现代”黑色幽默的呈现、文化符号的运用和拼贴,以及解构精神的阐扬等等。他的创作嬗变,与其说是一场艺术观念上的变异,不如说是以“后”的方式所进行的形式上的革新和丰富。他的影片在创作方法和技巧的运用上,留下了鲜明的后现代印记,进而为市场提供了既有商业价值又有文化深度的作品。
一、以黑色幽默的态度来对待现实与荒谬
黄建新总是面带笑容地讲述在命运拨弄下的苦恼与挣扎,从小人物的生存境遇中发现荒诞意味和随之而来的喜剧感。他擅长将电影语言的生活化与意象化较为自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通过情节设计和对白表现出一种冲淡、平和的幽默。用自我解嘲的幽默来反映困惑、焦虑的心理和人生渺小的意识,往往具有黑色幽默效果。所谓“黑色幽默”,是指把悲剧性的东西置于一种近乎喜剧的氛围之中,引出苦涩笑声,作为人类对生活中明显的无意义和荒谬的一种反响。“黑色幽默”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审美主张和人生态度,更是一种后现代解构的创作方式。
黄建新的影片往往以黑色幽默的态度来对待现实与荒谬,使人在辛酸的笑声中思考和关注社会和人生,在荒诞的玩笑中获得宣泄的快感。《站直,别趴下》中的知识分子夹在暴发户和保守官僚之间尴尬和无奈,在剧情的缓慢推进过程中,黄建新把人际关系的本质慢慢地剥离了出来;《背靠背,脸对脸》中,—个文化馆副馆长为了争取到“一把手”的位置,费尽心机,但他越表现出他的才干,却离自己预设的目标越远,影片的荒诞意味就产生了,就产生于社会空间、人性空间和人际空间里种种现实/话语结构的冲突。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影片把世界展示在道德的模棱两可中,把严肃的思考融入“带泪的笑”中。
“黑色幽默”的核心内涵是荒诞。“荒诞”是一种让人认为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的心理感觉,即运用夸张到了荒谬程度的幽默、嘲讽等手法,通过扭曲现象揭示现实世界的本质。荒诞之中蕴涵着生活的必然和内在的真实,荒诞的历史积淀和现实生存导致了黑色的建构。黄建新影片的幽默就得益于片中事件、人物及其行为的荒诞感。他用一个荒谬的事件作为故事的核心,故意把不可预料、不可并置的东西放在一起,建立起联系,并使之生活逻辑化、细节化,让人笑到无言,品出苦涩。比如《黑炮事件》一枚棋子导致几百万的国家损失;《错位》里机器人迅速地学会并堕落为—个腐败的官僚;《埋伏》两个人在塔上守着,却被人遗忘了,但最后,两个最没用的人起了关键的作用,让罪犯落网:《谁说我不在乎》里妻子疯狂寻找结婚证,《求求你,表扬我》救了人的男人四处求表扬……每—部电影故事的核心都是生活中某个荒诞性的一面,对生活荒诞的感觉始终是他的—个原色。
实际上,荒诞的故事只是黄建新电影的外壳,他以深刻的荒谬感发现了现实人生的种种怪圈和悖论,但更为关注的是这些荒诞的故事中所包容的社会症候,黄建新曾说:“文化的根就在现在,就在每个人身上……可能就表现在非常琐碎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他的思考永远联系着活生生的现实,以写实的笔墨去揭示生活的荒谬、社会的阴暗、理性的困窘。通过对看似平常又使人感到离奇甚至荒诞的事件的描述,将一种批判的思考定位在现实表象包裹的深层文化结构上,于荒诞、偶然中透出了真实和必然,使得电影中动态的现实和深沉的文化思考之间水乳交融。
二、对文化符号的运用和拼贴
黄建新的作品通常凝聚着深刻凝重的理性思考,深刻地表现了导演对现代社会的道德操守、精神追求上的思考。但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他的影片逐渐脱离“新写实”的轨道,极为新潮地使用了很多颇有后现代意味的电影手法,纯视觉娱乐化、感官化的画面越来越多,尤其引人瞩目的是运用了许多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如前卫装束、流行歌曲、电子游戏、时尚轻巧的动漫卡通等,应该说是從中国自身都市文化中孕育出来的,是中国特定的商业性文化符号,同时又影射了一些在当代社会得到默认(如感情联络费)或处于禁忌(如同性恋)的道德问题。真实存在物逐渐被大量复制的形象与符号取而代之,现实生活的“原本”变得不再重要,因为人们面对事物的指事物可以做出同样的反应。于是复制产生的无数摹本导致了原作“光晕”的消失。
《谁说我不在乎》构图精致讲究,充满了形式美,并运用了诸如动画卡通、想象性场景、DV效果、不确定性的对置等的后现代手法,表现出对感性视觉奇观的重视。毫无疑问,原有的理性深度与时间焦虑消散了,轻化了,呈现出了一种从社会政治文化反思到视觉消费的文化转向。
后现代理论家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目前最显著的特点或手法之一便是拼贴。它以片断拼贴和意象零散化对抗现代主义作品对艺术形式的执著追求。“拼贴式”叙事有时可以把几个缺乏内在联系的“叙事碎片”放在一起;也可以打破各种文类的界限,叙事在文学、广告、科学、新闻等文本间穿插进行,其目的既是表现叙事对象(人及其面对的世界)的
虚幻性,也表现了叙事主体对语言的真实性的质疑与否定。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塞尔姆特别崇尚拼贴式叙事手法,他说“碎片”是他惟一信赖的形象。这样,艺术创作最终成为利用各种现成的互不关联的“形象碎片”的即兴拼贴。
黄建新在作品中进行拼贴,影片往往是在正常的叙事过程中,突然插入动漫镜头,在叙事镜头与动漫镜头之间形成新异的组合形态。这使得故事的参与性和亲历性突然间中断,插入了旁观和反省因素。《谁说我不在乎》本是探讨女性心理和家庭关系问题的,却以孩子的视点介入,其中穿插了大量的拼贴、动画,与现实时空的组接,对生活进行独具匠心的艺术“戏仿”。片中有类似游戏大拼盘的电影场景,耳熟能详的广告语汇,女孩对母亲说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作独身女人挺好”,这些其实都是广告词。还在片中模拟像《杀手里昂》等经典影片的镜头……这些充满形式感的影像元素组合,都恰恰和观众收视心理吻合,在技术手段和风格上实现了突破和超越,形式上更加接近典型的西方后现代电影特征。
三、解构精神的阐扬
著名理论家德里达认为解构是揭示问题,并将其不合理之处加以分裂瓦解,即是说解构就是将任何形而上学哲学观念加以问题化、分裂化、反稳定化、将其“置于抹拭之下”,加以质疑。当今全球化语境中,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思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自然渗透,为中国文化与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言说提供了某种契机。解构思想也在中国文化运动中得到回应,它主要是在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上立论。可见,后现代主义言说无疑为中国式的文化解构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话语资源。
黄建新在这些文化思潮的激发下,有限度地接纳和吸收了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精神,对“理性”政治进行了一次很有历史意义的解构性批判,只是这一批判更具文化色彩。
第一部作品《黑炮事件》的片头段落,行色仓皇的赵书信,令人生疑的电文,营业员警觉的眼睛,警车疾驰而来,公安人员勘测现场,无疑是对十七年经典侦破片,反特片模式的滑稽模仿。而后,在影片的展开过程中却将片头所谓“特务”活动——黑炮事件的蛛丝马迹,还原为一个棋迷与棋友间极为个人的、寻常的接触与联系,于是,大陆十七年侦破片的话语型态及其语境便在其戏仿之中被解构。而黑炮事件的结果,因为这颗所谓可疑的棋子,由西方引进的WD--工程毁于一旦,国家巨额投资付之东流。
典型的后现代风格在叙事流程中对传统加以解构,正面与负面的效应在这里进行了戏剧化的交锋。《埋伏》的主人公叶民主在身体与精神面临崩溃之际,从一个电话里传来无数鼓舞人心的话语,这些话语给身处绝境的叶民主以无穷的力量。看到这里,我们都以为,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德示范的力量,是中国的红色宝典。然而,接下去的情节却告诉我们,神秘、智慧的“电话者”其实是个神志不清、不辨人事的聋者,只能靠电话上的那个红色信号灯来感知外界,至于他讲出来的一串串“壮志豪言”,也完全是非理性的痴人呓语—一这是对传统的信服和膜拜,又是对传统的反讽与解构。
黄建新对情节和意义进行解构与颠覆,使得道德的复杂性、悖反性也因此毕现无疑。《求求你,表扬我》整部影片都是围绕着要求得表扬这一事件,一方面让观众感觉到“英雄”的存在与纯粹,另一方面还暗地里埋伏了不少的细节,来瓦解这种高不可攀的“精神”的崇高。当杨红旗真正得到了表扬,杨父却传来死讯,在杨父灵堂前,村长的一缕微笑、崭新的奖状、粗大的红烛等,都预示着杨父之死是一个虚假的设置。这种细节设置具有先天的后现代解构与黑色幽默的味道。这个表扬除了伤害了欧阳花之外已经再没有任何意义。
黄建新不断进行形式拆解和意义拆解的尝试,一方面对具有强大意识形态特征的宏大叙事的疏离,针对的是政治权力文化对其他文化场域的霸权地位,以此消解政治权力话语,另一方面也消解了新时期以来建立在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启蒙与人学主题。正是黄建新的这些后现代的尝试和对解构精神的阐扬使我们有了更加广阔的思索余地。
四、结语
黄建新的电影曾以其特定的人文视点和造型语言,呈现给观众种种令人惊异的电影图景。当后现代主义介入其电影实践的具体操作过程时,他虽仍然注重戏剧性情节的构思与悬念的设置,但又彻底地抛弃了“讲故事”的老套;他“分切”情节,给予重新“组接”,纳入心理时空运动的轨道,又使用暗示、烘托、对比、象征等手法,形成辐射与交叉相结合的网状结构,既深化了精神内涵,又强化了在‘反叛基础上‘复归交叉的艺术特色,从而分离并显现出后现代主义特征。
当然,黄建新虽然运用了许多充满后现代色彩的表现手法,但其内涵想表达的那种对社会流弊、传统文化和当代情感变动的反思与内省则是非常现实的。“形式不仅仅是形式”,正如黄建新访谈中提到的“十幾年来,我的电影实际上是用我的心记录了我对中国社会变化的感知从激烈、激动、激情,到平和,到想象的过程。如果我做的事情还有一点价值的话,就是可以从我的电影里找到我对中国社会变化的一点一点的感受。”“对电影的形式感的捕捉,对电影外部形式的运用,取决于当时不同的社会感和心态。”影片以此为出发点,游走于新写实、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也就使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对一个故事的讲述,对一种创作意识和创作方法的实践。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谁说我不在乎》到《求求你,表扬我》,黄建新电影中的后现代因素越来越明显。他用一个貌似游戏的叙述框架展开他的后现代文本,常常具有游戏/寓言的双重性。一方面表现出影片作者对现实世界偶然性的洞悉,同时隐匿创作主体,又使影片力图消解主题与意义,留下了极其鲜明的后现代印记,从而明显地成为“黄建新电影”的标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