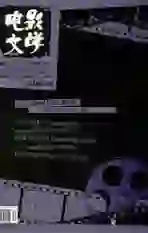《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文化叙事学阐析
2009-04-15贺萍
贺 萍
[摘要]《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真挚感人的情感、高超的拍摄技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本片叙事上的策略变化,探析文化误读和遮蔽的现象,试图分析这种现象的内在生成原因,揭示文化主动建构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文化误读;叙事策略;文化建构
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下简称为《贫民窟》)挟奥斯卡八大奖项之威,如激流劲浪汹涌恣肆,在全球掀起或大或小的波澜,冲撞着异国的敏感文化神经,冲刷出一道道思想的隔阂和烙印。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印度,在面对电影《贫民窟》热潮的汹涌来袭,官方及民众的不同反应及具体的应对措施;以及结合欧美国家和印度本国的具体文化情势,与原著小说相比电影的文化叙事策略有何转变,来分析、厘清文化的误读、遮蔽与存真,来解读文化间的碰撞、角力乃至交流与互融。
一、电影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印度吗
——文化的误读与遮蔽
影片从一开始,导演丹尼·博伊尔就用娴熟的二元交叉叙事结构、迅疾的影像剪辑及手提摄像机的跟拍式手法支撑起一幅动感十足的社会画卷,呈现出印度最底层的人民艰苦、贫瘠的生活居住场景;与此同时,粗糙的生活环境孕育着鲜活的力量,它生气勃勃,如同刚出笼的馒头热气腾腾。
这是印度的真实呈现吗?
影片中描绘的贫民区即是孟买的达拉维区——亚洲最大的贫民区。孟买是印度极繁华的大都市,宝莱坞和国家金融中心均设于此,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紧邻孟买的黄金地段,却仍存在着一个贫民区域。贫民区里有无数所简陋矮小的房子,触目惊心的垃圾山,甚至连河道内亦飘满了垃圾。在这里,充分展示了生活的复杂诡谲,富庶和贫瘠并存,文明与野蛮共生。
电影中与之相呼应的一个细节是,当阿米达·巴彻——印度著名的动作巨星——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贫民区时,杰玛却被哥哥舍利姆困在简易厕所里。只为了想得到一个签名,他决然地跳下粪坑。杰玛浑身污秽却高举着照片,以防止弄脏。他兴奋地冲向偶像,神奇的是,他获得了签名。诚如导演丹尼-博伊尔所言“……这一段实在太棒了。它将贫民窟的污秽,对阿米达的崇拜,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那就是孟买,它有点像这座城市矛盾的味道:前一分钟你还闻到粪便的臭味,而下一分钟,你却闻到了藏红花或茉莉的芬芳。”…导演在处理这一个场景时,镜头没有出现阿米达·巴彻的正面形象,有的只是一个高大、无言的背影,甚至背影也不算。这时候的阿米达-巴彻实际上成了一个抽象的象征符号,象征着上层社会的高高在上、高不可攀,近距离的接触只能暗证彼此之间的巨大的差异和疏离,这和上述导演的感受可相佐证。
我们认为,电影《贫民窟》既显示又没有显示一个真实的印度面貌。一方面,达拉维区确实是印度最落后的一块区域,在真实生活中,“一天晚上,我们听说阿扎(小舍利姆的扮演者)的房子被推翻了。他住在贫民窟,有时候理事会的人会去恐吓他们。我们派人到处找他,后来发现他睡在一辆车的车顶上。”-,-影片中贫民区大量生活细节的展示,生活中的更加令人酸楚的真实事件,无时不在提醒印度真实、脆弱的一面,现实世界充满着悬殊的贫富差距,充满了宗教和种族上的尖锐冲突,也充满了青春的迷茫和成长之痛。然而,影片中的大量跳跃、动感的画面呈现的是一种浪漫化了的贫民区生活状态,这些细节的展示无意中成了叙事的佐料,它使得影片更加细腻和客观,但同时它并不影响整部电影的叙事主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出现了某种偏移。影片的故事在愈来愈倾向于娱乐化以及愈来愈明显的励志主题倾移下,文化有意与无意间被误读了。文化和生活的真实被遮蔽。出现这样的结果,主要得力于电影独到的文化叙事策略。
二、电影《贫民窟》的文化叙事策略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述《贫民窟》的故事情节,即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金钱和爱情的双重丰收。就故事情节而言,它根本谈不上什么新意。关键就在于影片的文化叙事策略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电影开篇部分颇有史诗电影的气质,然而,当杰玛和舍利姆成功逃离黑帮,顺利爬上火车后,电影的叙事基调开始产生了变化。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体现在音乐上。我们注意到,当两兄弟由于在私人机场玩球而受到警察追逐的时候,这时音乐是磅礴的,伴着有节奏的鼓点,音乐流畅、悠扬,恰好和展示贫瘠而又充满活力的贫民区的画面相谐;当贫民区因为宗教和种族的冲突发生暴乱,母亲被杀害,两兄弟逃亡的时候,这时的音乐较为低沉,透露着紧张不安的气息;但是到了两兄弟在火车上叫卖的时候,音乐则转向了柔和、欢快。于是,叙事转向了浪漫主义叙事模式。而当两兄弟摔下火车而毫发无损,且奇迹般地达到了印度圣地——泰姬陵的时候,故事的重心已经完成了转移,剩下的就是表现杰玛怎样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中闯关成功,以及最终获得爱情。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将一个有潜质成为史诗的故事改编(拍)成一个普通的个人获得金钱和爱情的成功故事?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问题,我们不妨先将问题做一个转换,即先探讨电影内容和小说文本的主要差别体现在哪里?主要区别有三:
1弱化宗教、种族冲突。这从主人公的名字改动上就可见一斑。名字的改动令作者维卡斯·斯瓦卢普心有不平,“令我感到遗憾的是,电影将主人公的名字从拉姆·穆罕莫德·托马斯改成了杰玛·马立克。”由此我们知道,在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必有作者的深意。粗谙印度文化和历史的人,看到拉姆·穆罕莫德·托马斯这个名字的时候,可立刻明了其中所蕴含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元素。原作者的用意显然是希冀主人公能够超越狭隘的宗教与地域界限,成为印度人的代表,而不是单单代表一支宗教、一个种族,这寄予了作者对印度本土多元文化融合的美好愿望。然而在影片中,主人公的名字却被改成了杰玛·马立克,一个普通的名字。美好的愿望被消解了。或者可以说,影片根本就无意致力该方面的表达,起个简洁的名字,让观众更关注故事本身,才是影片改名字的真实意图。
2弱化苦难、冲淡人文情怀和理想。影片摒弃了小说中许多印度底层人的打拼和希望破灭的故事。“(小说中)底层的人,怎么样梦想自己将来会怎么样,突然又戏剧性的全部失去,这些东西不光是对孟买人、印度人、全世界的底层的人心理是一样的。这也是小说能引起很多共鸣的原因。”而这个共鸣的因素在电影中就彻底清除了,这正如影片最后的那一长段欢快的印度式的歌舞,以狂欢替代苦难,以娱乐消解沉重。
3与此相对应的是,爱情线索的强化。这是最大的一处改动。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并不存在于原作中,在小说中,杰玛遇见了形形色色的女子,最终爱上了一个妓女。爱情在小说中着墨并不多。而在电影中,爱情故事得到了强化。个人的故事比公共历史显得重要和迷人得多。对电影而言,这是一个极其讨巧的叙事策略。
至此,通过对影片和小说主要差异的分析,我们认为。
这部电影的叙事核心就是:去史诗化、去神圣化、去苦难化;庸俗化、娱乐化、狂欢化。这是影片叙事策略选择发生转移的内在原因。影片不是让你去接受、感触印度文化,而是让你在潜移默化中追求普世的幸福观和价值观,进而认同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本片无意也无力刻画沉重的苦难、野蛮和暴力浇灌的鲜血和泪水、底层民众的坚韧和生生不息。电影大众化了,它冲淡了人文情怀和理想,它远离了严肃的艺术精神探讨,但是它赢得了票房,获得了奥斯卡,满足了全球观众的猎奇心理和白日梦心态。
三、文化建构——在遮蔽中主动显现自身
格奥尔格·里朴斯梯兹说:“时间、历史和记忆在媒体充斥的世界成为质上不同的概念,电影和电视的消费者不再通过对共同的地点或祖先与过去联系,而是与他们从未见面的人们拥有共同的遗产;他们可以获得与自己没有地理或血缘联系的过去的记忆。”
从这个角度来看,《贫民窟》不仅想象性地重塑了印度这一国度的民俗、风情、经济和社会政治,同时也间接地重塑了他国对印度的集体记忆。在这里,印度的真实自我被遮蔽了,印度民众的粗砾、苦难但充满了生机勃勃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或者被浪漫化、理想化了,它成了手段、工具,表现它不是关注它本身,它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一个所指和能指出现游离的意念化合物,个体的痛苦感和幸福感被无限放大了,主人公作为游戏的胜出者受到了狂热的追捧,主人公个人的神奇般的境遇为无数的普通人找到了属于他们本身的那一个“自我”,个人的游戏遂演变成了集体大众的共同狂欢。
西方的文化叙事策略由来有之。上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即创立了所谓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当国人仍在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作无休止的争执时,西方的文化研究已经由理论的探讨、梳理转向对现实的干涉和介入,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这方面最显著的是对商业媒体和大众文化的研究,而焦点就在于好莱坞的经典叙事策略。
这给予了我们一个警醒,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明确无误的理念和实践,事实上是由“他者”来建构起来的,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西方的文明和文化价值观念——事实上,当我们在观影的时候。字幕显示的是中文和英文,英文是全球通用的;即使是作者本人在描述主人公的时候,用的也是中文和英文,印度本土文字消失了。说到底,底层民众还是不能够把握自身。他们不可能掌握真正的话语权来表达自我,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和精英阶层化被动为主动,致力于确证自身、显现自身独特的文化内蕴。
印度民众对电影《贫民窟》有节制的不满,和当年《卧虎藏龙》公映之后中国民众的批评态度何其相似。有人认为中西方的文化误读现象根源主要在于文化上的差异。作者本人并不赞同,至少可以说此种说法不全面。文化误读更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叙事策略选择,是为了文化价值观念的输出和覆盖,但被误读方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恰恰相反,文化误读,与其说是一个破坏性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建构性的机遇和过程。利用“文化误读”的契机。可以借机展示自己的独特文化价值和文化内涵。
一个容易让人忽略的事实是,当影片获得奥斯卡八项大奖后,印度舆论对影片批评的声音忽然间消失了,对两名印度人获奥斯卡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印度总理也适时发表言论,充分肯定了两人取得的成就,这其中也包括对电影本身的正面性评价。应该说,这是一个积极地向世界展示自身的信号,印度总理的言行不仅可以吸引世界的目光,而且可以借助文化上的效应来带动经济、政治的交流;与此同时,这也无形中增加了民众的凝聚力和面对新生活的信心。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真实的文化、真实的自我正在主动地显现其自身。
这正是一个主动文化建构和祛蔽存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