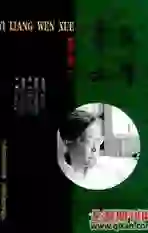侯马的诗
2009-03-30侯马
侯 马
侯 马1967年12月生于山西,1985年至1989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至199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律硕士学位。出版诗集有《哀歌.金别针》、《顺便吻一下》、《精神病院的花园》、《他手记》。曾获“十月”新锐人物奖、“诗参考”十年作品奖、2007年度汉诗榜最佳诗人,2007年度《诗选刊》中国先锋诗歌奖,2008年《人民文学》、《南方文坛》年度青年作家奖。曾参加“盘峰诗会”、“青春诗会”。现工作于北京。
那只公鸡
到今天我还能想起你
高傲 勇敢 从容 浴着血
踩着贵族的步伐
用浓缩的太阳做眼
一会儿用左耳
一会儿用右耳
谛听
打麦场是你的天下
整个村庄是你的天下
你君临的范围
是像梦一样隔绝的另一个区域
我只能是过客 漂泊者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五日
你故意走过庭园
渲染我七岁的孤独
无边无际
一只公鸡 生活在黄土高原
是许多公鸡的对手
众多的母鸡 爱着他
一个漂亮的超低空滑翔动作
使你的情人感受力之美 重量之温柔
用强奸的行为
满足伊的羞耻心和淫荡
没有过去没有回忆 充满定格
生来就是一只充血的鼎盛的生命
荣誉涨红了鸡冠 耸起
漫不经心地引吭高歌
冥冥之中和朝霞夕阳合拍
从从容容 自自在在
过着爱情的 闲散的 死亡的生活
你神秘地消失的那天
三股叉般的脚印
印遍了残墙颓垣
距离
他与她曾经同室相识
同桌就餐
同床共眠
只觉得熟
常记不清模样
有一年
坐长途汽车
两个前后分离的座位
拆开了他俩
他偶然回头
看到她抬头
新修的眉毛
白月般的面庞
就像一个陌生人
被他牢牢记住
望长安
——给伊沙
蓝衫人在一个夏天来到长安
正巧赶上了落日
蓝衫人出现在一棵云杉之下
他呼吸着 眺望着 辨认着
在城市的面前眯缝着双眼
市民在城墙的阴影里行走
城楼放飞着惊悸的鸟儿
而蓝衫人 伤心的人儿
落魄的人儿
他用风尘的笔写道
‘我必须忍受我的孤独,
像远山必须忍受着长安
口头禅
——致徐江
咋也不咋 他有决心
把这句话带入国际政治
中年婚姻 以及到处
寻找源泉的诗歌技艺
典型的北方话
可以看出他背后有人:
他的乡村祖先们
他同种同文同样颧骨的汉子
失败 抗争 妥协
徒劳 生死 爱恨
突然被无可奈何又
满不在乎的春阳照耀
一枚充当戒指的顶针
一碗冒充可乐的草药
他真正想说的是
除死无大事 可是
还有一种乡音说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这就没办法了? 只能是 咋也不咋
二十年前 他的密友
就意识到了他这种
可笑又可怕的说法
吸血迷情
“我告别人类的那晚月色之美
“令我哭。在东方,人也称我鬼
“我的身体要多腐烂有多腐烂
“但我也可以艳若桃花
“栩栩如生,长久保持
“离世时俊朗的容颜
“我不是死给你看的,也不想
“给自己看,我力图有一个结束
“却开始了永恒。我丧失了
“变化的权利,永远不老,死到不能
“再死。动与静皆类似真实的迷幻
“我的躯体,这无法收获的果实
“难以像番茄那样在咀嚼中消失
“生前它属于我,严格意义的遗产
“难以被继承,也难以被抛弃
“就这样,我从台阶上滑倒
“一下跌落了200年,先是被称为
“农业的僵尸,随即被称为工业僵尸
“最初是我拒绝了人类,如今不知
“该再生还是死去。我时而蹑足临世
“鬼气森森,时而销声匿迹影踪皆无
“继续着沉落,风采依旧
“风干而不朽。一个没有同类的僵尸
“独自承受着作为僵尸的孤独”
李红的吻
她几乎不露痕迹地藏起了河南口音
她几乎不费气力地套上了紧身旗袍
少女时四年的短跑生涯
留给她苗条的身段以及
不太灵光的头脑
真的,她从不沾酒
人家逼狠了,就起身逃掉
她说要是有人喜欢她
大概是觉得她性格好吧
每次开口,她红唇下的牙暴露无遗
关于童年,她记恨童年
三姐妹比肩生长
对一个只生姑娘的家庭
奶奶抱着族长般的冷落
在轻蔑中,她暗怀敌意
呀,目睹这现代一幕的变迁
有人顾不得顾影自怜
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
才能被称作男子汉
一个婊子要生多少娃
才能有人喊她一声妈
李红的旗袍裹着她的躯体
李红的智力含着她的美德
只有在酒吧旋转着挂在天空时
才能看到逃离的李红努努嘴好像一个吻
种猪走在乡间路上
阳光
这一杯淡糖水
洒在冬日的原野
种猪走在乡间的路上
它去另一个村庄
忙
种猪远近闻名
子孙遍布三乡
这乡间古老的职业
光荣属于种猪
羞辱属于种猪
而养猪人
爱看戏的汉子
腰里吊着钱袋
紧跟种猪的步伐
自认为和种猪有着默契
他把鞭子掖在身后
在得钱的时候
养猪人也得到了别的
一个人永难真正懂得
种猪的生活
养猪人又是欢喜
又是惶恐疑虑
这时一辆卡车
爬过乡间土路
种猪在它的油箱上
顺便吻了一下
卖塑料花的农夫
呵,农夫
清凉的四月
你把花儿驮到
殡葬馆门口
这些翠绿的花儿呀
有整整一麻袋
沿马路摆开
它的原料是可乐瓶子
花儿,比弃尸纯洁
比灵魂颜色深
呵,农夫
沉默的黑农夫
你的塑料花积压了春天
在南部升起一面六色旗
在北方摔落一架747
而在我祖国的乡下作坊
剪呀,绞呀,编呀,粘呀
塑料花茁壮生长
你的亡妻她操劳、奔忙
披着羊皮?的狼?
九三年
我在前门当警察
有一晚所里查获了一名卖淫女
因为要等女民警来问话
就先让她站在院里
她有一双骨碌碌的大眼睛
还有一付瘦削的身材
在秋风中紧抱着双臂
说她有点冷
让民警给件衣服穿
这儿可没人愿意搭理她
所长托辞没有女式衣服
她就哀求道:让我披件警服也可以
就警服吧
这个女人真是敢张嘴
这怎么可以呢
诸位想想
一个妓女,披着警服?
每次想起这事
我都不知该怎样使用
那个古老的比喻
红糖
我在杂货店里
总能最先嗅出红糖
少妇的体香
一种哺乳的味道
我了解生育的庄严
也深知其中包含危险
红糖来到北方
那么粗心
赤褐色的躯体
要由一块麻纸裹起
很快地
它像一碗草药散发着热气
一只酸软的手尝试着端起
在北方
青纱帐还沾着生产的血迹
在南方
甘蔗林已节节甜透
吃杏的姑娘
杏树在杏树园里
吃杏的姑娘
比杏花来的晚,比成熟的杏
来的要早一些
这又是使人心惊的一个下午
一枚青涩的杏,取代了一首诗
立在那里,取代了一个
在别的场景可能发生的故事
她端详杏,就像她端详夏
夏回望着她,她高举左手
环步杏园,她说:
“谁能把这枚杏顺原路送回枝头”
说着她把杏送到唇边
吃杏的姑娘来过以后
整个夏天弥散着苦杏仁的味道
一束花
亲爱的妈妈呀
为什么不把你的儿子
生成一束花
一束花的痛苦
一束花的茫然
在清凉的早晨
假如你把我生成一束花
妈妈
我就可以用一把生锈的剪刀
剪断了我的腰
剪断了我的颈
浸透了自己的泪水
眨眼间
消失了我的美艳
可是我的妈妈呀
我问自己
为什么你不把儿子
生成他渴望的一束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