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意象空间浅谈
2009-03-22田黎明
田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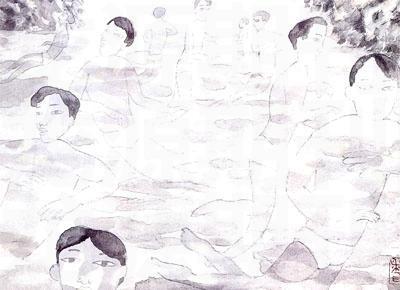

一、印映合一的文化体验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遵循的是一种自然文化模式,即把自己生活,思考之中所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困惑放到自然文化中思考,宋代理学家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我们的先人将自己看成是自然中的一体,以儒道释文化为基础理念。进行自我梳理、自省与体验。而这种体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则行合一”的方式来实现的。“知”与“行”强调的是“真知”与“必能行”的文化体验,注重人生经历、知识结构与心体、自然的圆融,所以中国文化有一种注重宇宙整体性体验的自觉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知”和“行”与中国画中所提倡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规律是相通的。而作用的主体,是我们认识事物、超越事物表象的体认方法,进而衍生出“天人合一”、由技进道、由道解物的文化理念。如,先人总结出五行——金、木、水、火、土,是对我们日常所见物的概括;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人类日常行为的方式。由此,天与人、知与行是可以用“印映”方式来体会的。
中国禅语中有“一月印一切水,一切水映一月”,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方式,强调用“映”与“印”的方法来把握传统文化对自然、对社会、对自我的超越和“进境”的方式。“印”是自然的本体,“映”是主观的本体,印和映的关系涉及到一种意象,其中意象的内涵便是“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如果说“真知”是印,那么“必能行”就是映,这可使我们从体验中来理解王阳明先生“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的内涵。什么样的意象才能产生“映”和“印”之间的贯通?老子所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就是这样一种理念。若把月作为大文化,水为万物的象征。这在中国文化里强调的便是气象。月作为一种气象,一种品格,水作为主体融入其中,才有自己的方位。中国画特别注重气象与意象,两者皆可产生境界。因此,体验“气象”与“意象”,其实就是体验境界的问题。那么,在境界中如何来呈现意象呢?慧源法师提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可以理解为“道”,可以很具体;以“道”来把握万物,必须要有内在规律。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画里必须通过观察和自己的体验来加强对文化认知和把握的深度。古人所谈到的“一”都是经过先人的体验,我们今天也应该通过这样的方式体验它的内在精神。
汉代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即是说中国人面对事物的时候要讲究行为,讲究道理,追寻道而不问其功——这是很重要的中国文化内涵,能够使人的心境透彻。所以说,“明道”是“一即一切”的源头。唐太宗李世民极爱书法,特别崇尚王羲之书迹,朝野上下,均以太宗意趣为准,崇王之风极盛一时。他在《论书》中说:“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这几句话对中国画的学习,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学习古人书法不只看古人的风格和特点,更重要的是基础。这种基础对于中国画来讲首先便是“作意”。“作意”是立品和取象,而“形势”指的是一种语言、画法、笔法、中国书画在这里对于中国文化的把握,首先是从意境上取象、立格、这对于追究怎么写,怎么画来说奠定了基础。
传统“六书”大约反映了战国末期到汉代人们对汉字结构和使用情况的认识,是古人分析汉字结构和使用汉字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其中,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属于造字之法,即汉字结构的条例;转注、假借则属用字之法。特别是其中的象形、会意。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方式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象形字“雨”和“月”,基本上是直观的一种字的形态。“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强调的是观物成形。会意则是用两个或几个物体的图形组合起来,拼合出字义。这种方法可以把一些无法直接描画的事,动作、状态表示出来。比如,三人成“众”,“北”是两人相背,物象相融而谦让等。以象形、会意作为一种观察疗法,在古人意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东汉蔡希综在《笔论》中云:“凡欲结构字体,未可虚发,皆须象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若云若雾,纵横有托,运用合度,可谓之书。”这里讲的便是古人在写字时一定要有一个“作意”在先,即意蒙思维。由此我们可以引出古人关于竹子的画法,“一笔片羽、二笔飞燕,四笔惊鸭”都是从生活中直接观察并归纳出来的。这个方法首先要取象,要目击象存;其次便是意合。看到这样的“作意在先”,对我们来理解传统绘画和自己在生活中如何把握意象是至关重要的。以此类推,由画竹方法再引申出书法中的永字八法。永宁八法主要是八种力和八种意象空间的体验。永字八法之力是借意象空间形成力的方位、归属,并由此以技进道,以具体笔力形成笔法,又形成笔意进而上升为一种气韵,所以谢赫六法第一句便是“气韵生动”。通过对传统文化强调的意象方式去体验用什么样的力把这个结构整合起来,对中国画创作非常有启发。
周汝昌先生在《永字八法》一书中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八法的意象方式。譬如,侧(点如侧,如鸟之翻然侧下),古人用高峰坠石来发力和找形,下笔时强调欲下先上,欲进先退;而策提(仰横、如鞭策、策马疾行),啄(出静而动,强调的是腾凌而速进,如鸟之啄物),这些既是一种形态,也是一种意象之力。所以永字八法强调的意象,每一种力都是意象引出,而这些方法又形成了中国画的方法。这虽是书法的技法,实际上也是中国画的技法,解决了中国画的造型理念。
在书法中,先辈们千变万化都离不开“体”。这个“体”可归结为一种心体。我们看书法心体对中国画的影响,可以借“法”来体验中国画的造型法则、用笔法则和气韵法则。其中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展开对这些字的体验,如果去体验,又是如何在发力当中体现。任何一种笔法都内含中庸的法则,向内是立道,向外是取象。所以通过对书法发力和结构的认识,可以概括出有关中国画创作的一些结构方法,而这些结构方法,首先强调的都是意象。宋代《梅谱》总结出一些程式化的经验,我们通过这种经验来理解中国画的特点及其与西方文化在生命体验、文化取向等方面的不同。西方人本意识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反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意识则是人与自然圆融的结果。所以中国文化是自然的本色,是对真、善、美的文化体验。我们的先人在生活体验中,总结出冲突。实境、自然、雄浑之气象,这也是我们在当代中国画创作中所要学的。
宋人的梅图有很多图式,而每一幅图式都有一种境界。如《遥山抹云》,这幅图画的虽是梅花,但是在空间的选择上,梅花俨然化为一朵白云围绕山体;义如《燕尾》,花的造型不仅是宏观的还有微观的,并通过描绘角度的不同形成各种意象。又如“雄浑之象”,“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刘邦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作为对其体验的再现,此时的大风、海内、猛士、四方,意在雄浑中产生合谐之势。而关于“冲淡”,“犹之惠风,荏苒在衣”,使我想起
陶潜《归去来辞》中的“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之句,实是陶公放下形役而内心真正领悟到本然的生命意义,产生了一种“风飘飘而吹衣”之感。而“实境”则“忽逢幽人,如见道心”,也使我记起来自清的荷塘“朗照”,这是朱自清先生心底的光明和中国文人骨气借助荷塘产生的文化沉郁之美,令人感慨万千。此刻,我感到在他们身上的中华文他温柔敦厚之美,看到他们印映出中国文他的大气象,体会到真、善、美的载道方式和生命承载的意象空间,体会先人的经典作品时,是以生命的体峻来参与,此时,古人发现了这样的造型,并为这样的造型确定了立品,取象。像宋人《梅辔》中野鹘翻身、蜻蜒欲立等,既是以微观之式来取象。也是对空间的心降所注,这自然天成之境。所以古人在取象方面解决了如何在自然中把文化的观照变成了物的载体,实现了印映合一的理念,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少的文化体验。
二、“格”与“象”的自然精神
对于中国画意象方面的思考,更多可借助于古典诗词加以理解。如秋风,古人写了很多有关自己对秋风感悟的诗与词。秋风原是一种自然的形态。秋风可以引申出素风、凄风、高风、凉风、激风、悲风、劲风等各种不同的文化的深层体验。而这些关于风的体验,实是关于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体验。如描写秋景的诗句中,有朗景、澄景、清景;草木里有衰草、疏木、衰林等,强调的都是主体的一种体验。
隋炀帝在《悲秋诗》中云:“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复来。露浓山气冷,风急蝉声哀。”扬师道《韧秋认错坐应诏诗》:
“雁声风处断,树影月中寒。爽气长空净,高吟觉思宽。”秋高气爽而有悲凉之意,这种悲凉通过对自然空间的描述,把自然空间景象转换成心象,并通过意象的方式解决了时间、空间与自然同生而随人性之生。再如凄风,庾信《晚秋诗》:“日气斜还冷,云峰晚更霾。可怜数行雁,点点远空排。”所描绘的景色是作者心底对自然的点化和浓缩,靠意象的方法来实现的一种经历与精神转换。又,庄子云:“大块噫气,其名同风。”云气飘浮,变幻无定,是天地间生生之气的显现,庄子以自然宇宙之躯来呼吸,感人至深。
关于劲风,乃人格之立,前面刘邦《大风歌》中所指便是劲风。“江海”和“四方”进入到精神本源成为刘邦胸襟和立格的写照。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通过秋风的变化,栖志人格所向。中国人对字意的理解,以精神之志超越自然之物,又返回自然空间深化自己的心性。燕太子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种悲风不仅道出了壮士的坚韧,也更能让人体会到悲风中所蕴藏的文化精神。可以看出传统书体强调的取象结构和风格结构,实际上是靠意象方式和立格决定的。每个人对自然、生活的体验方式之不同,产生了自己独到而坚定的立格方法和自己所理解的自然空间。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人物画中所传承下来的“吴带当风,曹衣出水”似的绘画样式,不仅是中国画线描的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审美空间,一种自然形态所印映出的文化空间。“吴带当风,曹衣出水”与永字八法同为一体,无论是其中的风体,还是水体最终都是意象或立格的载体。所以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积淀,由意象思维和表象方式所产生的程式语境,对今天的中国画创作有重要启示。
我们看过霍去病陵墓的雕塑,它们的精神载体与《大风歌》《秋风辞》也是一体的。因为这种大气磅礴的精神强调的是写意、写胸怀、写境界、写气象,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结构。所以自然之格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独特品性,是,种非常重要的载体,我们要通过“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印映合一”的体验方式和人文境界,以温柔敦厚的心体来把握。
关于“象”与“格”,可通过一些诗句来体会,进而使人意识到中国画的笔墨亦同诗一般,也可以定格在某…层面中来把握人之经历的不同。譬如,画一张平远山水,我们可以从中国绘画史上找出很多关于平远山水的作品参考、借鉴,通过观照将其定格在文化精神的体验中,以体验古人风范来把握画格。董源、倪云林、黄公望等人的平远山水,由于各自人生经历、阅历等方面的不同使他们关照对象时所产生的感受也不尽相同,这源于其画内所合有的深厚的文化理念和个人体验,所以董源进入了平淡天真的境界,黄公望进入了平常寂静的境界,而倪云林则进入了平常空间之境。他们借助身世,将心底对社会、自然,传统的体验方式,在追求品格之时,通过笔墨载体,反映出对文化的体认。对特神的观照、对自然的品逸,借自然之格赋之人格。
又如,东晋陶渊明的诗和唐代王维的诗,都有一种返璞归真之境。且寄乐于平常心、平常景。当然,这里的平景景已不是我们日常所看到的景,而是已经具有文化象征的“平常景”;同样的,平常心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平平常常的心态,而是进入到一种境界的空间里的“平常心”。所以陶渊明和王维所看见的平常景、平常心,已是一种心境的体现。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特别是后两句话便是一个追寻本源的思维方式。他借期望笼里的鸟返林,与树林中的鸟合一;池塘里的鱼回归,与江海的鱼合一,来寄托自己内心所向这是他的一种人格意识,强调的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方法——放下所有回到自然,体现出人的自然境界。而唐王维的诗《阙题二首·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则印映出天寒湿润的空间感。只有不受时代的限制,借助文化空间与人性、心性空间和自然空间来体会“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文化理念,我们再去体会诗句中的平常心和平常景才更有意义。
王维的许多诗以“空”的概念把自己的理想境界写出来、他用特有的平常景语概括出这种交化的空间,一直持续了千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种空的感觉已经不针对物质,而是对心性的生发,他可以在某山某水的任一空间都生发这种感觉,找到这种感觉。因为他的心性是空,具备了精神层面的空灵,当他布自然空间中时便可随时随地引发如此境界,而不是一定要找到一处山青水秀的空间。宋人周敦颐《爱莲说》中“……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也是体现了一种人格的独立,它不受环境的限制,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拘禁,所以在这样的“生有立象”中才生发出这样的诗句。嵇康诗:“微风清扇,云气四除。皎皎亮月,丽于高隅。”单单几句话把这种气象传给了后人,显示出中国文化的旷达。意象的觅处也在于此,所以我们的书体与画体、诗体必须要有承载意象的方式。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来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家园都长满了荒草,还不赶紧回来,这不是写实而是写意,作者而对现实中的任何一个空间,都能够写意。此文描写出陶公对自己以往的哀叹,觉得耽误了时光,想到自己的追寻和
目标。觉得前面的路跟昨天比起来仍然宽广而明朗,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之境,把“实迷途其来远,觉今是而昨非”提升为自己的意气,找到了自己心境所归之处。眼前的一切均随着心境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我想到“吴带当风”,它俨然已成为一种境界,而不仅仅是一种画法,形势和内容合为一体。光是内容没有载体,再好的内容也不能给人以感发和启迪。陶渊明的诗句虽然写的都是自己乡村的生活,但是里面形势的载体却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这里面反映出向内如何思考,向外怎么汲取的问题,即心性不随风所动,仍然强调取象与立格作为人之本来阐述的一种单纯的形势法则,使天人合为一体。所以我们刘风的体验、对水的体验、对山林的体悟或者对某个形势的体验都是介入“道”的载体中才有感而发,化遭遇为境遇。没有感受怎么会产生一种形势呢?形势一定是通过一种感受的方式来决定深度,你能感受的深度决定了形势的深度,所以古人要强调“知行合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非常有道理的,值得我们细细体会。
三、敦厚的文化心心性
古人的诗,往往以自然之状来隐喻本源。孟浩然的诗表现了一种空旷,“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不仅给人以空旷的感觉,而且还注入了许多关于人生经历的问题。同样的,王维诗《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们在读的时候感受是什么,体会又是什么呢?中国古典文化有许多诗词,像王维、陶渊明都能够借助一定的载体把自己内心所感受或体验到的东西一一表现出来。而这种载体是中国人心灵最真、最善的东西,是中国人心灵最纯朴空间的体现。这种文化理念,这种载体是通过一代一代的文人,通过自己坎坷岁月的历练、磨难才生发出的。我们的先人,一代代诗人在他自身或者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仍然把最美好的空间奉献给后人,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
南唐后主李煜,作为一代皇帝,他无疑是失败的,把江山都丢掉了;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他又是伟大的,他把那种丧国之恨转化成了一种湿润的文化空间,留给后人很多宝贵的财富。
所以,当我们而对平常心、平常景和非平常心、非平景时都要认真体验和思考。尤其是已成为经典的传统文化,更需要通过我们自己真实的感受来体会。老子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陶潜:“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讲的是本源问题。如何把同常的体验化为一种技能、笔力、或笔法,并将其提升为境界,这是我们学中国画所面临的一个课题。陈良运论述“诗言志”的规范时写到:“我感到文须立其所象,立其所品,文质然人道有理法,小道有技能,而不同形式与文思载体之迹将各复归道。”荀子说:“《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其中,诗与志,书与事,礼与行,乐与可引为印映中的“境”与“象”。扬成寅者《王羲之》一书,内有书象论,引王羲之在《书论》中“凡作一字……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蝌蚪,或加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道出意象很重要的方法。而意象方式又与主体性情相关,感觉一种形象,首先要积累自己很多内在的经验,然后再通过载体把自己的经验和阅历释放出来。我们要考虑和笔墨中用笔的方法利用笔的规矩,还有墨法,如何去“得”,这个“得”便是先贤倡导的平常心、平常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外表,这是种心性空间,使我们能够被感发。当一种笔法或种用笔能使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声音,另外一种空间时,一种曾经的美好经验就会被唤起。所以像王维、陶渊明诗句里对松、石的描述,其形象已经净化,虽然通过很具体的物,但所阐释的象却是“心性”的文化理念。
今天看古人经典作品,包括看近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他们的具有敦厚的艺术基础和文化精神的人格和艺术是以心性象、立格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道理就在其中,但做起来非常艰难。就像李可染先生讲的,要下大力气回到传统中体验,同时要在当代的生活中加以自省,自省是属于心性的文化。中国画强调自我完善,要自省才能进入到一定境界中,所以有感而发,自然而然的体现需要浑厚的学养来支撑。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中国文化与生命相关,指出中国文化理念有一个特点,凡是与自己生命相关的都可以有感而发。但是何为与生命相关?中国每代诗人之间都印映出人与自然的道心,在文化空间里,在自己的行程里找到自己所感悟的东西,如董仲舒所言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曾使多少人为之倾心,但当你真正到了他所描写的那个荷塘——清华大学罩面那个荷塘,你会发现也不过如此,这个大约三百平米,人工挖出来的荷塘怎能与乡村的自然荷塘比,但是朱自清先生却能写出这样美好的散文,可见这是他从心里引发出来的,而不只是眼前的平常景。它包含了中国的文化空间,也包合了他独特的个人体验。如果没有这样的体验,只能是表层的东西,所以,文者见心性,全在心得,而取象、立象、品象是在本心立格的自然中生发。中国美术史有两种不同审美理想,以六朝文来比较,初发芙蓉与雕缋满眼的文体,一是心性感发, 一是缘事而发,前者注重的是文化心性。
魏晋刘桢《大暑赋》云:“其为暑也,羲和总驾发扶木,太阳为舆达炎烛,灵威参垂步朱毂,赫赫炎炎,烈烈晖晖,若炽燎之附体,又温泉而沉肌。兽喘气於玄景,鸟戢翼於高危,农唆捉鳟而去畴,织女释杼而下机。温风至而增热,欹悒慴而无依,披襟领而长啸,冀微风之来思。”这里似乎缺少了‘些意象空间,具体的空间没有产生意味,所以是缘事而作。陶渊明《归园田居》:“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则寄予了人类共同向往的空间,体验的载体与人的精神、人的心性相关。
叶嘉莹教授在古典诗词分析论述中曾例举《玉阶怨》三首诗,并由此引出了“实”与“虚”,“具象”与“意象”等课题。其中,虞炎诗:“紫藤拂花树,黄鸟度青枝。思君一叹息,若泪应言垂。”偏重于对具象事物的描绘而缺少空间意味;而谢眺:“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则比较细致精密,把很细微的感觉写了出来,但是仍然给人以很现实的感觉;而李白:“玉阶生自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此月有拟人之感,所以月虽远但感觉很近,传达出一种心象的空间。董其昌论画:“摊烛作画,正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意在远近之间,亦文章法也。”古人“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以一种精神的观照成为印映合一的空间,意象便在这种空间里产生。这个时候,面对现实,怎样去把握格与象很重要。古人“净心抱冰雪”“对酒乃当歌”“茫茫余落晖”“惟有孤明月”之境,既是一种现实,义非现实,更是一种心体的自然之境,物与我齐一,物通过主体和心性被描述,体验并上升为对格的观照与追求。
绘画一定是反映人所追寻和遵循的一个信仰,并立足于信念,我们通过笔墨载体来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代人文境界,笔墨才能成为一种“气象”,同时也印映出人在自然中如何铸炼心性并把握立格、立象的方式,即“一月印一切水,一切水映一月”的体验方式,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思考和领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