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乃荣:上海话中的城市精神
2009-03-18胡凌虹
胡凌虹
上海又成了新词新流行语的集散地
记者:钱老师,你从学生时代开始至今,一直在研究上海方言,也出了很多上海方言方面的著作,你认为上海话与其他方言相比,它的形成发展有怎样的特征?
钱乃荣:上海话是历史悠久的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自宋代上海港形成以后至少有700多年历史。上海开埠以后,很快成为一个移民大都市,占80%以上的外来人口陆续带来了各地方言和外国语言,使上海话在老上海话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快的变化,变速为其他方言所无。不过上海话的快速发展主要不是外来方言的影响,而是自身的创新和繁衍,它得益于商业社会繁荣后滋生的巨大活力,得益于社会的多元和文化民俗的多样化,现代化的城市生活。首先随着上海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大量新生事物出现,上海话里产生了大量的新造词、外来词,比如“马路、洋房、自来水、电灯泡、沙发、麦克风、课程”等,这些词后来都传到江浙,还被在上海集聚的文人(三十年代时有20万人)写入文章中,实现了与书面语的交融,进入普通话,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在上海多元化的社会里,市民各阶层、各职业的人群都参与了新词语的创造,大量生动的市井流行语、习惯用语,如“牵头皮、收骨头、出风头、吃空心汤团”在市民口头产生传播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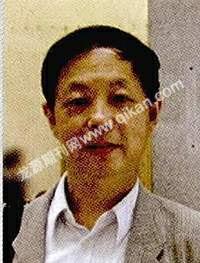
记者:从上海话的特征里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怎样的都市气质、市民精神?
钱乃荣:在上海话里,有些词语像英语一样没有明确的褒贬,含义很宽容广泛。比如“帮帮忙”既可以指帮忙,也可以指不要你帮忙,正反都可以讲。这跟上海这个开放社会有关,不强调好坏的明确区分。上海话里还有很多成语不讲究出身,比如说“避风头”,可能之前用在黑社会,风声来了,去外边避一下风头,后来就用得很广了,比如说“在文革中,我躲到山区总算避过了风头”。在上海,一出现特殊含义的词,马上就会在群众间推广开来,比如UNIVERSITY被调侃成“由你玩四年”,old three old four(老三老四)也在青年中传开了。这反映了海派的奇思遐想、领异标新,也标志着这个城市活跃的思想,发达的多元文化。这两年上海人在语言方面的创造性思维又活跃起来了,仿佛回到了上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成为了新词语和新流行语的集散地,很多上海的杂志、报纸把最新的口语吸纳进去,然后流传到全国各地。比如原用于股价下跌资金被困的“套牢”,进了《现代汉语词典》,现又被上海人活用,指结了婚离不了,或指陷入爱河进而引申到被某事牵绊。
记者:你曾说过,一方面要推广普通话,另一方面吴语方言也要得到很好保护。那么现在上海话的现状是怎样的?为何你一而再强调要保护、传承上海话?
钱乃荣:在上海普通话已经推广得很好,现在就要转过来注意保护、传承上海话了,因为国家所有的语言资源都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部分,方言是普通话丰富发展的源泉。小学、中学里面,不许学生讲上海话,连下课也不许说,有句口号叫“进了学校门,到了北京城”。有的学校进行评比,说了方言要扣品行分,这样家长也不敢在家里多跟孩子讲上海话了。孩子到了大学再重新学说上海话,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上海话中的许多有特色的词语不会说了,这样10年过后上海话要脱节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统计,黄浦区老闸区的上海籍人只占区总人口的6.4%,但外地来的人小孩都会说上海话,过去上海话不用学,跟着大人就会说,现在反过来了,普通话成为孩子出生后的第一语言,上海话反而成为第二语言。元旦前,我们开了第二届国际上海方言学术研讨会,有人也提到不要片面极端地理解校园语言。要区分公域和私域,孩子之间下课的讲话、老师和学生交谈也可以用方言。
记者:以前当一个外地人来到上海,第一个感到隔阂与被排斥的是语言上的不适,但是现在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很多人觉得会不会说上海话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钱乃荣:任何事情都要注意共性和个性,其实学上海话还是非常有用的。《新英汉词典》主编陆谷孙说,我到美国去,那里比较受群众欢迎的电视剧一半听不懂,都是他们当地的方言词和俚语。方言里有很多细致的东西,有人开玩笑说为何要找家乡人谈恋爱就因为说悄悄语方便。各地方言中日常生活的动词形容词语气词熟语等都很丰富生动,比如表示“拉”的动作,普通话里有10多个,福州话里有30多个。英语的可用词汇有40万左右,而汉语大词典里收入的很大部分是古代人用的,属于不可用词汇。之前顾彬说现代文学是垃圾,语言上不下工夫,显然他是说过头的。但是也有点合理的地方,为什么不下工夫,作家们也很苦啊,普通话里用来用去也就5、6万条常用词汇,《红楼梦》里就擅长用方言中的俗语谚语。所以普通话与方言要成为好朋友,要交融、互补、双赢,不然普通话没有人们口语中活跃的新词语,就会僵化,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记者:要传承上海话还有一个问题是口语与书面语脱节,很多人只会说不会写。
钱乃荣:是的,现在很多年轻人由于多样化的需求在网上聊天时也喜欢用上海话,但不知道怎么写,加上没有相应的输入法,所以就用拼音或音近字代替,比如把吃饭写成“切饭”,把上海人写成“上海宁”,这些都是错误的,甚至可能导致沟通不畅。所以我与郑晓钧合作设计出了一个集结了25000条上海方言词语(包括与普通话字同音不同的常用词)与“上海话拼音方案”对应的上海话输入法软件,还出版了一本拼音输入版的《上海话大词典》。
海派文化主要是大众文化
记者:钱老师,你对海派文化也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你如何理解海派文化,你认为它的精髓是什么?
钱乃荣:海派文化是开埠以后,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大批的文化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共同创造的,底蕴是江南文化,主要的特点是海纳百川、中西交融。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就基本形成了有特色的文化。比如连环画,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那么多的连环画,题材非常丰富,而且群众性很强,影响了好几代人的文化素养和生活趣味。此外,当时上海涌现了非常多的文学作品、电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映生活的各个方面。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也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来。而沪剧、滑稽、上海说唱、评弹、越剧、淮剧等10多种江南江北的地方戏曲,也是在上海草创、汇聚、改造并在60年代初达到顶峰的。海派文化的基础是大众文化,有全民性的特点,同时也孕育了最优秀的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它们是在自由竞争的氛围中形成的。
记者:早前在上海,沪剧、越剧、电影、话剧等非常繁荣,但是任凭以前再辉煌,现今也难免衰落的命运,你觉得根源在哪里?
钱乃荣:除了票价太贵,把大众挤出剧院,演的东西也不贴近现代生活、不符合青年人口味,有时太注重教育意义。另外我想新世纪整个世界要讲和平、和谐,我们的文艺比如电影《黄金甲》、《英雄》、《夜宴》等,有较多厮杀血腥场面,还老是演古代王朝,讲统治阶级的勾心斗角,这些东西不是不能演,只是面对整个世界潮流,面对青年人,不要老是拿古代的斗争出来。你看有些国家的影视剧现在都很注重和谐,很多反映了年轻人和平生活中的矛盾冲突。
记者:现在在上海不少话剧、滑稽戏等也表现了年轻人生活,但是很多年轻人还是不习惯去看。
钱乃荣:这是很自然的。很多兴趣爱好都是从小时候开始的,年纪大的时候再看陌生的东西怎么会有兴趣?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大世界里各种剧团都有,里弄里也演出沪剧、越剧,大人在家也唱,我们小时候有很多少年歌曲、游艺活动,还有不少兴趣爱好,像集邮啊、集糖纸啊,都玩得很开心。但是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小没有感受大众化的娱乐活动,之后成为家长、小学教师的他们也就不知道如何教孩子、学生,而现在的小孩一空闲下来就是补习功课,没有时间去搞文艺活动,考试很好,什么爱好都没有,千人一面语数外。
记者:结合上世纪海派文化的繁荣,你对现在上海文化的发展复兴有怎样的建议?
钱乃荣:除了之前说的文化艺术要贴近现实生活,还要处理好雅和俗的关系。《红楼梦》开始也是俗的,现在认为是很雅的东西。雅从俗来,不要把开始有些俗的东西砍掉,今天的俗就是明天的雅。大众文化普及以后,精品就会出来。有人说流行歌曲里唱“老婆老婆我爱你”太低俗,那么弄得国家大乱的《长生殿》里的爱情就雅吗?现代人重讲历史有些不全面又有多大关系?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就把曹操写错了。吸引大众来听就是好的,文艺批评不能太绝对,应由群众来选择。在上海应该是各种爱好的人各得其所,比如现在的话剧街就很好,还可以建立起沪剧街,越剧街等,高票价与低票价并举,再要搞“平民戏剧谷”。所以无论是地方文化还是国家文化,最好能在宽松的环境中竞争成长,不要强求一律,有了发达的大众文化氛围垫底,优秀的、高雅的文化自然会不断涌现。
钱乃荣
1945年生于上海。现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上海方言有关著作有:《上海方言俚语》,《当代吴语研究》,《上海话语法》,《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话大词典》,《沪语盘点——上海话文化》,《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北部吴语研究》,《上海方言》,《新世纪上海话新流行语2500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