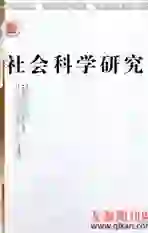西方民俗学视野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2009-03-10叶静余悦
叶 静 余 悦
〔摘要〕 现代意义上的古典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以周作人、闻一多等为代表的众多学者从中国文学的源头和经典取材,用西方民俗学的观念和方法重读古代经典。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民俗学在学术、学理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均表现出对本土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适用性。90年代末至今,结合民俗学方法的古代小说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本文认为,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不能截然分开,民俗文化的琐细方面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自身生活,透过习俗可以到达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把作家和作品放在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民俗文化层面上观察,从而达到对文学的主体——人的精神源泉的一般把握,这样我们的研究将更有作为。
〔关键词〕 古典文学;民俗学;跨学科;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1-0184-06
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民俗学以研究一国或一民族群体固有的传统生活文化为己任,中国现代引进西方民俗学科,是以文学切入的。西方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初舶来中国以后,为中国的本土文学研究提供了多一层视域和多一重的理论选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文学理论和民俗学方法的交融互用已为当代学者所接受和认同。在古典文学批评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是这样,很多学者在传统考据学和训诂学之外,另辟蹊径,运用民俗学的观念、方法,发现和解决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给人启发。
近20年来,古典文学和民俗学虽然在学科上都有边缘化趋势,但是结合民俗学方法的古典文学研究,似乎方兴未艾,不少富有创新意味的研究论著的出现,使得新时期的古典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更加多样化。本文关注这方面的尝试与努力,在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型古典文学批评和研究进行整体梳理的基础上,着重考察结合民俗学等多学科观念的古典文学研究情况,以及民俗学方法在其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一)
西方民俗学的引进发生在20世纪初,“五四”运动把当时已经僵化了的正统文学(所谓“贵族的文学”)视为中国落后贫穷状况在文化因素上的顽疾痼瘤,而把与正统文学相对的民间文学提上了史无前例的高度。〔1〕许多学者参加了当时北大倡导的收集歌谣的学术运动,为的是给中国文学增添范本,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然而,若要正确地认识和研究民间文学,必须找到先进的理论方法为治学之器。恰逢其时,民俗学理论被当时西学东渐的文化浪潮裹挟着引入中国,为当时苦寻救国救民出路的学者们所接受和实践。
朱自清《歌谣与诗》中说:“在民间文学领域,西方[注:朱自清1929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课程的讲义中,借用《英语民歌论》(獷nglish Folk睸ong,1915)来界定中国的古代歌谣概念。见朱自清《中国歌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5页。]的影响如此强烈,迫使我们不能不追随之。”“西方的影响”这里指的是那些具有启蒙意义的学术观念,“我们追随”的方式一是把那些著述移译过来;一是把接受的理论和方法用到本土文学的研究上来。歌谣运动中对于民风的调查和口头创作的采录,既是民俗学意义上的田野作业,其实也是语言学(或者说方言学)意义上的资料搜集。从理论上讲,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创作和传承的口头文学,是一种集体性的创作。然而口头文学必须经过专人的收集和记录整理(在此过程中还难免被辑录者润饰删改),以歌谣、谚语、传说、故事等各种样式被收进历代的典籍或文学作品里。口头文学终究还是要以书面形式才能保存下来。比如《诗经》既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民间歌谣的集子,《山海经》、《楚辞》里记载的多是上古时代的神话和传说,包括《史记》在内的许多正史杂著,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民间文学的成就。因此,从民间文学的内容看,能经历漫长年代而依然留存下来的,大多是依靠古代的典籍和文史资料。
正因为如此,民间文学研究实际结合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大多由古典文学入手。周作人的童话专论、茅盾的神话研究,都深受英国民俗学家安德路•兰(Andrew Lang)的启迪;郑振铎对俗文学、赵景深对童话和戏曲、黄石等人对神话传说的研究等等,无不吸收了西方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进化论”、“文化遗留物”等学说为主要特征的欧洲文化人类学深深影响了一大批力图摆脱乾嘉考据学派的中国学者。当时的学术思想和学风整个为之转变,如宗教民俗学家江绍原所说的,“中国学人开始用近代学术的眼光和方法,去重读他们的古书和发掘研究他们的古物了。因为有这种工作,他们对于古思想,古生活,古制度等等,业已重新发见了若干事实——若干被人误解或忽略了的重要事实。”〔2〕
尽管在学术形式上有差异,西方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关注文化(或文明)的连续性和传承性,认为文化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主张从田野调查、神话传说、不同结构的遗俗甚至陈旧观念的碎片当中,去“还原”历史和社会生活场景。这些理论和方法正是学者们重新审视古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的一个合理且必须的选择。1930-1940年代,运用民俗学和神话学方法对古典文学进行诠释和批评,实践得最彻底也最成功的学者中,闻一多无疑影响最大。他在《姜嫄履大人迹考》中考证“履迹”为祭祀中一种象征耕种之事的舞蹈,而“感生”说乃耕种季节时“野合”风俗之结果;《伏羲考》一文论证古代“兄妹配偶和洪水遗民”的故事;用民俗学和神话学去解释《诗经》、《楚辞》里诗歌的性爱象征和原始乐舞“性爱享神”的功能等等。无论这些结论如何新奇大胆,闻一多既没有背离乾嘉考据学的“实证”精神,又没有脱离民俗学领域的观念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畴里去研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3〕。“生活范畴”这个概念在当时提的人并不多,但闻一多认识到,它对帮助人们“读懂”古书,从而接近古人真实的思维、情感和生活习俗,助益良多。
从事古典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孙作云,秉承导师闻一多的学术思路,依然走民俗学的路子去研究《楚辞》、《诗经》以及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在《诗经恋歌发微》一文里,孙作云从古代人民生活的两大季节谈起,论述与这两大季节相应的风俗习惯和典礼仪式,进而发掘出《诗经》里有十五首恋歌都与上巳节祭祀高媒、祓禊的民俗文化有关。〔4〕
此外,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郑振铎间隔十年先后发表的《汤祷篇》和《玄鸟篇》,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学术论文,它们的意义并不在于那些打开人们眼界的具体观点和结论,而在于结合了理论的分析和考释使人们对古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的价值(或者说精神)有了新的思考角度,也使得他们的研究具有了区别于前人的鲜活的时代特征。
从上述可见,20世纪上半叶,民俗学视野中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批评多从中国文学的源头和经典取材,用神话的、习俗的、仪式的科学来参证文本中的经典意象,阐释遥远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感。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是零星的、片断式的,但它们开创性地将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融入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批评领域,提升了学科的眼界,深化了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
(二)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新形势和学术研究新气象的鼓舞下,民俗学重获生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也得到开拓。“美学热”、“方法论热”、“文化热”等风潮此起彼伏,一些新式的文艺理论也在此时陆续被输入到国内学术界,比如系统论、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原型批评等等。早在20世纪初就来过中国的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在学理和学科方面也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而面对新时期国内外学术环境的显著变化,中国的传统人文学科在当时似乎并未及时解放思想、调整思路,而是继续沿袭以作家生平、时代背景、思想内容等为基本模块的套路去研究古代文学,相形见绌之下,学界开始对研究方法的单一、视野狭窄等问题提出批评。要解决这些问题,方法的改变和理论的更新是唯一的出路,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提出了相应的看法,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
季羡林先生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高度谈到文学的研究应该注意比较,他赞同闻一多的主张,认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文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民族性和时代性。代表民族性的民族文学传统是历时形成的……可以算是经,代表时代性的民族文学随时代而异的现代化,这是共时形成的,这是……纬。经与纬,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就产生出了每一个时代的新文学”〔5〕。 在比较的概念和方法上,“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季羡林认为,类似的或相近的比较会带给学科新的活力;〔6〕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二者应该结合起来,相得益彰。〔7〕
金克木先生就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和适用层面等问题发表过一些精要的见解。他意识到,“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这四样知识在50年代以后,国际上几乎交叉起来”,“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对于研究文学来说,和关于作品的知识、美学的知识、历史的知识同样重要”。〔8〕金克木指出,“当时国内的民俗学研究仅是民间文学研究,而广义的民俗学研究则包括流动传播的研究、历史地理的研究、心理分析的研究、结构形态的研究等,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学研究”〔9〕。
两位文化大家虽然没有专门就文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提出具体性的意见,但他们不约而同都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可以用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话来总结,“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10〕。
1980年代,第一个从学科的理论层面提醒大家关注民俗学与古典文学、民间文学之间关系的,是钟敬文先生,这大概与他以文学背景从事民俗学研究的经历有关。他很早就注意到日本学界流行的以民俗学做手段,研究古代史和古代文学史、艺术史所取得的显著成果。他认为民俗学和古典文学“联结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部分就是民间文学”,一方面,“现代的民俗资料,可以被运用去解决或推断古代的民间文学(如歌谣、传说、神话等)的某些问题”,另一方面,“民俗学资料可用以论证现代流传的民间文学作品里的社会意义和存在问题”。〔11〕他还从民间文学在古典文学中的位置、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民俗现象、民俗学方法如何为古典文学所借鉴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古典文学和民俗学之间的关系。〔12〕80年代中后期,钟敬文提出了民俗学理念的新思路,认为民俗学既有一般性的研究,又有局部性的研究,即使一种局部性的民俗学,往往又包含着若干支学,如文艺民俗学就包含有神话学、史诗学、传说学、童话学、谚语学等。他指出,“民俗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意识到和没有意识到,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就大不一样”〔13〕。钟敬文在学科构建方面的倡导和努力促进了民俗学学科系统的整合,许多高校的文科院系相继开设了民俗学课程,一些专家学者在反思学理和展望学科前景的同时,分别提出了建立与民俗学相关的新的独立学科的构想,如历史民俗学、宗教民俗学、文艺民俗学等。
以文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为例,80年代后期,陈勤建教授提出文艺民俗批评的新模式,是以民俗学与文艺的特殊关系作为切入口。1991年出版的《文艺民俗学导论》一书中,陈勤建阐述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即“从民俗学独特的知识、理论、方法对文艺发展的一些主要侧面进行分析研究,力图通过文艺作品的民俗批评,把文艺学和民俗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揭示文艺创作、欣赏、研究过程中的民俗机制和文艺发展中过去所忽视的一些规律”〔14〕。当时文艺民俗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三个:一是从民俗学角度理解文学作品里的环境和社会;二是通过民间文学的传承了解其向文学化发展的要素;三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某种意义上的民俗资料,从而研究文学发生的时代背景。文艺民俗学从一种文艺研究的新方法到一门新的学科,和传统的文学研究不同,和民俗学的文学化倾向也不相同。虽然它不可能去研究文学和民俗的全部,但是两学科的交叉并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新的学术空间。
从上述学术环境、学术理念和学科建设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在跨学科研究兴起的时代,文学的研究不论古典还是现代,要想走出困境,有所创获,必须选择一条符合自身特质的道路,而民俗学的理论方法正是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
(三)
20世纪80到90年代末,古典文学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格局,许多风靡一时的理论来得快也去得快,然而学科的交叉和拓展却是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些相关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大大拓宽了(古典文学的)研究视野,增添了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15〕。具体到民俗学和古典文学相结合的研究,虽然并未大红大紫,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致来说,这时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可概括为以下三类:
1.文学作品与民俗文化(知识、习俗、信仰等)的互动关系研究。
这类研究简单来说,就是从民俗的角度读古典文学作品。复杂一点,包括文学与某一时代(或时期)民俗文化的关系、风习性的文化传承对创作主体的影响、民俗意象与文学作品的审美关系等等。如邓云乡《红楼风俗谭》(中华书局,1987),对《红楼梦》中的风俗民情,溯本求源,旁征博引;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即是民俗学意义上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从民俗学的视角涉入文学史的研究,探讨唐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的关系,全书涉猎甚广,从岁时节日、都市民俗、妇女生活,到神灵崇拜、巫术禁忌、民间文学与技艺,材料丰富且不失理论支撑,是跨学科研究的一次很好的尝试。此外,对古代笔记小说中的神话宗教和民俗因素也有初步的认识和研究,这其中不仅有国内学者的著述,也有国外相关研究的译介。[注:如白化文、李欣《古代小说与宗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李稚田《古代小说与民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日〕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中华书局,1993年;〔俄〕李福清《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说》,尹锡康、田大畏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等。]
2.将民俗作为古代典籍、出土文物之外的“第三重证据”研究法。
这种方法实是闻一多先生早期神话学研究方法的延续。它注重田野调查,也可以说重视地域文化的特殊形态和风貌,试图用活态民俗中的风习性文化来参证古代的文学作品。这类研究中的实地调查所具有的原创性使得研究本身新颖而可贵,有人称其为一种“文化的考古”。萧兵和林河等人以楚文化和沅湘诸地的民间文学为基础研究《楚辞》可为这一类方法的代表。[注:例如,萧兵 《楚辞与神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楚辞新探》(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林河 《试论楚辞与南方民族的民歌》(《文艺研究》,1984年第1期)、《楚辞与沅湘民俗》(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等等。]
3.神话和原型批评。
这类研究吸收了J•G•弗雷泽(1854-1941)的“巫术宗教”理论、荣格(1875-1961)的“集体无意识”和弗莱(1912-1991)的“原型”批评,认为最基本的文学原型就是神话,“原型批评”即“神话批评”。它要求从整体上把握文学类型的共性和演变规律,当它用于古典文学批评时,则成为一种宏观的文化阐释。叶舒宪《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多部著作对上古神话、诗歌、风俗、仪式、文字等领域做了宏观的透视;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东方出版社,1996年)从传统文化中抽绎出“兴”和“象”两大系统,用原型理论阐释月亮、黄昏、雨、门、船等一个个语词,试图理解古典文学中的某些经典意象;另外,原型理论还被用于中国古代戏剧的文化阐释,如胡志毅《神话与仪式:戏剧的原型阐释》(学林出版社,2001年)[注:此书出版于2001年,但其理论方法及写作时间大部分都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等。
以上三种类型是在20世纪前半叶研究基础上的延续和深化,古典文学领域一些难解的题目或者被传统文学批评所忽略的方面得到了有意义的研究,民俗学的观念和方法使散佚的神话传说有了文化的模式,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到,一代之文学有着精神生活的丰富来源,丛谈小语亦有可观的前景,上述论著的创新之处也正在于此。
毋庸讳言,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问题和不足,比如神话原型的理论对文学作品、文化现象的解释限度问题。中国古代的自然神话其实很不发达,这与古希腊、古埃及等民族体格完整的神话系统形成鲜明对比;盘古创世神话中“道”、“太极”、“气”等概念是中国先民宇宙观的基本要素;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意识强烈而宗教情结相对淡薄;诸如此类,这些中西方文化结构的差异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考察的。20世纪90年代,钟敬文就曾批评说,神话研究像是“猜谜”,的确,只是简单地把西方的神话理论拿来解释中国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要么削足适履,要么只能是一种猜想了。任何理论都有它的适用范畴,视野过大有时会导致思维的泛化,而过度的文化诠释无益甚至有害。我们对神话原型理论的运用应该在充分考察本文的个性前提下进行,以避免对原始思维和精神的扭曲。
(四)
近几年来,很多高校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选题在悄悄地发生转变,一个变化是研究对象的边缘性和交叉性;另一个变化是研究方法的多学科性和综合性,这也是由研究对象的各方面因素所决定的。这些选题包括文学与通俗文化的交流互动;宗教民俗与文人及其作品的关系;民俗文化对文学形式走向的内在作用;文人的日常生活和交往活动等等,总之是将目光投向广阔的传统文化生活的不同侧面,或者是对文学作品中的某个题材某种体式进行研究。而从这些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民俗学的观念方法占了不小的比重。以古代小说为例,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就小说论小说,有的从“母题”和“意象”等角度来解读小说,立论新颖,有的把小说和古代的文化紧密相连。如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用“母题”概念分析小说的生成和演变,在追溯岁时民俗事象的同时,阐明了古代小说意象的源起,古代的岁时民俗以及与古小说相关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得到较为系统的呈现。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说的变迁》(中华书局,2007)把宋代文言小说放在社会文化、文学生态的层面上,探讨小说与文学转型的内在关系,从而揭示它趋于世俗的变化。
在古人的眼中,小说是“君子弗为”的“小道”,而在现代人的心里,小说是挖掘古代中国人生活文化的宝藏。这和西方意义上的小说理论又全然不同,因此它们的解读难免有“隔”的感觉。由民俗学角度进入古代小说的研究,却没有这种理论上的困扰,因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正是当时社会的世俗风尚和生活文化。我们还是从数量极多的研究成果中撷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来做简要的说明。孙逊《释道“转世”“谪世”观念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民间化的宗教信仰对古代小说的内容、形式和主题的深刻影响。刘勇强《掘藏:从民俗到小说》(《文学遗产》,1997年第6期)论述了古代盗墓和掩埋金银宝物的风俗演变和小说题材的契合,从一个侧面考察了民俗和小说的密切关系。杨天舒、唐均《林黛玉形象与中国民间文学中的“下凡-归仙”母题》(《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3辑)从“世外仙姝”形象的性质入手,考察林黛玉与民间传说中的神女之间的渊源,对进一步理解艺术形象的文化内涵很有益处。朱迪光《民间信仰、母题与古典小说的叙事》(《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一文将古代的宗教民俗与小说母题相结合,探讨了两者对古典小说叙事的作用和影响。
我们追本溯源就能发觉,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其实是启动中国小说研究的触点,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先贤们对民间文学的启蒙式创解和对一向被高雅文学所轻视的“小说”的大力提倡,很难想象我们的小说研究会从寥若晨星的昨天走到如今的多元格局。民俗学方法在纷纭的西方文化理论当中,只是小小的一束,但它能够适应于中国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场域,并且或隐或显地,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走到21世纪的今天,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探讨:
1.民俗学方法在运用于文学和文化传承的研究时,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而这种解释能力又并非为文学本身所具备。由于民俗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它是研究一国或一民族的文化内涵的学科,这些内涵是相对稳定的,集体性的,因而它对世风民俗的表现、移风易俗的发生、约定俗成的习惯等等,必须做出描述和分析。
2.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领域有时很难截然分开,文学作品和民俗文化因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民俗文化也是文学研究者的对象之一。
3.民俗学在学科上带有交叉性,所以它具备和文学研究中的某些方面相契合的特质。在中国,民俗学从西方经过日本传入以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本土化的过程,使它从一门世界范围的人类学具体到以研究一国或者一民族民俗文化为主的人文科学。因此,虽然在学理上它是西方的,但是在学术的研究对象上则是本土的、历史的、国民的。
我们不必穷尽所有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文学的研究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民俗学在各自独立的同时,又同属于更大的文化系统,从文化整体中来审视相关学科共有的文化对象,才能使民俗学和文学的“联姻”成为可能。
(五)
在危机与挑战如此激荡的21世纪,各门学科都在前进路途中对本学科的研究过往和发展前景加以省察和思考,文学研究也不例外。文学既是“人”的学问,也是文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个“人”是处于时代文化大熔炉中的人,这个“文化”既是当下的文化,又是历史民俗文化的承续,还可能是未来文化的薪火。拿我们自己来说,世风民情和时代文化中的微小细节都会对我们的言行举止产生深刻的影响,只是由于我们身处其中而不觉得罢了。正如很多学者所意识到的,前代的学术风潮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往往是时代变革和政治环境变化的某种反应和要求。那么,在当今国内的学术环境相对宽松,而国际上政治经济风起云涌,价值体系又面临新一轮重估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吸取前人的观念和成果,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应该是一个嵌入我们所有的学术行为的问题。
在古代文学作品的考证、校注、辑佚、补遗等基础性研究工作日趋完备,信息检索和资料查找方便快捷的今天,结合民俗学等多学科方法的研究对于开拓古典文学的视野、提高古典文学的综合水平固然重要。但同时,我们要看到,这种边缘交叉性的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深刻地理解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和充分地掌握文学资料,会很轻易地把交叉停留在文学作品与社会风俗和文化背景的表层。我们当然需要那些以展示民俗生活的种种现象为主要目的的传统文化普及工作,但对于研究工作来说,我们更需要在现象背后做出甄别和分析。我们要注意,停留在文学作品上的研究是不够的,对于构成文学元素的某些传统、情节和形象的源起的研究也属于文学的研究。
古典文学和古代社会像是现代人永远不能亲身踏入的神秘世界,我们可以把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当作理解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化的一扇窗户。透过习俗,我们可以到达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指导行为方式,民俗文化中的琐细方面其实正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自身生活。因此,在对文学创作主体的研究中,从作者的生活经验等方面(而非仅仅是生平经历)去看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把宏观背景和微观习俗相结合,会把我们的研究带入不一样的天地。
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文献资料的真伪需要加以考证,这是我们使用材料的前提,而对于历史上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佚闻、野史,古人未能做出判断或误判的,我们也可以用民俗学的方法去辨认、厘清它们与文化的关系。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前人也许已经研究过我们感兴趣的任何东西,但这不代表没空间可做了,前人的研究正是我们的起点,因为他们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对某个问题展开讨论的基础,确切地说,是一个深入研究的起点。对于这样的研究,新材料和新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民俗学所注重的实地调查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也应当为古典文学研究者所掌握。此外,地域文化和文学的类型研究也要与相关学科结合起来才能有所作为,从而使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得以接通被时间割断的古今文化的桥梁。
古典文学是历史的,民俗学是现代的。民俗学以探索本国本土的民众生活和理想为目标;文学的研究说到底,是对时代和人的精神源泉的一般把握;但从人与人的对话这一点上来说,它们是相通的。
〔参考文献〕
〔1〕〔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M〕.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2〕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导言〔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3〕刘烜.闻一多评传〔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75-276.
〔4〕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M〕.中华书局,1966.279.
〔5〕〔6〕〔7〕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325,157-158,166.
〔8〕〔9〕金克木.文化卮言〔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268,266.
〔10〕钱钟书.诗可以怨〔A〕.钱钟书散文精选〔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11〕钟敬文.民俗学与民间文学〔A〕.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M〕.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65-169.
〔12〕钟敬文.民俗学与古典文学〔A〕.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80.
〔13〕马昌仪.钟敬文与民俗文化学访谈录〔N〕.文艺报,1992-03-14.
〔14〕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绪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15〕徐公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近代化进程论略〔J〕.中国社会科学,1998,(2).
(责任编辑:尹 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