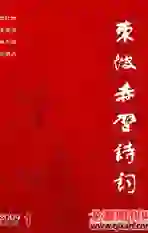从格律诗词谈到新诗
2009-03-07
吴洪激:本刊是以传统格律诗词为主兼发新诗的诗词文化期刊,故所发作品坚持平水韵的诗词格律(新诗除外)。然而,我们在一些刊物和报纸上看到,一些完全不符合格律要求的所谓诗同却层出不穷,还堂而皇之冠以“七律”或“七绝”之名,有的甚至是名人名家,搅乱了诗词的体例,模糊了诗词的界线。我在楚天都市报上看到您发表过很精辟的意见,您能就这一问题和本刊的定位,淡谈您的看法吗?
谢克强:诗词近些年确实比较热,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中国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诗传承下来的;是由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令、清诗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奋勇当先的新诗一路传承下来的。中国之所以号称诗国,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孩子的启蒙教育也是从诗开始的。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大概由于这些些原因,不要说赵忠祥这样的人,还有山东省作家协会的某副主席等以诗言志抒情也就不足为奇了。据我所知,在中国大陆,没有那一个县没有诗词学会,有的乡镇都有诗词学会。赵忠祥的《神七赞》经网络传播引起热议,也引起更多的人对古典诗词的关注,我以为是件好事,至少可以使人们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存发展现状有一点了解。《楚天都市报》的记者采访我时,我是说过“格律诗自有其规律,且要求严格,如果不合规律,比如平仄不对,那就不是格律诗了。”当然还不止这么多,但核心是这个意思。我也在《楚天都市报》上看到有的同志谈到:“诗词写作重在意境,个别失律的地方可以接受,规范不是不可以打破的。”这个意见我不敢苟同。我以为一切艺术都重在意境,但每门艺术都有自己的规范,诗之所以是诗,词之所以是词就是由它们的规范决定的。规范当然可以打破,但打破还得遵循它的艺术规律,如果失律那肯定就不是律诗而只能是伪律诗了。诗人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就说到“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这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他在这里只讲平仄不符,如果失律那就更不是律诗了。所以他在1957年《诗刊》创刊时给《诗刊》主编臧克家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其中除了表示同意《诗刊》发表他多年创作的旧体诗词18首外,还写了如下一段十分重要的话:“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我还注意到臧克家在《毛泽东和诗》中还转引了毛泽东的另一段话:“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他对新中国诗歌发展的战略设想呢,即新体诗和旧体诗都要发展,但应以新诗为主。
贵刊是当代中国诗词的重地,我赞成贵刊的定位,也钦佩贵刊为发展中国当代诗词所作出的贡献。
吴洪激:有人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格律诗词也要进行改革。此话不错。尤其是普通话的推广,过去平水韵的许多仄声字变成了平声字。如拼搏的“搏”,国家的“国”等。但我认为格律诗词自南北朝的齐梁时期发端,直到唐初成熟定位,已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今天的诗韵改革,也须加以探索,也要一个漫长的时间,不能一蹴而就,故本刊专设了“诗改试验”栏目,就是希望接纳各方面有探索性的新格律(如旧词新韵、自度曲等)、新声韵作品,为诗词改革推波助澜,积累经验。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谢克强:随着时代的发展,格律诗词要进行改革,这个话题已说得很久了,我就看过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很好的见解。要改革是一回事,怎么改革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问题不仅是古典诗词界,在新诗界,这个问题也讨论得比较热烈。在我执行主编的《诗歌月刊》下半月刊2008年7月号中就发表了诗评家吕进先生的《论新诗的诗体重建》和诗评家邹建军的《中国新诗诗体重建的基础与路径》。不久前,我还读到丁芒先生的《对当代诗词体式改革的几点思考》。丁芒先生不仅在思考,并进行了改革实践,创作了大量的新体诗。他将他创作的新体诗集寄给我品赏。我在品赏时,不禁想起诗人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信中的另一段话:“要作新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的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我感觉丁芒先生似乎是在作这种尝试。
形式当然是重要的,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内容。就我目及的范围,我看当前格律诗词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内容。前几年,省直某系统组织了一次诗词大赛,来稿有几百篇(首),我应邀作为评委,我在读过几百首格律诗词之后,不仅感觉内容大多雷同,甚至语言也大多相似,似曾相识。最近网上传播赵忠祥的《神七赞》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且不说它是否合律,单就诗的语言就缺乏诗意。这类重大题材,选择切入的角度非常重要,不仅要有独特的角度,更要有富于个性和张力的抒情语言。中国的诗歌是特别强调意象的,虽然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都是试图再现什么?表现什么?说明什么?但诗人总是力图避免赤裸裸的表白。创作实践使我体会到,意象实质上一种经验的表达而且是自己所有的经验,诗人写出它来,实际上是在咀嚼自己的独特性,或者说是形象意蕴的再造。
吴洪激:新诗是本刊的一翼,我们开辟了一个专栏,专门发表新诗。但我在审读新诗的来稿时,总感到有些迷茫。一是读之如嚼腊,二是甚至读不懂。记得我们这一代人走上文坛。也是从写新诗开始的,当年熊召政同志那首《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是那样清新明白。令人震撼。我认为新诗写作也有个大众化的问题。您是当代著名诗人,您能同我们的新诗作者谈谈这个问题吗?
谢克强:可以这么说,这几十年来,我没有脱离中国新诗现场,对新诗生存发展现状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先说说诗的大众化问题。我个人认为,诗不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而是一种小众化的艺术。有人曾说:诗属于天才,而歌属于大众。这话虽然有点偏颇,但自从诗歌分为诗与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诗是和者寡,而歌却流行众。因为写诗、读诗或者欣赏诗还是要有一点闲情逸致。这就致使她不可能在大众中流行,而只能为少数人所钟情。在我的印象里,新中国诞生后似有过三次诗歌大众运动。一次是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成果结集为《红旗歌谣》;一次1976年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而发生的“4.5”诗歌运动,结集《天安门诗抄》;再一次就是今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而迅速展开的一次诗歌运动,就我目力所及,大概结集有几十部之多,为中国新诗发展史所罕见。《红旗歌谣》、《天安门诗抄》和汶川地震诗集都列在我的书架上。这几次诗歌运动的发生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因为人们有话要说,有情要抒,不吐不快;而诗歌就是“诗言志、歌咏言”的艺术,所以有“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说。就这三次诗歌运动之后结集的诗歌作品来看,客观地说,符合诗歌艺术规律、体现诗歌艺术特质的诗歌作品并不多。在这里就有一个思想与艺术的标准了。你说到诗人熊召政的抒情长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这使我想起我当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的一次诗歌朗诵会,当朗诵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时,仅仅开始朗诵这首诗的标题“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全场几万人欢声雷动。那时,诗是作为思想解放的先导出现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时过境迁之后,这些诗可能只是作为一种历史文本了。所以诗人徐迟在一次诗歌对话会上就说:诗有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诗能够发表,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不难;第二个层次就是诗发表后,当时能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有一点难,但也不太难;难的是第三个层次,诗发表了,也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还要留得下来,传得下去。而当今诗坛,发表诗是太容易了,有一点反响也不太难,难的是可以留得下来传得下去的诗作太少。你说你在审读新诗的来稿时,总感到有些迷茫。一是读之如嚼腊,二是甚至看不懂。这种感觉不仅是你,我在读一些诗刊上发表的诗都有这种感觉。因为现在很多诗歌作品已经丧失了诗歌抒情的特质、诗美的特质。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诗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要有富于个性的张力的抒情语言。诗也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艺术,而这种形象思维就是诗的意象,而且特别强调象外之象。这样的诗才可读、可品、可赏。反之,怎不味同嚼腊呢?
吴洪激:感谢您谈了关于诗的这些精辟之见,我想这对于本刊的读者、作者一定会有所教益,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