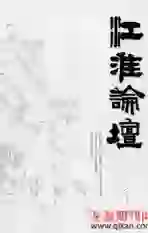“国语”如何统一
2009-02-26崔明海
摘要:近代国语运动以民众教育普及化为其初始目的,但与此同时,中国历来地域方言隔阂甚重,时人也认为民众之间因言语不通而互不团结,无益于国家强大。职是之故,推行国语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近代国语建构和推广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统一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如何认识、处理代表“国家”的国语和代表“地方”的方言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精英在语文规划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国语; 方言; 语言统一; 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H17文献标志码:A
近代国语改革以民众教育普及化为其初始目的,但与此同时,中国历来地域方言隔阂甚重,时人也认为民众之间因言语不通而互不团结,无益于国家强大。职是之故,推行国语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以北京话(标准语音)和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国语”在社会层面得到初步推广,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学校教育和各种社会宣传方式的推动下,近代国语推广发展到制度化实践阶段。[1]但在近代国语建构和推广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统一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如何认识和处理代表“国家”的国语和代表“地方”的方言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精英在语文规划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本文就此问题作一相关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国语、国民与国家
早在雍正时期,清政府就积极推广官话。其中福建、广东两地的语言系统与北方官话差异极大,以至两省官吏持乡音“赴任他省,不能宣读训喻、审断词讼”, 只能由“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 不仅如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官员“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使“身为编氓,亦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 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2]1074官民上下,语言不通,成为执政的重要障碍。因此,清廷特地在闽粤地区大力推广官话,规定“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涪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3]369-370但是,语言推广并非易事,清廷并没有能够实现语言统一,闽粤地区一直延续着原有的方言系统。 但这一时期语言统一还仅是清廷政令下达,专制统治的需要。
随着晚清民族危机的加深,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不少精英强调语言统一与民族认同、国家富强间的密切关系,统一国语呼声日渐增高。创制切音新字的卢戆章指出,如果人们“各操土音”,必然“对面无言”,而如果“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那么国家“新报、告示、文件以及著述书籍,一经发出,各省人等无不知悉,而官府吏民,亦可互相通晓。”[4]3这对于国家与民众而言,都是极为有利之事。而晚清桐城派教育家吴汝纶东游日本之后,深受日本国语教育思想影响,[5]96回国后即向张之洞奏请实施国语教育,他指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层差不齐,此为国民国体最要之义”,主张向日本学习,在学校推广国语教育。[6]436与此同时,他提出以京音统一天下音律,以实现语音统一。[6]436长白老民亦深谙此意:“世界各强国无不以全国语言一致为内治之要端,故今年吾国洞达治体者,亦无不深明此理。”[7]34 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在给时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呈书中,亦认为中国南北各省,“口音互异,甚有各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而“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因此,“统一语言”可以“以结团体”,可以强国家。中国“无事不规仿泰西,步武日本”,唯独对语言统一问题“漠然置之”,是不可行的,因此,强烈呼吁推行官话合声字母。[8]36
民国建立后,由于助推国家建设和统一的需要,舆论渐趋加强对国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强调,“国语”的重要性被纳入到“国家—国民”的话语叙述之中。蔡元培就认为国语是“融洽国民感情的媒介,是个人求知识,谋职业的应用,是服务于民族国家,尽一个国民应尽责任的应用工具。”[9]3-4远在日本的华侨呼吁只有学习统一的国语,才能“做中华民国统一国家的大国民”。[10]
而在1920年代,军阀混战、国家分裂,许多人寄希望于国语的推广能加强地方军阀对整体的认同,实现全国政治上的统一。倪海曙认为,民初旧的封建势力很快转变成军阀割据的状态,连年内战,“使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政治统一的需要,于是许多人又都从统一上着想,这种意识反映到语文改革上,便造成了注音字母与国语运动的合流,使‘待用文字的注音字母转变成了‘统一国语的注音字母。”[11]这正如时人所希望的那样,“方今南北纷争,忧国之士力谋统一,但统一南北,非先联络感情,则言语之效力乃大”。[12]这种国语统一观反映了时人现实需求。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众多精英认为语言不统一,方言隔膜造成了国人之间犹如一盘散沙,国族性不强。[13]50-58国民和国家之间的隔膜状态造成了国民只知个人、家族、乡土而不知国家、民族,正如蔡元培所言:“中国人民肯替家族、地方牺牲,而不肯替国家牺牲,就是因为感情的不融洽,像广东一省,广州、潮州、汀州、漳州都各有各的语言,所有时起纠葛,虽然也有其他种原因,但是语言的不统一,总是一个重大原因。”[14]1288所以在支持国语统一运动的人看来,国语就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象征,是“国民精神所寄托”,只有“国语统一,国民精神才能统一,现代的国家,没有不承认的”。[15]2而民众只有在操持了共同的语言之后,“国民统一之精神,自随而勃发,驯之五族一志,四亿同心,后扩充军备,以固国防,振兴实业,以裕国计,普及义务教育以培国本,发达科学技艺,以宏国用,种种问题皆得迎刃而解矣。”[16]7
以故,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近代语言统一观是一种国语、国民和现代国家共生的语言建设思想,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由传统王朝体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由于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人们希冀从统一语言进而实现再造新国民、消弭地域保护主义和加强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诉求。
二、政治权力和国语统一
如上文所论,国语统一提倡者大多赋予语言统一/国家认同和民众团结,方言/地域保护主义之间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以此强调国语统一的重要意义。但方言和地方认同、地方政治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现代学者金以林曾指出方言是民国时期粤系地方势力派形成内部认同的一个重要外在工具。[17]236但在民国时期,强调地方认同或者自治,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固守本土的方言而反对国语。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在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的联邦主义思潮时也认为,方言固然是地方认同和保守主义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倡导地方自治的情形下,方言的保护,并不一定要以不接受国语为代价。[18]238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国境内方言隔膜甚重,在支持国语统一的一部分人看来,地域性方言文化对国语推广和政治统一仍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这一点,在国民党企图统一全国的政治行为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以地方文化的代表形式之一——方言电影为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电影检查委员会从上海搬到南京,当时正是国家政治上寻求统一时期,电检会也在其时坚决主张,“对于侵害国语统一运动和大腿肉感诱惑社会的两种影片将严行取缔”,因为这两种电影都有不良的社会影响,所以都被归类为“不良电影”。而这种侵害国语统一运动的影片在当时的语境下大多是指粤语对白片,因为它表现了“广东人特别嗜好和桑梓观念之深,他们往往对于一张粤语对白片,会以多倍以上的欢迎热忱来接受它,于是粤语对白片在华南大走红运”。[19]744在代表国家利益的电检会看来,方言影片是形成地方性保守文化的重要方式,于国家政治统一实为不利。这种想法也是一直以来两广地区与南京中央政府之间政治矛盾的现实反映。所以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认为“中央数年来推行之国语电影政策,对国家统一关系甚大,当兹全国政治统一之基已奠,为整顿电影检政,杜绝将来流弊起见,由本会重申功令,通告全国电影界,以期促进国产影片之统一”,而“国语电影,为中央数年来已定国策,当此国家统一之工作努力猛进之际,决不能因地方区域特殊情形而改变已定之国策,此广东电影检查之不能不统一办理,而粤语方言影片之不能不加禁止”。[20]159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一部有蝴蝶、梁寒珍合演的粤语片《美德夫人》,电检会就以方言影片侵害统一国语为由,予以严厉的禁映,并且声言此种地方言语的电影,决计从严取缔。[19]744而电影界人士也认为方言声片(粤语、厦门语),已由电检会明令禁止,但一些影片制作公司认为方言片能迎合当地民众的口味,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摄制方言影片,这种唯利是图之举,罪实可诛。[21]563显然,这些举措和思想都与一些国语推行者主张“凡放映有声电影,表演话剧及广播新闻或讲演等必须采用国语,庶能普及人间”的观点不相谋合。
尽管广东粤语影片受中央政府以侵害“国语统一进而影响国家统一”为名而受到严厉打压的情形不能作为普遍例证,[22]但如此,我们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到在国语推广过程中某些方言文化的生存状态。虽然就国语推行的复杂过程来看,支持国语和方言并行发展者并不乏其人,如1943年3月12日在重庆举行的全国方音注音符号修订会议中,罗常培委员就认为国语务求统一,应该全国一致推行国音、国语,不必再顾方言,而吴稚晖则认为方言是自然存在的,即使将来国语通行全国,而各地方言仍会在各地老百姓嘴里应用,决不会归于消灭。由此可见,就是推行者之间也不见得有统一的观点。[23]但语言既需统一,以国家行政权力作为后盾,向社会推行国语就不可避免地对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地方”方言,以及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文化形式有所冲击和影响。据程美宝的广东地域文化研究,作者认为书写粤语是广东地域性文化的重要特质,在民间娱乐、传道、教育妇孺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广东人心目中,粤语写作是属于边缘地位的,而从民国以来的国语化运动,又让这种方言的发展处于一种受压制的状态。[24]111-163
三、 “国语”如何统一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国语和方言、方言文化之间如何共存,“国语”应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真正统一?1940年由于用上海方言演出戏剧《上海屋檐下》和《黄昏》而引起的一场方言剧、戏剧大众化和国语统一的争论让我们对这些问题有所管窥。
1940年10月,上海华光戏剧学校将吴天编的《黄昏》改用上海话演出,接着上海剧艺社也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用上海话演出了一天。对于这样的方言戏剧演出,在支持者看来是“给上海戏坛开来新的路,是值得纪念的”,[25]168而反对者“在很严肃的指责方言剧的不当”。[26]167不支持方言剧演出的有“如立人、幼明、赵致远、贝涣智、温士谦等诸先生”,他们认为“方言剧可以不必在上海提倡,因为上海在他们看来,现行的‘国语已可能为‘大多数人接受,所以方言剧的推行,他们以为还是到农村内地,或如幼明先生所说‘某种特别场合去推行来得适当些。”还有如幼明先生所说“我对于方言剧曾经是下过这样的定义:‘特殊场合下的突进手段……所谓‘突进手段,在目前说起来,是为了抗战间急于要用的手段。方言剧只能作为一种手段而不能作为戏剧大众化最终的目的,我不相信就如新如先生所说:将来的大众化戏剧就是用方言来演出的。”又如赵致远先生所说“起初为求观念来了解和发生兴趣,不妨用方言演出,但是到一个相当时间必须改用国语。起初我们为适应环境,不妨用方言演出,但是只能限于最初。”温士谦也认为“提倡方言剧是暂时的,并且只是限于在农村各个角落。它的使用时间是有限制的,最后还是要用‘国语,所以他不必也不应有独立的发展。”[27]169还有些人认为“方言剧会阻碍政府历年来所提倡的言语统一这一件工作之进行。”[28]162无独有偶,1933年的《山东民众教育月刊》刊登了一份和此次事件无甚关系的关于《民众戏剧语文,用国语好,还是用方言好?》(民众戏剧问题征答特辑)的调查表,在这份问卷回答表中,主张用国语演出戏剧的人,如陈治策认为“民众戏剧的对话应该用国语。这样子才会统一舞台用语。……这样有标准,统一的戏剧将来会产生国剧出来。”而卜少夫认为“应该用国语,这虽然在开创时期有些困难,但为来日的利便,我们不能图这一时的爽快。而且方言是窝藏封建意识的大本营,所以用国语还有统一言语与解放中国思想的意义。”[29]9卜少夫的回答已经将方言和封建意识联系起来,赋予国语相对的先进性。这些回答大致也能帮助我们了解那一时期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民众对国语、方言及其方言剧关系的认知。
此次方言剧争论的话题繁多,概言之,反对者认为上海话不好演西洋剧,上海多数人听得懂国语,没有必要用方言演出;而支持者则认为方言和方言戏剧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有的戏剧只有用方言来演才无损于戏剧艺术,方言剧运动是戏剧大众化,唤醒民众的有效方式,契合当时抗战建国任务的需求。但这一问题的深刻内涵已不仅仅局限于在现行的国语运动范围内(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国语运动”)来讨论方言戏剧和国语统一的关系问题,而恰恰是当时的国语运动本身已经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质疑,许多人对国语如何才能真正统一的未来语文建设之路提供了新的思路。正如思雨在评论这些观点时认为“当前的分歧点似乎是在方言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上,因为对于中国语言现实的估计有所出入,和对于未来中国民族统一语的形成看法不同,一部分人就自然而然有鄙视方言和抹煞方言的倾向,从这种倾向出发,也就产生了方言剧只是暂时用来辅助国语剧所不及的一种‘突进手段和方言剧只能在‘特殊场合演出并且只能演‘当地的事,当地的人等意见。”[27]169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以为将来的民族统一语便是现行的这种‘国语”的观点是否就具有自明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呢?国语的统一是否要依靠抹杀方言、抵制方言文化的生存空间才能形成呢?
方言和方言剧存在的价值。从中国的语言现实状况来看,这也是整个世界的语言现象,易贝认为,“戏剧的言是人的,戏剧的对象是人,人是有语言学上的分歧的(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那便是方言)。那么我们在戏剧中(在舞台上)也就要有,而且必然要有方言。很简单的,一句话解决了。”[30]157从维护戏剧艺术的需要来看,方言是维护戏剧艺术性的重要工具,而有些戏剧并不适合用国语来演说。雪影认为:“地方色彩本是增加文学的真实性的,我们已能发现以前的许多有价值的方言文学,而戏剧利用方言是合适的。所谓方言剧,不但是用某一种方言作说白,而且在这说白中是包括着这一种方言的各种特色的,如常用的语汇、虚字等,这样创造的戏剧因真实的地方性而有更高的艺术价值。”[31]161
方言剧是抗战时期戏剧大众化和社会宣传的必要,正如雪影所说,“为了达到大众化与宣传的目的,连文字也利用语言化的方言了,但是在直接利用语言宣传的戏剧上却反而用了不通俗的国语,这与大众化上岂非一大矛盾!所以方言剧是实在是必然而必要的趋势。” [31]161孔令境也认为:“要达到戏剧的完全大众化,自非目前所能做到,所谓提高群众对艺术欣赏的水平,也得在一般文化水平提高了以后,而一般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还得客观环境的变革,不过我们主观的努力,却也可以有若干的努力,方言剧的提倡,目的也就是帮助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在近年来后方的抗建运动中已经获得了不少的成效。”[32]165渔翁则认为,在“八一三”之前,时常有利用上海话表现话剧,在工厂里,或是在学校中。方言剧的应用,往往适用于特定的范围中,如往浦东工厂里去演,观众的对象大多数是浦东人,用国语演戏,有时不能使他们听得懂;而用浦东话演,反能使他们接受。而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到“农村去演剧”,引起了许多艺人的注意,而农村剧多半是利用乡民自己来演出的。那些流动演剧队,并且到处训练乡民自己来演方言剧,这些行动,无非是为了要更急速的达到宣传和教育的目的。[33]
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支持方言和方言剧发展的论者从中国语言现实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用方言演出戏剧的必然性;从维护戏剧艺术的角度提出用方言来演出戏剧的必要性;从利于戏剧大众化、社会宣传角度提出方言比国语更适合某些戏剧的发展,这也是方言、方言剧独立存在的价值之所在。
民族共同语形成的路径。希行认为,“要偌大的中国语言统一,这件工作决不是短期或规定一个时期所可能完成的,据语言学家说,这工作至少也得经过三个世纪以上的时期才能收效。而且,照这样,这一件统一工作还是发展得很不自然的。(虽然并不一定是要自然,但在其发展速度上确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如果要使语言统一其最重要一点倒还是先沟通各地的交通,组织交通网,利用这一个媒介体,而是各种不同的语言由经常接触而自然地统一起来,以这样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比要一个素来没有听过见过国语的无知民众,硬紧记牢一个字的发音比较迅速而合适吧?何况中国土地面积这般广袤。不使各地在关系互相多生接触,而先要使连隔两地的地方讲一种想同的话是合乎逻辑的吗?所以,归根说来,实际上方言剧对于国语并不存在有破坏或阻碍性。”[28]162陈企丹也认为“无论对于演剧演说或写作,我们不必反对大家学北平话,也不必反对大家学任何其它方言,更不必想一味用人工方法强使方言消灭或使某方言发扬,而应以实用为主要条件来随时随地决定采用哪方言自然发展。乃至教育普及,交通便利之后,各方言自己会在优胜劣汰的天演定律之下决定其生灭存亡的命运,而真正的中华民族统一语也会在这种场合下,混合升华而生,则此‘标准也不立而立了。”[34]167孔令境认为我们对于国语运动的正确理解应是:“现在一般方言剧反对讨论者,动不动就说方言剧的提倡是破坏国语的统一的。我不知他们头脑中的国语统一运动是怎么做法的,我以为要使国语统一,最要紧是发展和加强全国的联系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是全国达成一片,能够达到这一步的时候,言语的隔阂自然会渐渐消除了。”[35]165
思雨的观点最具有建设性和代表性,他认为:“我们虽然也一样热烈主张消灭方言,统一语言,但是我们决不把现行的名义上是‘国语实际上是‘准北平方言的‘国语看作未来中国的民族统一语,而且我们也根本反对用一地方言来统一全国的办法。”而以瞿秋白为代表的方言拉丁化运动所主张的语言统一化之路则是未来中国民族共同语形成的方向和路径,这个方向和路径就是:
“‘发展方言来消灭方言,也就是所谓‘欲合先分的办法,认为只有高度的发展方言,是各种方言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淘汰旧的沉渣,发挥原有的潜能,一方面吸收新的成分,然后再利赖了客观条件的具备,如生产交通等的发达,使各种方言在口头上的接触机会增多,以及人为的改造,如方言文字的建立和各种语音语法语汇的对照表或字典等的创制,使学习方言的便利性增大,而各种方言在书面上的接触也增多。这样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全国人民的生活内容渐趋于统一,一方面由于各种主观的努力,方言便将自然地而又人工地和合成为最高阶段的民族统一语,这一种统一语才是有血有肉的真正的统一语,不是现行那种只统一了一个表面的‘国语所可比!”
他以为以准“北京方言”作为国语只能代表“北方”,而不能真正代表“国家”、“民族”,各地方言应该平等发展。“我们主张发展各种方言的方言剧,也一样不反对发展这种‘北方普通话的方言剧,各种方言的方言剧的必须发展,就像‘北方普通话的方言剧的必须发展一样,而各种方言的方言剧消灭的时日,也便是现行的‘国语的消灭时日,现行‘国语剧不消灭,各种方言的方言据也绝不会消灭。他们将共同向前发展,直到中国有了真正的民族统一语为止。虽然,这种真正的民族统一语便是在它们——各种方言和现行的‘国语——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让步、吸收、溶化而合成的。”[27]170-171
方言和方言剧的支持者显然认为民族共同语决不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形成的,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各种方言自然融合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并继而从这个理论角度来对现行的以北京语为标准语的“国语”和以依靠政令来推行的国语运动的合法性进行了质疑。在这种论调下,“国语”和方言都是平等存在和发展的,而方言剧、方言的存在就不会对当时的“国语”有任何的破坏和阻碍性,反而有助于未来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实际上,在20世纪30、40时代,在中国语文改革和民族共同语如何形成的问题上,承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遗续,相继引发了大众语、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之间的相关争论,[36]前文所示争论正是在这一大的社会环境下展开的。在实践方面,当时由左派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发动的新文字拉丁化运动对社会影响较大。和南京国民政府开展的“国语统一运动”不同,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倡导汉字、方言拉丁化的左派知识精英并不认同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以北京方言为主的国语运动,他们认为这种依靠政治行政力从上到下的国语统一形式,违背了语言依靠社会发展的自然统一化之路。拉丁化新文字者认为只有废除汉字,彻底实现民众口头语言的拉丁化,普及教育才有可能,而真正的民族共同语也只有在各地方言充分发展的基础才能形成,此所谓“欲合先分”。这一时期的拉丁化新文字也先后在上海、北平、天津、太原、开封、西安、重庆、汉口、长沙等地得到研究和实践。[37]
综上所论,近代中国语言改革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以故它的复杂性不仅表现为各派观点的迥异,其间也掺杂着党派意识形态方面的隔膜和对立。但这些争论共同的指向大多可以归结到近代中国唱响已久的主题——民族启蒙与救亡,所不同的是将要采用何种方式来唤醒中国。而这其中,作为各种启蒙思想传播的载体——语言文字就成为了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和文化势力争相改革的对象。
(本文曾得到南京大学历史系陈蕴茜副教授的精心指导,特此致谢。)
注释:
[1]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民国丛书(第二编52),上海:上海书店,1934年影印版。并可参见崔明海:近代国语统一运动研究[Z]的第二章“国语政策制定与师资培养”,第三章“国语的社会推广和宣传”相关内容,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7年5月未刊稿.
[2] 清世宗实录[Z]卷七十二.
[3]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M],俞正燮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6:369-370.
[4]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1892年),清末文字改革文集[C],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3.
[5] 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氏谈片(吴振麟录),吴汝纶:东游丛录[M],日本:三省堂书店,1902年:96.
[6] 吴汝纶:与张尚书[C](1902),吴汝纶全集(三),合肥:黄山书社,2002:436.
[7] 长白老民:推广京华至为公义论[C](1903年),北京: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958:34.
[8] 何凤华、王用舟等:《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1903年)[C],北京: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958:36.
[9] 蔡元培:国语的应用[J],国语月刊,第1卷第1期,北京: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编辑,1922:3-4.
[10] 周光:日本长崎华侨国语消息[J],国语月刊,第1卷第8期,1922.
[11]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M],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8.
[12] 新:国语与国体之关系[N],申报,1923-5-30(3).
[13] 张国人:统一国语[J],中央半月刊,第2卷第2、3期,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行,1930:50-58.
[14] 蔡元培:三民主义与国语[C](1930年),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1288.
[15] 潘公展:国语教育与唤起民众[J],上海市教育局教育周报,1935,(284):2.
[16] 罗重民:国民之统一与国语之统一[J],学艺(第二号),丙辰学社,出版日期不详:7.
[17] 金以林:从汪胡连手到蒋汪合作[J],近代史研究,2003,(1).
[18] [澳]费约翰着,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M],北京:三联书店,2004:238。(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呈现出一种新旧杂成的局面,民众的国语观念的形成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政治、经济中心到穷乡僻壤,在新/旧观念冲突之间,诸多精英固守传统的文/野、雅/俗观念,对国语白话文的推广多有反对,以保存文言和读经传统。而普通民众对国语的认同与否,不但受各地方言文化的制约,更受地方文化精英和社会主流风气的影响,从实用性角度排斥国语。这种实用主义语言价值观实质上反映了民初文言和白话在社会通行上,国语白话还没有取得对文言的绝对优势。参见林志宏:社会和情感的交互作用——清末民初文言与白话地位的逆转[C],胡春惠等编: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变迁(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2003年。崔明海:近代国语统一运动研究[Z]的第四章“语言统一视野下的国语与方言问题”相关内容,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7年5月未刊稿.)
[19] 平凡:电检会取缔不良电影,方言声片和歌舞影片的厄运[J],电声(上海),第3卷第38期,1934:744.
[20] 电检会订定整理华南影业办法,摄制方言声片严重处罚,粤语影片重加检查得暂放映,国产影片运粤今后关税豁免[J],电声(上海),第6卷第2期,1937:159.
[21] 我们的话:方言的声片盛行[J],电声(上海),第3卷第29期,1934:563.
[22] 电影片检查标准[C](1941年),行政院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编报的禁映影片一览表[C](194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Z](第五辑第二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79.
[23] 全国方音注音符号修订委员会会议报告[C],国语教材展览目录及国语发稿簿等文书[C](1942、1948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Z],案卷号:5-12295.
[24]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2006:111-163.
[25] 陈鹤翔:方言剧[J],中国语文(上海),第2卷第3、4合期,1941:168.
[26] 陈企丹:国语与方言[J],中国语文(上海),第2卷第3、4合期,1941:167.
[27] 思雨:谈谈几种对于方言剧的不同意见[J],中国语文(上海),第2卷第3、4合期,1941:169.
[28] 希行:也来谈谈关于方言剧[J],中国语文(上海),第2卷第3、4合期,1941:162.
[29] 民众戏剧语文,用国语好,还是用方言好?[J],山东民众教育月刊(济南),第4卷第8期,1933:9.
[30] 易贝:谈方言剧的语文建设性[J],中国语文(上海),第2卷第3、4合期,1941:157.
[31] 雪影:从拉丁化新文字谈到方言剧[J] 中国语文(上海),第2卷第3、4合期,1941:161.
[32] 孔令境:论方言剧与戏剧大众化及国语统一运动[M],中国语文(上海),第2卷第3、4合期,1941:165.
[33] 渔翁:谈方言话剧[N],申报,1940-11-28(3).
[34] 陈企丹:国语与方言[J],中国语文(上海),第2卷第3、4合期,1941:167.
[35] 孔令境:论方言剧与戏剧大众化及国语统一运动[J],中国语文(上海),第2卷第3、4合期,1941:165.
[36] 有关文言、白话、大众语的争论可参见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M],上海:启智书局,1934年影印版;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语论战[M],民国丛书(第一编)(52),上海:上海书店,1934年影印版;文逸编:语文论战的现阶段[M],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影印版;聂绀弩着:语言·文字·思想[M],民国丛书(第一编)(52),上海:上海书店,1937年影印版.
[37] 倪海曙: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M],民国丛书(第二编)(52),语言文字类,上海:上海书店;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M],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8;胡绳: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M],大众出版社,1936;叶赖士:拉丁化概论[M],上海:天马书店,1935.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