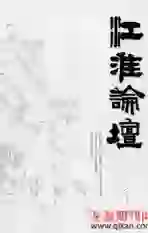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2009-02-26何刚
何 刚
摘要: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各方论战者从理论引用、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古代社会性质的确定等方面对郭沫若古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论战中包含着合理科学的学术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郭沫若古史研究的修正和完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本文力图侧重于从学术史的视野叙述郭沫若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从而部分还原其被遮蔽的学术面相。
关键词:中国社会史论战; 郭沫若; 马克思主义史学; 学术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志码:A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论战刚告一段落时开始,对它的总结和研究就已经出现。迄今为止,过往研究多从此次论战中十分显见的革命话语和政治背景出发,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的论争,过多地强调和阐释论战的政治和革命意义,忽视和遮蔽了其本有的重要学术史意义。其实此次论战的各方无论被划入哪一政治派别,他们都奉唯物史观为圭皋,采用的都是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时期,则是唯物史观派的一统天下,是唯物史观的一次大爆炸、一次大阅兵”[1]。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推动了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阐释与应用、历史材料的考辨等方面的进步,逐渐修正和发展了各自的史学主张和体系。
同时,从当时的论战文章本身来看,中国社会史论战并非如以往所认为的“完全不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全然没有学术可言,而是“仍然保持了一定高度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论战者中更不乏在当时中国思想学术界具有重要分量的人物,“讨论者态度的严肃基本保证了这些讨论的学术水平和科学性质”[2]。随着论战的展开和深入,特别是在1931年后,一些论战参与者改变了之前主要为了迎合现实革命分析的需要,开始转向了历史本身的研究。当时参与论战的学者之一——王宜昌也将此时的论战和唯物主义史学划入到更具有学术水准的“研究”阶段。无疑,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继起的直接针对他的许多论战文章和评论也大致应在此列。同时,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此次社会史论战的焦点之一,针对他的各方论战文章也非常多,许多论战者更是在直接批判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古史观点。
所以,在上述考虑之下,笔者将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视为一个学术史的课题,从学术史的视野进行考查,全面评述各方论战者对郭沫若古史研究的批评和学术主张,希望能梳理出这场激烈论战所包含的科学合理的学术成分,从而部分还原其被遮蔽的学术面相。
在研究方法上,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些论战者,过去多从政治思想和派别的角度,将其分为新潮流派、动力派和新生命派等。然而,具体到他们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主张时,我们会发现,这种划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即使是同一派别的人,他们的主张往往相差悬殊,甚至背道而驰。比如在奴隶制问题上,同是中国托派,杜畏之等人否定,王宜昌则对之完全肯定。所以,如果采取分别叙述各论战派别的中国古史观,及其对郭沫若古史研究评述的做法,结果只会是漫无边际,愈说愈乱。本文拟按照论战讨论的几个主要内容来划分论战者对郭沫若的批评,然后分而述之。何干之在1937年将论战内容进行了总结,认为其不出乎三点:(一)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什么,中国会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二)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完全相同?(三)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是怎样?[3]前记2各方论战者对郭沫若的评述也大致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
一、摩尔根与“亚细亚的”:对郭沫若理论范畴运用的批评
美国左翼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将论战者对郭沫若的批评大致上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更为理论化的批评”,主要关注郭沫若的历史分期观、他对于社会形式的理解和他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理论范畴的应用;二是将批评的矛头具体指向郭沫若对历史资料的阐释上。这两种类型在绝大多数批评者那里并没有截然分开,而是相互掺杂在一起。其中论战者对郭沫若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概念范畴时所表现出来的“机械主义”,无不提出了广泛的指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秩序,“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直接引用这段话,接着说:“他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的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4]正是严格按照这一演进规律,郭沫若开始了中国历史系统论述和阶段划分。
批评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类型只是一个总体上的陈述,马克思并没有认定所有社会形式都是普世的,也并没有明确要求一定要按照他所叙述的顺序排列。相反,在郭沫若那里,他的分析和对中国历史的划分就是建立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演化都是同一的假设之上,“觉得这个公式是历千古而不变,放四海而皆准的。于是中国的历史只好跟了他所误解的公式而发展了”[5]。
众多论战者就郭沫若对摩尔根关于家族结构演进观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先史民族之进化阶段”表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以此来说明郭沫若引用理论时的武断和错误,并由此带来的在理解认识上的严重偏差。程憬和李季的批评最具代表性,在他们看来,“觉得这个表差不多是出于郭君的杜撰,和摩根的意见相差甚远”。第一,认为郭沫若把史前时期——蒙昧时代均划为“女性中心”的“杂交时代”。将杂交时期延伸到整个蒙昧时期的做法,混淆了家族组织之间的关系,太过轻率武断,因为“杂交”与“群婚”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二人指出郭沫若认为整个氏族社会都是以母系为中心,将“固定的夫妇”制、“男性中心”的先史划出氏族社会之外,完全放在国家形成的阶段之上,从而将氏族社会和母系制度等同起来的做法,也是不符合摩尔根将氏族社会分作“女系”和“男系”两种的观点,严重偏离了摩尔根的理论模式。程憬他们指出,氏族组织包括母系和父系两种形式。所以,总的来看,“此书的图案恰和他的形态一样,也是由两种东西杂凑而成:即经过伪造的摩尔根的‘先史民族进化阶段表和已经废弃的马克思的经济发展分期说。此书所根据的前提既不正确,则其所演的结论,谬误百出,是势所必至,不能幸免的”[6]201。
如何看待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社会”这一概念,是论战中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批评者承认马克思早期确实曾把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和亚细亚社会视为同一,但是在获悉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视它们为不同的范畴。所以在李季等人看来,郭沫若“不独对于马氏意见的改变毫无所知”,并且“认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这是显而易见的错误”,“把整个的殷代看做氏族社会,便是一种绝大的错误”, 认为这是郭沫若对于马克思“孔趋亦趋,孔步亦步”,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把自己套在马氏的方式里面的结果。[7]李季虽然也采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言中的分期模式,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置于历史发展的早期,但是他不同意郭沫若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同于氏族社会。他视土地国有制为亚细亚社会的最显著特征,他认为这一阶段只有在社会发展超越了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后才能实现。受普列汉洛夫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影响,李季强调,因各自地理环境的不同,东西社会演进模型也不一样,在“东洋社会,亚细亚生产方法,就是氏族社会的承继者”,而不是奴隶社会。[3]65-66那么在李季看来,中国是在什么时期进入了亚细亚社会呢?他“毅然相信夏殷两代相继经过这个局面(即亚细亚社会——引者按)”。之所以有如此自信和坚决,是在于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信教式地盲从马克思,而是因为有了某些特别原因,从氏族社会发展到土地国有,和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有了这个步骤,西周的封建制度才不嫌突如其来”[6]182。可见,李季等人同意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有过一个完整独立的历史发展时期,但他们反对将其等同于中国的原始社会阶段。他们认为中国的亚细亚社会存在于夏商时期,从而在理论范畴上拒绝了中国有奴隶社会一说。
现在,学者们认为,承认东方的古代社会具有不同于“古典的”古代社会的特点,其实才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亚细亚社会作为全球社会发展的普适性一环来加以认识。[8]而郭沫若却完全参照社会进化五阶段论的框架来安排“亚细亚社会”的历史位置,完全忽视了东方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社会之间的区别。此次论战中的各方批评者虽然确实预设有各自的政治意图,然而,仅从学理层面上讲,他们对郭沫若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上的公式主义错误,忽视东西方社会差异和特殊性的批评,也绝非空穴来风,无的放矢。相反,他们倒是提醒了大家要注意这种社会差异和特殊性,然后再来理解和安排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各方意见长期分歧,难以取得共识,后来的讨论也多是早前有关看法的重复。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这场社会史论战的一个主要的,也是首要的论题,它承接日本、前苏联等海外论争的影响,贯穿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始终,以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史研究。进一步讲,也正是这场讨论曾经有力地推动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例如,认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不能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的侯外卢,就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理论依据,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实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9]。
二、商代是什么社会?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黄帝以来的五帝和三王的祖先的诞生传说,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根据文献资料和卜辞的记载,他认为商代也“还是一个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
在众多批评者看来,郭沫若过低地将商代定位在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是无法让人信服和接受的。他们或从自己理解的人类社会演进序列出发,或如郭沫若一样,做古书文献的考证,指出商代社会的发展水平早已超过氏族社会的阶段。
李季就认为,郭沫若“对于殷代和周国的祖先时代的描写与批评,完全不正确,完全谬误”。因为郭沫若认为殷代只“达到野蛮的中级,至多也不过达到高级的初步”,但是,继之的“周代则于数十百年中急剧穿过野蛮的高级而达到文明时期”,这种跃进式的演变显然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渐进规律,“倘若周初有一个文明国家与之并立,因受其影响,遂急转直下,这原是可能的”。同时,李季在将周代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提下,认为在发达的封建社会之前竟然是野蛮时期的原始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武王克殷,大封同姓王和先王之后,这是周代封建制度的正式开端。然没有封建诸侯的底子存在,决不会有封建制度的出现”[6]179-180。
王伯平虽然同意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的“中国历史应从殷代开幕”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之开端是在殷代”。但是,他显然不同意郭沫若“殷代还是原始社会末期”的过低评价。王伯平认为根据安阳考古发掘的结果看,殷代“已有了完备的象形文字”,并不是如郭沫若所说的产生还不甚久,还在形成的途中;他断定殷代应为铜器时代,而郭沫若认为殷代是金石并用的时代的观点是不对的。同时,王伯平接着说:“殷代的生产已有了超过需要的可能,再加之以奴隶部分的发现,我们可以断定‘社会的不平亦已发生。所以氏族制度逐渐解体,盖成为不可争论的事实了。”在文化上,王伯平甚至认为,殷文化高于周,周在文化上承续了殷。[10]王伯平能较早地利用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来论证中国古代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其在批评郭沫若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关于殷商社会性质的结论也有合理之处。
李麦麦则指出,根据考古学的知识,远在二十万年以前原始社会已经出现。虽然中国的原始社会是否在二十万年前或后出现,现在不得而知,但是,“想来在‘金石并用和‘已有文字的商代该不会是原始共产社会吧?”“商代既是‘畜牧盛行时代、‘农业已经发现时代,为什么商代还是原始共产社会呢?”同时,李麦麦认为,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的社会中间还间隔两个社会——氏族社会与封建社会,“原始共产制的社会转变为奴隶制的社会,这也是我们从未听过的”。所以,他强烈质疑郭沫若关于商代的论述。
接着,李麦麦根据《诗经·商颂》的“长发”、“殷武”诸篇来反驳郭沫若的观点,《商颂·长发》说:“玄王恒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 。”《商颂·殷武上》有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李麦麦据此认为,这两首诗都道出汤有天下之后,是采取分封授土的形式。这些证明商代:“(1)不是原始共产制;(2)不是氏族制;(3)更不是原始共产制向奴隶制推移。”最后,李氏认为:“商代是中国封建制度起源时代,氏族制在商代只有孑遗形态。”[11]
程憬则对郭沫若称商代为氏族社会的三点论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郭沫若的三点论据:一为商代王位继承的“兄终弟及”,二为商人的“尊崇先妣,常为先妣特祭”,三为“在殷代末年都有多母多父的现象”。程憬认为,这些都无法证明商代“母系制”社会性质,并一一作了反驳。程憬指出,第一,郭沫若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有区别的看待和利用文献记载,借重历史上已经有了的关于“兄终弟及”的文献记载,而认为文献上同样也记载有的“父子关系”“亦不必便是真实的”!而且在郭沫若认定为封建社会的时代(如晋朝)中也有“兄终弟及”的事实,为什么不说晋朝那时也是母系时代呢?第二,商代的“先妣特祭”诚是事实,但据此不一定能推出“母权中心”时代的结论,因为王襄又说:“商则诸妣无不特祭,与先公先王同。”所以根据“先王先公特祭”,或也能推出商代是“父权中心”的结论;第三,郭沫若自己也承认,“亚血族群婚”是母系氏族社会之“现象或其孑遗”,程憬便问,既然是“或其孑遗”,那末,殷代(尤其殷末)怎么还是“母系时代”?他甚至将郭沫若“时代犹有留存”之语接了下去,说:“各地报纸的社会新闻栏中,常见有‘一人而御三女,四女,甚至五女。‘此犹是杂交时代之孑遗!”以予讽刺。[5]
由于上古史资料多是神话传说,加之缺乏考古材料,以上各家并没有做详实的论证工作,他们的观点多是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从已有的文献记载出发进行论述,反对郭沫若将殷商定为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的过低估计,大多认为殷商时代已进入到奴隶社会或其它高级阶段的社会形态,其观点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对郭沫若的批评应该说也是切中了要害,他们将殷商时期定为奴隶社会(或者其它高级社会形态)的主张无疑对后来殷商社会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启发。稍后参与社会史论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利用考古发掘的材料和古籍有关传说的记载,并结合现代民族学资料,在1933年完稿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这部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开拓之作中,即论证了夏殷时代是奴隶制社会的观点,成为古史论战中独树一帜的古史观,并逐渐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接受。郭沫若后来也对殷代的社会性质不断地进行认识,修正自己的观点。在1941年12月,他发表《由诗剧说到奴隶社会》一文,正式抛弃了自己的旧说:“我以前把殷代视为氏族社会末期未免估计得太低。现在我已经证明殷代已有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存在了。”1942年2月,他在《屈原研究》中更明确表示:“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这一层近来已得到一般公认。”4月,他又写了《殷周是奴隶社会考》专文。最后,在1945年发表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和《青铜时代》中对殷代为奴隶社会的观点作了系统的阐述。
三、西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
在郭沫若之前,中国人大致上还是从“封建”一词的古典政治含义,即“封诸侯,建藩卫”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认为自西周开始,中国便进入了封建社会,继起者才是奴隶社会。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的普遍认知。“中国的封建社会,大概是发轫于夏代,至周初算是繁荣到极端了,可是其命运亦于周末衰歇。”[12] “无论怎样说法,中国封建制度最完整的时代是周,这是谁也承认的,到了战国,封建制度已从根本上破坏。”[13]在社会史论战中,据何干之的观察,参加论战的“老将”或“新兵”,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奴隶社会的否定论者。
所以,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的“西周奴隶说”,无疑是一根本反叛。“西周时代的社会本极明显,是完全封建的,但近来有许多异论,最著的仍为郭沫若先生,他以为西周是‘奴隶社会。”所以,在此次论战中,“附和他的人极少,而反对他的人却极多”[14],人们对郭沫若的批评便集中于此。针对郭沫若古史研究的最早评论文章《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质疑》即是代表。作者周绍瀛说,郭沫若“其要点是以中国生产的进展,去分析吾国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和其思想,这种研究的手腕,并非我怀疑的所在。但其研究的结果的解释,实有不能使我无关”。周绍瀛认为:“照着他的结论看来,以为王道(即周之统一)的基础,为奴隶制,霸道(即春秋战国以后)的基础为农奴制。故以为奴隶制发生于封建制之前;而农奴制发生于奴隶制之后。他的见解,适和我相反。我以为奴隶制,为封建制度摇动后之产品;而封建制度的发生,即在农奴制发生之际,所以说王道(即周之统一)的基础,为农奴制;霸道之基础,为奴隶制。至若我所解释的,也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事实,而加以分析的。”[15]
由于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未能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界定,因此,无论是郭沫若,还是他的批评者,都是根据自己的标准来理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王宜昌在稍后的总结中就敏锐地看到:“他们在纯理论上没有充分的论证,以否认古代奴隶社会之为历史的必然阶段,又没有充分事实证据,以证明中国社会没有奴隶社会的发展。分不清楚封建制度与奴隶制度的理论来否认郭沫若的奴隶制度理论。”[16]正因为如此,时常出现根据同样的证据却得出截然相对的结论的情况。难怪李季曾说:“现在总括起来,郭君企图证明西周为奴隶制所举的种种证据,没有一种是能够成立的,不独不能成立,并且时常举出很显明的封建制度的证据去作奴隶制的证据。”[7] 因此,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存无以及年代划分的争论,在论战中表现得尤为激烈和复杂,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着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与讨论。
在否定奴隶社会一营中,李季针对郭沫若的“西周奴隶说”做了文献论证,他说,既然郭沫若叫“我们不要为文字所拘泥”,那就先考查文字,看一看这个“古时……号称为封建”的周室到底有无封建制度的存在。他根据《吕氏春秋》和《史记》的记载,认为西周显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封建社会了。《吕氏春秋·观世篇》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国”,李季说:“这种说法与事实虽未必丝毫不差,然决非完全向壁虚构,我们即‘不为文字所拘泥,拿他打个对折,也可以窥见周初的封建制度是盛极一时。”[6]182-183
王伯平是在对郭沫若的《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批判》的批评中阐述自己的古史观的。他也属于否定中国奴隶社会存在的阵营。他说:“郭先生以为易经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时代,以易经时代社会结构的特点说,确是一个过渡时代,但不是由原始共产社会向奴隶社会推移的一个过渡时代,而是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推移的一个过渡时代。”然后,他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考察论证。[17]他还从批评郭沫若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错误的角度,来否认中国奴隶社会之存在。他戏称:“郭沫若君的书是穿着马克思主义衣服出现的,对于读者是极有害的。”王伯平指出,古代罗马的封建社会是由奴隶制度转变来的,但是这殊不能作郭沫若之“奴隶制度变成封建制度”论断之根据。同样,双方对封建社会的界定相差悬殊,所以,虽然王伯平也承认在氏族社会末期就有奴隶的发生这一现象,在卜辞中也可以找到佐证,但是,按照他的理解,奴隶的存在恰恰证明的是封建社会的存在,因为“奴隶在社会上成为一个严重现象乃是封建社会中才有可能。奴隶制度不能列作一个社会进化的独立阶段,可是郭沫若就犯了这个错误”[10]。
与气势颇盛的否定奴隶社会主张相比,在社会史论战期间,肯定中国奴隶社会存在的观点则要势单力薄得多。具体到对郭沫若的评论上,他们大多肯定郭沫若对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论证,但是却不赞同其将中国奴隶社会划定在西周,认为自东周以后甚至更晚,中国才开始进入奴隶社会。
王宜昌也主张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并将其存在时间划定在夏代至三国时期之间。他说,“中国奴隶社会由半开化末期的夏代发展,经过文明时代初期的西晋而灭亡。”在《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这篇恢宏然而冗长琐碎的力作中,王宜昌罗列了大量文献资料,试图构建自己的奴隶社会学说体系。所以,针对郭沫若的西周奴隶社会说,王宜昌说:“郭沫若从卜辞等证明商代已有奴隶之起源,而西周为奴隶社会,是对的。但说东周以后,开始了封建社会,那是错的。我们会从秦汉社会生产的分析上来证明秦汉之后为奴隶制度的古代社会,和从罗马底比较上来证明秦汉是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的变化和消灭,即其没落,是在秦汉以后,而不是在秦汉以前的东周。”[16]陶希圣原本对奴隶社会采取回避态度,以为中国自有神话传说以来,一直至清末鸦片战争以前,都是封建社会。后来学者曾把他列为否定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见解屡变”的陶希圣也没有明确反对过奴隶社会的存在,而且在1932年发表《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反对认为“中国三千年之久不变”的“永久封建论”,明确肯定奴隶社会的存在,他说:“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其中的主要阶级是奴主与奴隶”,“中国社会发达过程与欧洲大同小异。由氏族的生产到家长经济、奴隶经济、封建的生产、城市手工业即先资本主义。”[18]最后,与王宜昌大致相同,陶希圣将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制的确立断在魏晋。所以,王宜昌和陶希圣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后来八种“封建说”中“三强”之一的魏晋封建说的理论先导。
在社会史论战中,论战各方都坚称自己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极力证明论敌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以起到釜底抽薪的论辩效果。所以,争辩双方大多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用公式去推论历史。表面上热闹的你来我往的理论大战其实是真正理论的缺失。然而,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自觉和努力下,这种理论争执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实则促成了对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的深入探索。“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刺激了历史研究工作,到了30年代中期,已经对于‘范式的(normal)历史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186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此次社会史论战本身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郭沫若的古史研究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完善。
首先,论战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深入地思考史学理论的建设,纠正此前在理论的理解和方法的运用上的不准确。这些成果主要有何干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以及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著作。翦伯赞就说,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正确的哲学,作为分析认识以至批判的出发点”,所以,“为了研究中国社会的形势发展史的问题,历史哲学是必要的。方法问题也是必要的”,所谓方法,就是“史的唯物论”。[20]郭沫若也开始纠正此前的公式主义倾向,到了30年代中期以后,与以前的著作相比,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援引也显得不太起眼。[19]135其次,除了理论建构之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料整理的工作上也取得了极大成就,而这当以郭沫若为代表。此时的他已公开宣称:“只要经典文献与考古所获材料有所冲突,则无论如何它们都无甚价值了。”[21]再次,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郭沫若于30年代晚期、40年代初期“修正自己的旧说”与社会史论战中批判者的指责有必然的联系,然而,这些尖锐的声音和意见应该是给了郭沫若提醒和启示。而且从实践上来看,郭沫若后来的一些修正确实是针对批评者此前所指出的某些问题而进行的,并逐渐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古史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1] 王学典.唯物史观派的学术重塑[J].历史研究,2007(1):12-18.
[2]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64-68.
[3]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论战[M].上海:生活书店,1937.
[4]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上海:现代书局,1932:176 .
[5] 程憬.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J].图书评论,1932,1(2):7-17.
[6] 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M].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
[7] 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J].读书杂志,1932(2、3):1-150.
[8] 杨念群.导论:东西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C].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75.
[9] 刘宝才.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J].中国史研究,2003(2):17-26.
[10] 王伯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发轫[J].读书杂志,1932,2(7、8):1-23.
[11] 李麦麦.评郭沫若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J].读书杂志,1932,2(6):1-30.
[12] 雄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M].上海:昆仑书店,1929:211.
[13] 易君左.中国社会史[M].上海:世界书局,1935:84.
[14] 梁园东.中国社会各阶段的讨论[J].读书杂志,1932,2(7、8):1-41.
[15] 周绍瀛.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质疑[J].读书杂志,1931,1(4、5):1-28.
[16]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J].读书杂志,1932,2(2、3):1-71.
[17] 王伯平.易经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郭沫若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批判[J].读书杂志,1933,3(3、4):1-26.
[18]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J].读书杂志,1932,2(7、8):1-9.
[19] (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0]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3.
[21]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76.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