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贻白:胡同里的戏剧大师
2009-02-13韩晗
韩 晗
他曾凭借《中国戏剧史》执中国戏曲史研究之牛耳,却一生饱经磨难,多次深陷囹圄,中年竟靠出卖自己的藏书维持生计,但是,他毕生矢志不移地钻研学术,始终未曾放弃自己的学术信仰。
他曾经参加过北伐战争,参加过上海滩上的左翼文学与左翼戏剧阵线,又在新中国成立前毅然从香港回归,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他临终前却被称之为“反动学术权威”。
他出身湘剧演员,既没留洋,也未读过大学,却凭借自己的勤奋与努力,在而立之年以后不断抛出了一部部话剧、电影和学术专著,蜚声剧坛。由巴金创作、他担任编剧的电影《家》在半个世纪之后仍能入选中国50部经典电影;20世纪40年代即与钱穆、钱基博、夏承焘等学者一道,被上海复旦大学等聘为讲座教授,但是,在他逝世时,讣告上竟以“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头衔冠之……
他就是周贻白,这个本不应该被忘记的戏剧大师。
名师高徒
“他在屋里憋了三年,靠卖旧书过日子,每天只吃一碗馄饨。最后,他终于写出了《中国戏剧史》。”
这是2005年4月21日《南方周末》登出的一篇采访。被采访者是戏剧史家周华斌,文中的“他”,就是周华斌的父亲、中国戏剧史研究的先驱周贻白。他的《中国戏剧史》的不同版本,近年来分别被收入了上海的“世纪文库”和湖南的“湖湘文库”。
“卖旧书”,乃是卖自己的藏书,这绝非是故意“夸穷”——尚有买书者为证。一位学者曾在一篇文章中作如是回忆:自己当初在无锡当小学老师时,常在旧书店买到扉页上有“贻白藏书”印章的旧书,一打听,卖书者不是别人,正是著名学者和编剧家周贻白。
这位年轻的小学老师因为被卖的这些旧书上的名章,激发了对周贻白的兴趣。他开始主动打听关于周贻白的信息,了解到“周先生生活很困难,经常卖书度日”,于是对这位声名卓著的学者油然产生了敬意。1946年,这位年轻的小学老师凭借一股子韧劲儿和对学术的热情,考上了周贻白执教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
这所学校因钱基博(钱钟书之父)、章太炎、钱穆、周谷城、胡曲园、陈衍、朱东润、夏承焘、饶宗颐、周贻白等学者的执教而被当时的学术界称为“南清华”,与这个年轻人同窗就读的还有日后成为“南北二钱”的钱仲联、上海大学校长的钱伟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文学史专家蒋天枢以及南京大学教授陈中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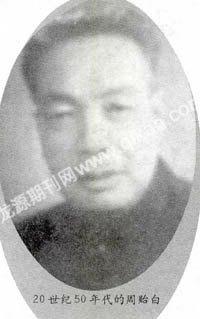
名师高徒,前面一串学者的名字,继承着从桐城派到五四再到当代的文化传统。但是随后的年轻人,在当时的无锡国专都穿着一样的粗布长衫,抱着字典与课本,穿梭于教室与宿舍之间。生活朴实而单调,仿佛除了学问二字,别无其他。
但是,这个年轻的小学老师却对学问有着比别人更为浓厚的兴趣,他不止一次地与同学敲开周先生的房门,向周先生请教各种问题。那时这位小学老师还年轻,有着冲动的学术理想,而正在埋首奋笔的周先生却并不因为这些学生的贸然打扰而有何怠慢。周先生待人“坦率诚恳”,“常常放下手里正在写作的工作,与几个学生谈做学问的事”。
后来,“伯乐识马”的周贻白将这位好学的学生引荐给了当时中国戏剧界的前沿人物——田汉与洪深。照此发展,原本这个年轻人可以成为中国戏剧界的专家,但是却因学生运动而被迫退学,周贻白也因政局变动去了香港。待到1954年,两人再次重逢,周贻白仍然是闻名全国的戏剧史专家,但这位年轻人已到中年,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年轻讲师,主攻方向是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学。
小学老师不是没有成长为大师的可能。虽然周贻白早已过世卅载,但这位当年的年轻人却未负周先生的厚望,现在已名扬海内外。凭借当年无锡国专群星璀璨的诸位学者打下的学问底子,凭借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与对敦煌学的深刻见解,这位小学老师成了当代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文化学者之一,而且先后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名誉院长——冯其庸,周贻白真正意义上的学生。
人民作家
说周贻白是一个学者,是因为他在学术上自成一家,并具大家风范。其以文史研究为纲、场上研究为目的戏剧史理论体系,早已被海内外学术界所认同。同时代的张庚、郭汉城、傅惜华等学者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众多学者无不沿着与周贻白同样的路子,进行着戏曲史的深入探索。
说周贻白不止是一个学者,是因为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作家与社会活动家。他不满日本人为中国戏剧编史立传,宁肯自己卖藏书、每天只吃一碗馄饨也要立志写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的戏剧通史。他左手做理论探索、整理古籍史料,右手搞文学创作,独立编剧二三十部。而且,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南国剧社、北伐战争、海员工会、左翼剧坛都有他的身影。作为作家的周贻白是成功的,作为爱国学者的周贻白是实至名归的,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周贻白是不孚众望的,这是那个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的写照。
这是一群文化先行者的群像,他们经历了我们未曾经历过的涅。
中国现代学术史中的周贻白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他的作品富于个性与多样性。他对历史的精通和不乏幽默诙谐的语言,让我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一书中不断地击节叫好、拍案称绝,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尤其书中对于三国的历史评论,可以这样说,当今很少有学者能够达到周贻白所领悟的境界。他的《中国戏剧史》讲座更是深入浅出,不落俗套,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雅俗共赏。

做学术著作尚且如此,做戏剧创作更不必说了。《北地王》、《李香君》、《风流世家》、《花花世界》……这些在上海、重庆乃至全国不断上演、出版的作品,很快在平民大众之间树立起了一个畅销书作家、名牌编剧的形象。可惜那个时候大众传媒未能像今天这样发达,作家、编剧不过是清贫的弱势群体,这些作品的作者始终过着清贫苦寒的生活。
他来自民间,他是穷人的儿子,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作家、草根学者。他出生在大厦将倾、列强入侵的清末,成长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民国——但是这不要紧,这些都没有限制住他的天才思维和如泉涌般的才华。乱世出英雄,穷而后工之。往往越是恶劣的条件,越是常人不敢想象、不敢去面对的困难,越能激发某些特殊人物的斗志与毅力。数千万字的作品,40余部专著、剧本、小说,包括景物诗、竹枝词、曲艺、小曲等等,竟然是在20余年颠沛流离和战乱的环境中写出来的。这里有一种超强的耐力与人格。
但周贻白并未能及时地享受到这样一种成名成家的快感。他至死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土地。20世纪40年代初,他把可以使自己免受战乱之苦的远洋船票,像处理一只旧打火机一样放到好友郁达夫的口袋里,自己在大陆落入了日军的监狱,备受折磨。20世纪40年代末,他又在香港与挚友梁实秋、林语堂等揖别,毅然转身回到了大陆。
2000年是周贻白的百周年诞辰。周华斌、傅晓航为周贻白出版了纪念集《场上案头一大家》,并在中央戏剧学院举办了一次颇有学界声势的纪念会,以纪念这位被人遗忘了太久的学者、作家。出席纪念会的黄宗江称周贻白为“场上案头一大家”,说自己不过是“场上案头一小卒”;原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钮镖则甘愿当“场上案头一小子”。
一代宗师
周贻白来自民间,回归民间。无论苏州、上海,还是北京,他都住在胡同小巷里。他生于胡同小巷,长于胡同小巷,始终与耳聋的老百姓们住在一块儿。
在长沙,他出生在一个叫坡子街的巷道——即现在的解放路附近。那里虽属闹市区,却是三教九流、梨园戏班的杂居之地。在苏州,他住在“养育巷”、“王洗马巷”;在上海,他择居石库门后面弄堂里的“亭子间”进行写作。到了北京,按道理应该可以享受宽敞的书房大堂了,但是他一直住在东棉花胡同22号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如今在一条名叫小经厂胡同里,在一间书房、写字台、饭桌、客座兼容的十几平方米的陋室里,是周华斌的寓所,堆放着周贻白数以千万计的书籍资料—— 像其父一样,那里经常高朋满座。
执教中央戏剧学院的周贻白不改当年在黎明学园和无锡国专讲课的风格。祝肇年、谭霈生、余从等年轻学生是周家的常客——日后,这些弟子很多成了中国戏剧戏曲界的著名学者和领衔人物。时过半个世纪,那些曾经出入周家的年轻人现在早已两鬓苍苍,但是一提起东棉花胡同的那些日子,谁都感觉到仿佛回到了那个令人无法忘却的年代。
前些年,戏剧学者史航写过一篇长文,叫《名剧的儿女们》,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央戏剧学院。我想,更早一点,名剧的儿女们应该铭记欧阳予倩、周贻白等执教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辈学者和教师。那个年代离我们太久了。
周贻白毕生生活在胡同里,与底层民众生活在一起,他是来自于民间的戏剧大师,但他的影响却是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他所执教并参与创建的中央戏剧学院,如今仍依然是胡同里的大学,却并不妨碍它的影响力与生命力。文化的生存,全凭心境与视野,与生活环境的大小了无必然的联系。
在阅读周贻白时,我总能想起一个叫康德的人。他一生清苦、终居乡里,与村民们打成一片,但是视野无比广阔,终成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作为戏剧史上一代宗师的周贻白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