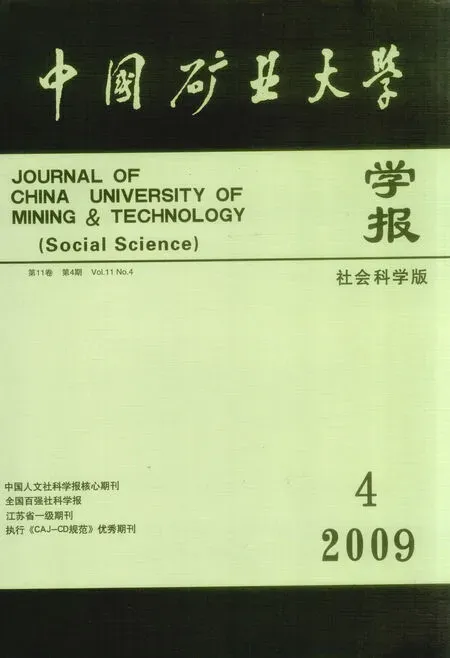政治发展:研究脉络与语境变迁
2009-02-09张娟
张 娟
(长沙国防科技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4)
政治发展:研究脉络与语境变迁
张 娟
(长沙国防科技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4)
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行为主义运动的滥觞,政治发展研究在西方开始兴起,并成为现代政治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70年代以后,制度范式被“重新发现”,新制度主义开始崛起,并从经济学向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迅速扩散。在后行为主义时代,政治发展研究并没有随着行为主义的衰落而式微,而且在新制度主义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并逐步走向深入。
政治发展;行为主义;新制度主义;理论框架
政治发展乃是与人类的政治生活相伴随的基本问题,因此也是政治科学需要孜孜探索的永恒课题。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政治发展问题自国家产生就已然产生,但是在政治科学中真正有意识地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却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而兴起的。此后政治发展理论便成为现代政治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7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科学研究范式从行为主义向新制度主义的更迭,政治发展研究亦不断走向深入。
一、行为主义运动的滥觞与政治发展研究的勃兴
政治发展研究源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走向鼎盛。政治发展研究的发轫和繁荣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发展研究专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P· Huntington)和乔治·I·多明格斯(Jorge·I·Dominguez)所十分中肯地指出的,政治发展研究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两股学术活动潮流汇合一起的结果:一是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区域研究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研究比较政治的学者反映当时的政治条件把注意力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欧和北美。二战之后,“学术研究随着信号旗进入了针对苏联的冷战,然后又进入美国在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存在。一些主要大学都制定了区域研究计划,用以扩大美国知识和了解这些国家和大陆。”在各主要基金会的积极鼓励和支持下,大批教授和学者纷纷涌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当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系作系统考察,发展问题包括政治发展问题遂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二是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作为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研究的新范式,行为主义范式高扬“科学主义”的大旗,要求“把理论的严密性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系统的多国比较来考验普遍性。这种要求理论严密的愿望促使政治学家插足并从当代主要的心理分析学派那里吸收了诸如结构、功能、输入、输出、反馈和体系这样一些概念。这些概念给政治学家提供了可以在分析和比较不同国家的政治中运用的有系统的框架。”[1]148-149而在这两股学术潮流中,行为主义革命的滥觞乃是政治发展研究发轫勃兴之最主要的驱动源。
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兴起,并迅速在60年代替代传统政治科学而成为政治科学的主流。什么是行为主义?从词义上来看,行为主义的 “目的在于用已经观察到的和可能观察到的人的行为来阐明一切政治现象。”[2]145-146在行为主义者看来,“较之于那些阐明应当怎样的准则或规范,行为才具有根本性,因为它涉及的是活生生的政治活动”[3]54,“行为”才是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要素和基本分析单位。行为主义革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梅里亚姆于20世纪20年代所开创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致力于以“科学主义”为指导思想来革新政治科学研究,并培养了后来领衔美国政治科学的许多学者,比如拉斯维尔、阿尔蒙德等人,从而广泛撒播了“行为主义革命”的种子。20世纪5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迅猛发展,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东山再起,并推动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滥觞与繁荣。概括来说,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孕育于20世纪40年代,蓬勃于50、60年代的行为主义运动是一种旨在使政治科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经验化、实证化的运动,它具有四个显著的学术倾向:一是科学主义。行为主义主张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模式,例如物理学、生物学,有时也采用心理学模式来发展政治科学,其目的是“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4]。二是经验主义。在政治理论的历史、规范和经验理论三部分中,行为主义最关注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认为,经验理论的发展是科学理论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因此政治学家们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创立经验理论之中,通过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使政治科学中的经验主义部分更加科学化。三是实证主义。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物质技术基础。电子计算机和与之有关的数据处理设备的发明和迅速发展,社会调查、资料收集和分析技术的进步,运筹学和统计学研究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中逻辑实证主义的崛起。抽样分析、定量分析等被大量运用于政治科学研究中。“在某种意义上,当时的行为主义被当作实证政治学的同义词,尽管是一种注重个人行为的重复性、可见性、可量化性(或注重可衡量和量化的动机)的实证政治学。”[5]四是价值中立。行为主义运动守持价值祛除(value-free)或价值中立(value-neutral)。在大多数行为主义者们看来,道德或伦理探讨与科学论证截然不同,陈述事实和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科学仅仅包括前者,因此,道德准则或规范性传统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而科学对真理的追求,却意味着对道德观念或实际存在的规范的经验性探究,这是不科学的[3]55。由此,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必须努力超脱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准则之上。
行为主义革命对政治科学的发展影响甚深,贡献甚丰。它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改进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实现了政治研究的跨学科整合,完善了政治学的学科分支。正是在行为主义政治学思潮影响下,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交叉的新学科新理论纷纷涌现,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生态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人类学、政治系统分析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沟通理论、政治发展理论、角色理论、团体理论、决策理论、精英理论、冲突理论、政治博弈理论等等。其中,政治发展理论的兴起繁荣并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则是行为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在行为主义革命浪潮高涨的20世纪60年代,政治发展研究逐步系统化,臻于全盛。从50~60年代的这10年间,“论述政治发展的意义、用途、顺序、危机、原因、结果、模式、范围、组成成分和理论的文章和书籍,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1]148在行为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政治科学家在政治发展领域的研究精品迭出、成果丰硕;政治发展理论自成体系,在政治科学诸领域中独树一帜。按照亨廷顿和多明格斯的归纳,在政治发展研究全盛时期的60年代,至少有三大流派。一是体系功能方法派,主张把体系理论要素与结构功能主义相结合。其代表学者有:马里恩·列威、戴维·伊斯顿、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宾厄姆·帕威尔、戴维·阿普特、伦纳德·宾德和弗雷德·里格斯。二是社会进程方法派。该派试图通过对国家社会进行比较的定量分析,把政治行为和进程与诸如城市化、工业化和传播媒介的日益利用等社会进程联系起来。其代表学者有:伦纳、多伊奇、雷蒙德·坦特、马丁·尼德勒、菲利浦斯·卡特赖特、小海沃德·埃尔克、迈克尔·哈德森,等等。三是比较历史方法派。倾向于把传统方法与追求系统严密性的努力的结合。其代表学者有:西里尔·布莱克、S.N.艾森施塔德、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小巴林顿·穆尔、丹克沃特·罗斯托、莱因哈德·本迪克斯、塞缪尔·P·亨廷顿和卢西恩·派伊,等等。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局限性,如果扬长避短结合起来使用,就会使政治发展进程以暂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1]150。
诚如政治学家詹姆斯·法(James Farr)所言,我们在今天都仍然还应该记住这场政治科学内部的革命,因为正是通过这场革命之后,政治科学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才得以大地扩展,政治科学的研究面貌才因此而焕然一新。自此之后的政治科学即使发生了分化与重组,但是几乎没有哪一个流派不是在与行为主义进行对话与交流之中发展出来的[6]84。但是行为主义范式也有着深刻的内在缺陷:它过于强调政治科学的科学性而放弃了政治科学的政治性;它过于聚焦政治主体的“行为”而忽视了型塑政治行为的制度因素;它倡导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而在实际研究中根本不可能做到;它过于注重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而排斥了政治研究的历史主义与规范主义传统。正是这些缺陷阻碍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科学、全面的认识。政治科学研究的视野不能否弃制度,因为“制度确定了一个社会之中的基本活动框架,只有明确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活动框架之后,才有可能深入对这个社会的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也并不完全是一种纯粹物理行为,而是一种受人的理性、动机和人所制定的规则所驱使的行为”[6]91。离开制度,不可能达到对政治的科学理解。
二、制度范式的复兴与政治发展研究的视角更新
把制度和规范研究排除于视野之外,是行为主义运动的最大诟病,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运动为此受到了诸多批评并走向衰落。西方政治学于70年代开始进入后行为主义时代。出于对30多年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反思,西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都掀起了“重新发现”制度的热潮。
首先聚焦于制度研究的是经济学界。与行为主义之前的政治学传统研究范式一样,在经济学说史上,关注制度者早已有之,且贯穿整个经济思想史。根据马尔科姆·卢瑟福的归纳与研究,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可以分为旧制度主义(The old institutionalism)和新制度主义(The new institutionalism)两大门派。旧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托斯坦·凡勃伦(Torstein Veblen)、维斯雷·米契尔(Wesley C. Mitchell)、约输·R·康芒斯(John R. Commons)以及克莱伦斯·阿里斯等人。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科斯(Ronald H. Coase)、诺斯(Dougalass C. North)、德姆塞茨(H. Demsetz)、阿尔钦(Armen A. Alchain)、奥尔森(Mancur Olson)拉坦(Vernon W. Rutton)、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张五常(Steven Cheung)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开创者是罗纳德·H·科斯(Ronald H. Coase),他的两篇开创性论文《企业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奠定了基石。后随着斯蒂格勒的关于信息经济学的论文(1961)、阿罗关于适度报酬的论文(1962)相继发表,新制度主义开始崭露头角。1975年威廉姆斯正式将其命名为“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军人物、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North)先后发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等重要著作,提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主张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来解释经济变迁,建构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罗纳德·科斯、德姆塞茨、张五常的产权理论、奥里弗·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共同形成了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已成为当今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并被经济学家们视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受新制度经济学辉煌战绩的鼓舞和启发,部分政治科学家也开始把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引入到政治分析中来。1984年,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en)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从而开启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兴起的序幕,“新制度主义”开始吸引越来越多政治学者的注意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崛起成为西方政治科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许多学派都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要理解不同社会系统在发展方面存在的重要差异,社会或经济结构变量不是关键原因,政治制度却是最重要的解释性因素。甚至可以说,被理解为制度发动机的政治已重新找到了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早期所丢失的中心主题。诚如鲍·罗思坦(Bo Rothstein)所言的,“制度研究已经处于当代政治科学理论的中心地位。”[7]许多学者都自称“现在我们都是制度主义者了”,[8]在后行为主义时代,政治科学研究并没有随着行为主义的式微而没落,反而在制度研究复兴的浪潮中被注入了新的理论动力并逐渐走向深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和分析途径的不断拓展,其学术队伍迅速膨胀,学术派别日趋细化。关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划分众说纷纭,在学术界影响比较大的、得到公认的则是豪尔和泰勒于1996年在英国的《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共同发表的 “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 一文所提出的三分法。彼得·豪尔(Peter A.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C. R. Taylor)指出,80年代初以来在西方的政治科学中已经至少有3个流派都自称是“新制度主义”,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而且,这三个流派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理论假设和分析路径,各有其鲜明特征和优劣之处[9]。彼得斯(Guy Peters)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大流派的共同点可归结为:制度因素是社会分析的最佳出发点;制度为人们的行为创造出了大量的调节性规则;都将制度视为人们意图性行为的限制因素。伽马克(Paul Cammack)则将新制度主义的共同特点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新制度主义强调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在起作用,并循此而追问制度的长期效率及其后果;二是将制度重归其位,重点考察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因素,而不是政治发展过程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三是倾向于将政治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四是注意通过对公共政策的研究来探测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五是倾向于将制度的长期演进看作是一个不连续的过程[6]15。
在后行为主义时代,作为对行为主义范式的匡补、替代和超越,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正日趋深化和完善。随着政治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演进,政治发展研究也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新制度主义范式给政治发展注入了新的理论动力,使得政治发展研究的视角焕然一新。
三、新制度主义语境中政治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新制度主义为政治科学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语境中,政治发展研究也获得了新的理论框架。
(一)政治发展的本质:正式与非正式政制的变迁
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政制的变迁和创新是政治发展的核心与本质。政治文明主要体现为政制文明,政治发展主要体现为政制从专制到民主、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运动和变迁过程,也即政制的变迁与创新。政制变迁就是政治制度的创设、调整、打破、更替的运动历程。政制创新则是前进意义上的政制变迁,就是通过渐进改革或彻底打碎旧政制的方式,以一套更具功效的、更适应时代潮流的新政制部分性或根本性取代旧政制的方式与过程。政制变迁与政制创新可以是根本制度的彻底更新,也可以是具体制度的渐进改革,具体在政治发展中采用哪种方式,则需要视社会经济状况与时代环境而定。新制度主义视野中的政治制度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正式制度:就是政制创新主体所创设的借以组织国家政权、安排政治生活、调节政治关系、规范政治行为、实现政治统治的一套法则、规范、程序。正式政治制度包括三个层次:(1)根本制度,它决定国家政权的根本属性;(2)基本制度,是根本制度的具体体现形式,包括选举制度、议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等等;(3)具体制度,指为保障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实施而制定的一系列操作性的具体规范、原则与安排。二是非正式制度:即影响和制约政治进程的非正式规则,如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政治伦理、政治文化等的总称。可见,新制度主义视域中的政治发展主要包括两方面——思想价值层面和国家制度层面的嬗变演进。
(二)政治发展的方式:连续渐进型和断裂突变型
制度变迁可分为连续-渐进型和断裂-突变型两种方式。连续型政制变迁是一种在保持根本政制框架稳定性、连续性的前提下对局部政制的逐次调整、变革和更新。突变型政制变迁是指以激进的、急剧的、全局的方式在短时间实现政制的质变性的替代更换。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压倒性的方式是渐进式变迁,制度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一个制度框架的总体稳定性使得跨时间和空间的复杂交换成为可能[10]111。经过漫长的时空演进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博弈,无数个具体、微小的规则变化的总和,最后建构成了基本的制度变迁。在此过程中制度变迁呈现出从正式规则到非正式规则的逐次深入。但是诺斯也同时指出,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战争、革命、武力征服以及自然灾害等情况下,会发生非连续性、断裂性制度变迁,即突变型制度变迁。当政治交易或政治冲突双方无法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达成谈判和妥协时,其中一方就会利用意识形态凝聚支持力量,凭借暴力手段打破制度僵局,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新制度。对于这两种政制变迁方式的优劣评价,应结合具体民族的具体历史情境来判定。在和平时期通常采取渐进型,以逐次铺展、探索试错的方式进行政制创新。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社会长期陷入了制度无效率的路径锁定状态下,就必须通过突变型政制变迁来跳出僵局,粉碎旧政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制度创新的抵制和阻碍,以更具效益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但是突变型政制变迁也有弱点,除了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暴力流血之外,还有一大弱点就是,突变型政制创新的结果是正式规则发生了迅速改变,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却异常缓慢,由此就会形成“非正式规则与新的正式规则之间的紧张关系”[10]121。由于非正式规则是基于社会深层次的文化遗传,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即便是当正式规则的向前延伸与发展的时侯,非正式规则的巨大引力仍会导致正式规则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归和变异。因此,对于许多经激进革命而完成新政制创建和政治发展的阶段性跃迁的国家来说,革命后的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任务比革命本身还要艰巨复杂得多。
(三)政治发展的动力:政治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
政制创新的直接原因则是受利益驱动。马克思有句经典名言:“人们所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进一步从“成本—收益”的视角出发揭示了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因,乃是制度创新主体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即当人们认为创设新制度的收益大于因此而招致的成本时,新的制度就会出现;反之,人们就不会冒着风险去创新。如诺斯所言,“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12]。政治学家戴维·菲尼也指出,“对制度安排的变化的需求基本上起源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按照现有的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在原有的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13]。与经济制度创新一样,政制变迁与创新也是源于利益的驱使,这种利益是复杂多样的,不仅仅只是经济收益,还包括获得政治权力、增强政治合法性基础、博取政治认同与支持、积累自身的政治资源等政治收益,甚至还必须考虑到民族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由于政治领域比经济领域更充满冲突与博弈,政制创新进程也更为复杂和艰巨。政治发展进程充斥着各种复杂的政治主体之间的权力争夺和利益博弈,正是各种政治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博弈推动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演进。
(四)政治发展的阻碍:政治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政制变迁与创新的阻碍来自两方面: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治制度具有阶级性,总是服从服务于特定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因此,政制一经确立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繁衍出各种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具有抵制任何变革的动力和权力,因为变革会剥夺它们所攫取的扩大了的社会产出份额”[14]。政制创新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现存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的打破与再分配,影响既得利益集团的租金收益,因而必然会遭到旧制度所庇护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与阻碍。二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某种制度一旦被选定和确立就具有极大的惯性和惰性,并会产生一种自我捍卫和自我强化机制,沿着初始选择的轨迹一直演化下去,非凭藉强大的外力难以扭转其发展路向,这就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借助路径依赖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精辟地解释了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以及长期不良绩效的社会和经济为何会持续存在。当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派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观深为认同,但同时也强调,与经济制度相比,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征更为明显和突出。政治学家皮尔森(Paul Pierson)指出,相对于经济生活而言,政治世界具有几个明显的相互关联的特征,这些特征强化了政治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是集体行动的核心地位。在政治活动中,任何一项政治产品(政策)的产生过程都是集体活动的结果,每一项政治活动也都依赖于他人的合作,极易产生人们对制度的适应性行为;二是政治制度的高度密集。供给公共产品的政治生活必然要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因此大多数政治活动也就必须基于法律和制度约束的基础上而展开,而无法自由退出;三是能够运用政治权威来提高权力的非对称性。政治活动主要是一种权力活动,权力具有非对称性。权力的支配方在巩固自己权力的同时,也在巩固既存制度;四是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使得政治生活中缺乏明显的纠错机制;五是政治活动所提供的是一种非竞争性公共产品,政治供给的非竞争性决定了政治活动的主体缺乏改善制度的动力[6]238-242。
(五)政治发展的目标:实现效益取向的制度替代
政制创新的目标是以一套更具效益的制度替代旧制度,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发展。这种效益是全方面的:第一,经济效益。根据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政治制度尤其是宪政秩序通过决定经济制度和经济安排而间接决定着经济绩效,因此能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则无疑是衡量政制效益的根本标准。第二,政治效益。有效益的政制至少应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权威性。有效的政制必须具有权威性和刚性。政制安排与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涵盖全体社会成员,任何人都不得有超越法律和制度的特权。制度只有具有权威性才能保证其平等性与公正性,才能正常执行其对政治生活的规范与协调功能。(2)自立性。虽然政制总是带有阶级偏好,但是有效的政制总是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如果政制纯粹地沦为某一集团疯狂逐利的私人化工具,就意味着这种政制公共职能的枯竭和政制的衰败。当代新制度主义把制度的自立性尤其是司法组织和制度的自立性看作是制度有效运转所必需的实施机制与保证。亨廷顿把政制自立性看作是不仅是衡量政制绩效,而且是衡量整个政治体系发展程度的标准。(3)合法性。政制的合法性就是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也即政治制度能够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的认同、支持与服从。如果一套政制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那么就会无形中提升政制的整合和规范功能,法律和制度的实施及政策的贯彻执行时受到的阻力就会比较小,政制的运行成本就会降低,运作效率就会提高。政制的合法性与政制的有效性之间是相互依赖,相得益彰的关系:政制必须具有合法性,才能有效地运作和实施;政制的施行也必须具有高效性,才能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合法性不仅是政制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其重要目标。第三,文化效益。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是复杂的,文化孕育了政制,同时也型塑了不同的政制模式;政制深嵌于社会文化之中,并与文化母体进行着传导与互动。有效益的政治制度应该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动作用推动引导社会文化的嬗变转型与发展进步。莫伊尼汉说得好:“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15]
纵观政治发展的理论历程, 政治发展研究随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发轫,随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鼎盛而繁荣,随7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的崛起而日趋深化。作为继行为主义之后又一次深远的范式革命,新制度主义运动对包括政治科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新制度主义的深入,政治发展研究也必然会日趋完善。
[1] [美]塞缪尔·P·亨廷顿,乔治·I·多明格斯.政治发展[M]//[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 [美]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45-146.
[3] [英]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4.
[4] [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73.
[5] [美]詹姆斯·W·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91.
[6]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7] [美]罗伯特·古丁,等.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03-211.
[8] Mark D. Aspinwall ,Gerald Schmeider, Same menu, separate tables. The institutionalist tur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8,2000:1-36.
[9] [美]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J].何俊志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05).
[10] [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12] [美]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74.
[13] [美] V·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38.
[14] [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57.
[15] [美]亨廷顿,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前言)[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
PoliticalDevelopment:theCourseofResearchesandChangesofContexts
ZHANG 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4,China)
After 1950s, with the diffusion of behaviorism, the research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began to spring up and soon became an important branch of modern politics. After 1970s, institution paradigm was rediscovered. New institutionalism gradually grew up and spread from economics into the realm of social sciences including politics. In the times of post-behaviorism, the researches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have not declined with the declining behaviorism. On the contrary, they have acquired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are gradually becoming more thorough and deep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behaviorism;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etical framework
2008 - 10 - 23
张娟(1976-),女,法学博士,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社科系政治学教研室讲师。
D091.5
A
1009-105X(2009)04-0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