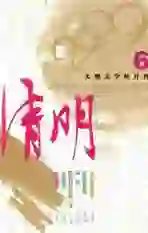那盏贪婪的煤油灯(外二篇)
2009-01-20庞余亮
庞余亮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是隶体,红漆拷上去的。
转过来。
“奖”
“大寨河工程纪念”。
还是隶体。再下面就是时间了,就是父亲得到这个搪瓷茶缸奖品的时间,这个时间应该和我的出生有关系。而等到我明白这个时间和我有关系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不再相信母亲所说的“你是从我胳肢窝里掉下来的”的话,也不再相信父亲所说的“你哪里是我们家的,是我从渔船上抱过来的”的话。对于他们的话,我曾经有过多种幻想。现在想起来,我是多么的丑陋和可笑。
这只搪瓷茶缸曾作为父亲的宝贝,父亲用它喝茶,用它往田里带自己中午的午饭,用来刷牙。家里人也喜欢用这只茶缸喝茶,仿佛这只茶缸里面的水更甜。用多了,里面的白首先染上了茶垢和水锈。再后来,外面也不白了,上面还落有了父亲的黑指纹。再后来,这只茶缸子还丢失过,又找了回来,虽然很多人家都有这样的作为奖品的搪瓷茶缸,可是都有了记号。我们家的茶缸记号是上面打了瓷,其实每个人家的茶缸都掉了瓷,我们家的比较特殊,掉的是两块大瓷,正好就像一双眼睛。不过怎么看,还是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用我母亲的话说,活像三歪子的眼睛呢。
我就是那个三歪子。
搪瓷茶缸上的两只眼睛:一个是父亲自己失手跌的,一个不晓得是谁跌的,父亲非说是我跌的,还为了这个收拾了我一通。他说,只要你承认是你跌的,就不打了。可的确不是我跌的,我为什么要承认?母亲最后也劝我,他是你老子,他就是错了,也是对的,你就承认吧。不晓得后来我是承认了还是没有承认,反正我为了这只搪瓷茶缸被打了一顿。
有了一双眼睛的搪瓷茶缸还能够用,不过全家人对于这个已经掉了瓷的茶缸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当心了,这样的结果使得这只搪瓷茶缸身上的瓷掉得更多。还瘪了几处,上面的字也残缺不全了,就有点像后来我的先生教我的字,他本身没有读好书,他教了我许多错字,还有别字,后来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才改变了一些使得我出了不少洋相的字的读法和写法,不过还有一些,就没有办法改正了,比如,倒笔划。
后来,也是肯定的,搪瓷茶缸就漏了。母亲想找我们庄上的补锅匠补一下,可是在搪瓷茶缸漏的时候,正好我父亲不再和补锅匠说话了,父亲还自己用牙膏壳补了一下,补漏要用锡,父亲认为牙膏壳就是锡的。我们家总是用“芒果”牌牙膏,说不定是父亲剪的牙膏壳可能太大了,也有可能是漏洞本身已经出问题了,反正父亲没有把搪瓷茶缸的漏洞补好,漏洞反而更大了,牙膏壳的伤疤显得非常滑稽,一茶缸的水放进去,漏洞那个地方就像尿尿。
没有人敢笑话父亲,这只茶缸就丢在一个角落里了,上面落满了灰尘。母亲后来就在漏洞的那里垫上一层纸,装了当年留的黑纽扣样的丝瓜种。再后来,由于母亲总是把药水瓶做的煤油灯打破,(药水瓶是玻璃的,而煤油这个东西就喜欢往外“爬”,煤油一爬出来,煤油灯就滑得很。)父亲想到了这只退了休的搪瓷茶缸。父亲到老木匠那里找来浸了桐油的一块石膏,他那时正好替生产队修船,父亲就把玻璃药水瓶做的煤油灯放到了搪瓷茶缸里,然后再在玻璃瓶的周围衬上了油石膏,一盏有把子的煤油灯就这样做成了,母亲再拿起灯到灶屋里做事时,就不再滑手了。
那时的煤油都是上计划的,为了节省煤油,父亲在中堂和他们所在的东房间的墙上掏掉了一块土墼,煤油灯就端坐在这个缺口中,这样,一盏油灯就照亮了两个房间,照了一段时间之后,土墼的上方就熏出了一道黑灰,白天的时候,家里最明显的地方就是这道黑灰。很醒目。而搪瓷缸做的有把手的煤油灯成了母亲最喜欢的东西了。母亲只要喜欢一样东西,就会经常放在嘴巴上。
“这可是你父亲挑大寨河的时候奖的茶缸呢。”
不仅是母亲这样说,在我们村庄,也把挑大寨河那年作为一个年限。说起一件事情,总是把挑大寨河那年作为标志。大寨河,可能不是我们那个地方独有,我曾经到过一个地方,他们把一条像小水沟一样的河也叫做大寨河。我们那里的大寨河可是一条很大的人工运河,是集中了全县十万民工的力量挑了三个月才挑起来的。当时我父亲就在这个工地上。茶缸上的时间就是结束的时间,也正是这个时间,我想到了我的出世,还有和我同年出世的那些童年伙伴。
本来我没有想到这些,还是我们庄上老接生婆王四娘说的话提醒了我。她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王四娘见到了我,她不认识我了,我告诉了她,我是二马屁家的三子,她记起来了,她说,我没有给你接过生,你母亲有本事,自己给自己接生哩。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那时我也忙啊,你们都来不及的往这个世上跑,害得她屁股都来不及着地。她还说,一下子来了那么多孩子,真正是来了一个大部队!
她的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又特地仔细看了那盏煤油灯,搪瓷茶缸由于做了煤油灯,上面的瓷反而没有再掉多少,我还是看清了上面的时间,大寨河工程结束的时间,这个时间和我的出生时间相差八个月。
可以想像一下我出生的起点,那个泥泞的,混乱的疲惫的大寨河水利工地。
大寨河水利工地的白天是泥和锹打交道,担子和肩膀打交道。到了晚上,睡在全是泥腥味的工棚里,主要没有事做。冷是不怕的,大队里带的稻草特别多。这种黄金被暖和得很呢。应该说大家挖了一天的泥,挑了一天的担子,应该早点睡着了。今天工地上的大喇叭又表扬我父亲所在的团了。可是大家睡不着。睡不着就有人提议讲下流话。矮支书也在场,估计他们睡着了,估计他们又想听。本来大家都要三十八讲的,可是他们假装睡着了。俗话说得好,睡着的人好叫,装睡的人叫不醒。这时候三十八就出场了,应该是那个老光棍三十八,因为只有老光棍三十八,他才能胜任讲下流话的任务,也正是他一以贯之的下流话,后来完成了对我的最初性启蒙。
三十八讲了三个下流谜语,三个谜语的谜底分别是马桶、烘山芋和牙刷,但谜面却黄的很。三十八的嘴巴里还有许多这样下流的谜语。谜底很简单,可是很撩人。尤其离家一个多月了,大家身体里的火苗一蹿一蹿的。还带了呼啸的哨声。不久,黑暗中的哼叽声响了起来。
突然听见有人在穿衣服,问做什么,说是尿尿。立即有人揭发了,尿尿?刚刚不是尿了吗?不是想婆娘了吧。穿衣服的那个人说,想婆娘又怎么样?我得回家一趟。黑暗中有人问,你是不是熬不住了?那个人说,是的,又怎么样?就是想婆娘。一个人把话说开了,他说要回去,其他的人也纷纷套衣服,也要回去,说是要回家拿衣服。矮支书应该就在这个时候醒了过来,于是他们就很生气,说,明天你们出工不出工了?他问得快,其他人回答得也快,怎么不出工?明天早晨就回来。
矮支书很是棘手,他和干部们开了紧急会议,七嘴八舌的,最后的主意当然是矮支书定的。矮支书和大家一起回去,主要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大队还决定,不要跑夜路了,回去危险,回来更是危险。还是用机船好,明天早晨五更头上回来。五更头有点亮了。矮支书的决定受到了大家欢迎。你想想,干了那个事情是不能喝凉水的,再回来,受了风寒,就要得病了。当然也有不好回家的,刚才讲荤话的三十八留下,今天是他惹出的祸,他负责看棚子。这些深夜回家的人,坐的是大队里马力最大的抽水机,有十二匹马力呢,父亲很积极,抢着做了机工,刚摇了几下,机器就发动了,抽水机后面像炮筒的出水铁管一下子昂了起来,然后,一阵激动的河水就喷了出来,终于,这群被三十八的荤话撩得急吼吼的劳力们从河面上消失了,之后一船的人像蝌蚪一样游进了黑暗之中。那抽水机冲出的浪头,把停在一边的其他村的水泥船弄得咯啷咯啷的起起伏伏,久久不能平静。
这其实是我后来想像的一个场景,但有一点可以说明,荤话肯定是有的,否则不会有那样的效果,带队的矮支书也不会同意开大队的机船。没有荤话的点燃,矮支书是不会答应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父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死于中风,六十年代末期的大寨河工地上的那个工棚里详细发生了什么,其实已经无关紧要,关键是由于这一个晚上,导致了三歪子的出世。还有三歪子的其他童年伙伴的出世。还有大寨河工地,一只搪瓷茶缸的奖品,这只奖品上面的字,以及时间,以及后来做了煤油灯,都和我的一生有关。
也许很不恭敬,把父亲埋葬之后的那个晚上,我就呆坐在这盏煤油灯下,母亲以为我伤心,其实我是在猜想自己的出生。我只是一次劳动之后的偶然,一次欲望对于劳累的背叛,一次由于荤话引起的冲动,带来了我羞辱、卑微而又自闭的生活。大人们多年前一次不负责任的偶然带来了我们必然的痛苦、绝望和希望。还有一群拥有脏得发亮的前襟和袖口的丑孩子,他们一直生活在我的记忆里,打闹,调皮,没有理由的闯祸,有时候,我用肥皂和清水替他们洗干净了,但洗完之后,他们就变得陌生,已经不是我的丑孩子了,他们曾经那么清澈的目光就变成了对我的绝望和憎恨。命运不想忘记他们,更不能替他们洗净身上的灰尘、汗水、草屑和鼻涕口水的混合物,他们的黑眼睛一直看着我,看着我,这个已经长大的丑孩子,我必须将最为真实的记忆作为煤油注入搪瓷缸做底的老煤油灯中,并且用贫穷和单调的童年中渗透出来的快乐将这盏煤油灯点亮。
一盏煤油灯,就能够照亮一个名叫三歪子的丑孩子,他将以它金黄的灯光为食,喝下它所照亮的,啃下还没有被它照亮的,他对于疼痛表现出来的贪婪的胃口,和他对于幸福的贪婪胃口一样大。
黑暗中的炊烟
中年人回味童年,肯定是衰老的标志。其实岁月就是一颗怪味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吃下去,有一些酸楚有一些苦涩还有一些甜蜜的往日啊。
防震抗震那年,我上四年级。
那还是深秋季节,教室的草屋顶刚刚换上了新稻草,像是得了白癜风。老师抓粉笔的手上都是泥巴,他们刚刚从田里回来。我无心上学,因为有人在说五里外的邻庄要放电影了,有人将弄一条船去。
放学了,我没有像往常一样蹿回家,而是磨蹭着,看看有哪些人没有走。果真,有几个大个子的同学没有走,我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以代他们做三天作业的代价上了那条生产队的大木船。
那些大个子同学弄小船有一手,可都不太会弄这条生产队来回上工的大木船,木船头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好在那天风不大,否则我们肯定看不成电影了。就是这样,待我们靠到邻庄大柳树下,打谷场上的电影已经开始了。好在有经验的,那不是正片,只是放过好几遍的《新闻简报》。
我一生都会记住那晚放的两部电影,一部《红孩子》,一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正当白骨精化作老妖婆时,派去察看船的伙伴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说,竹篙没了!
孙悟空还在那里三打白骨精,我们只有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寻找竹篙,是哪个丧良心的把竹篙偷走了呢。后来,我们来到一家门前,发现有一把竹篙正倚在他家的竹篱笆上,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小心地把竹篙抽出来,扛了就走,反正我们的竹篙就在这个庄上呢。
电影是看不成了,只有上船回家。也许是做贼心虚,一路上,我们被一些黑影和突然出现的高坟吓得魂飞魄散,好像四周都是吃人的白骨精,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我们才把大木船靠到码头上。此时已经是半夜了,村庄静悄悄的。
刚上岸,一只狗突然狂叫起来,满村的狗也狂叫起来,后来发现都是自己人,不叫了。可我们都不敢回家了,只好宿到一同伴家灶屋里的稻草上。稻草可能淋过雨,一股霉腥味冲得饿极了的我们无法入眠。
不知道是谁发现了一堆芋头籽,大家连洗都没有洗就把它们扔到了锅里,加了水,盖上锅盖,往锅腔里塞满稻草,开始了烧芋头。可能是火光的缘故,我出去撒尿。外面的夜空瓦蓝瓦蓝的,有几颗金色的星星在闪烁,草屋顶上有一缕炊烟袅袅向上,好像是笔直地爬上了天空!
——可能是觉得太美了,我全身不停地打颤!回到屋里时,灶火已经把同伴的脸映得通红通红,芋头发出了诱人的香味。
第二天早上,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回到家中,也做好了被脾气不好的父亲痛打一顿的准备,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擅自在外面过夜,但奇怪的是,母亲见到了,说了声,你为什么还不去上学?锅里有山芋粥。我看了看父亲,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呼呼喝了两碗山芋粥,上学去了,好像家里不晓得我在外面过夜啊。但我一直想不通,父亲为什么不知道我丢失?还有,那炊烟,为什么那么笔直,就像是一把炊烟做的直尺?!
三棵榆树过年
我家门口长着三棵很高很高的榆树,过年还没到,三棵榆树上挂满了我父亲从河里罱上来的杂鱼,杂鱼的腹部被我母亲用一截一截的芦管撑开——像一个个迎风敞开棉袄的顽童。母亲还用一根竹条——将它削细,然后将这些大小不一的杂鱼一律串起,这些“顽童”一下子就有了组织性和纪律性。我不心疼。我想吃它们。所以我和一只馋嘴的黑猫就总在榆树下渴望,黑猫喵喵地叫着,像替我数数似的。腊月了,和粉做粉团。我和母亲去舂米。臼杵很粗。我总是要用全力才能将臼杵那头抬起,我母亲往臼母里撒米。一臼杵下去,很久才能抬起来。母亲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搞好呀,养只猫养只狗也比你有用。我又用力——只好全身站上去,臼杵那头好像咬住了臼母,我又用力蹲下去,其实蹲下去又有什么用?过了很久,臼杵牙齿终于被糯米粘疼了——终于松开了口……我从臼杵的一端落下去,猛然一震,脚后跟上的皲口就裂了开来,疼。还是再站上去,又一震。老棉袄里满是汗,我不能脱,我只是光身扛着一件老棉袄,像裹了一身盔甲。
做米团(糯米圆子)了。我已累得不成样子了。我躺在灶后的草上呼呼大睡。待第一笼粉团蒸好后,我姐推醒我,吃米团了,吃米团了!我咬了一口就不想吃了,我又衔着米团睡着了……直至第二天早晨,我又看着三棵榆树上晃来晃去的咸鱼。咸鱼们逃了一夜,一个也没有从母亲的那根竹条上逃脱。它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在落了叶的榆树上做风向标,像在纪念什么生活。我和黑猫仍在眺望。天那么蓝,草屋顶上的霜开始化了,一层雾气。巷子上有换糖的糖锣声。当当,当当。我的耳朵都要震聋了,他的生意肯定不好了,我已把母亲藏在破木箱里的一袋花生糖偷吃得差不多了。我不想吃糖了,我想吃咸鱼。而咸鱼们正在树上学习鸟儿筑巢,三棵榆树在过年,而我和黑猫被太阳晒得软塌塌的,仰望着,我开始打喷嚏,一个,又一个,再一个。母亲听见了,嗬嗬,再打一下。我真的再打了一个。母亲说,四百岁!再打一个!我真的想打,可我打不出来了,眼泪鼻涕都流下来了,像受尽了委屈似的。母亲说,要过年了,要过年了,快去跟我把你的爪子洗洗。
我低下头看我的手,我的手上哪里是脏,全都是冻疮。三棵榆树依旧在带着三串咸鱼扭来扭去跳秧歌,三棵榆树在过年。
好书可以终身为父
夜晚所毁灭的,梦会补偿
我梦见了那些书的分娩
疼痛和血汗浸湿大地
——博尔赫斯突然失明
谁的身体在黑暗中变得修长?
他看不见,可以抚摸
一张丑陋之脸上的泪水
就像是花园里交叉的小径
是谁在说——好书为父
好书可以终身为父。
这是我写于鲁迅文学院的一首诗《好书可以终身为父》。
是的。好书可以终身为父,这就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葵花宝典。我读的第一部名著是《水浒传》,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上中下三册的那种,墨绿色的封面,翻开就是一大段毛主席语录。与它相逢时我十三岁,正在离家十里外的公社中学上初二。是爱听广播评书的同桌借给我的,他先借给我上册。
借到这本书的那天,刚刚下了一场雨,我怀抱它走了十华里泥泞的路,回到家里就看了起来。当时的煤油是很紧张的,严厉的父亲看到我看得那么投入,就问了一句,看的是大书吧?我的心狂跳起来,如果他知道我在看大书,他一定会将它撕掉,再痛打我一顿。
偏偏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虚构”。我说,什么大书,这是课本!是先生叫我们看的!我之所以有胆量“虚构”,是因为父亲是文盲,母亲是文盲,我姐姐同样是文盲。父亲听我说是课本,不再说话了。父亲辛劳的一生中,最为敬畏的有两种人,一是干部,二是先生。
连续三个星期,我看完了第一部名著《水浒传》。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根本就不知道我当年撒了谎。直到他去世,他也不知道我一直是在梦想做一名作家。我和他之间一直存在着不能沟通的隔阂。可我现在很感谢父亲,这种感谢缘于生活,更缘于我读过的那些书教会了我理解父亲。或者说,因为我所读过的书,打开了我卑微的生命。
2004年,我作为江苏青年作家的代表,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全国中青年作家第三期高级研讨班学习,除了见识了许多好同学,还有一件快乐的事就是拥有了鲁迅文学院的图书馆,那里的文学图书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市场上基本已绝版。更让我快乐的是,借书卡上前面借的人都是在鲁迅文学院就读过的名作家,比如王安忆,比如莫言,比如陈世旭,比如余华。余华借看过的一本是《辛格短篇小说选》,上面还有余华用铅笔做的记号,难怪余华那么喜欢辛格的《傻瓜金姆佩尔》。
我还在图书馆里看到那种墨绿色封面的《水浒传》,我把三本书一起借了过来,晚上,我在宿舍里翻着它们,心里真的百感交集。恍然回到1991年的夏天,父亲瘫痪在床,我在他的病床前守护,洪水形势非常的危急,我在他的鼾声中阅读美国作家托马斯·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前言中的一段字让我禁不住流下了泪水:“……我们之中有谁真正知道他的兄弟?有谁探索过他父亲的内心?有谁不是一辈子关在监狱里?有谁不永远是个异乡人,永远孤独?……哑口无言地记起来,我们去追求伟人的、忘掉的语言,一条不见了的通上天堂的巷尾——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扇找不到的门。何处啊,何时?嗳,失落的,被风凭吊的,魂兮归来!”托马斯·伍尔夫是福克纳的老师,也是我精神上的导师,那个夏天,《天使,望故乡》教我明白了我的局限和自私。
第二天,我和我的作家同学恰巧讨论如果有前世的话谁会是什么角色。他们纷纷说出了自己不凡的前世,大多都是前世的伟人转世。我忽然想起了那部墨绿色的《水浒传》。它就像我所热爱的文学一样,墨绿色的文学,墨绿色的生活,养育了一个热爱文学的作家。所以我对我的同学们说,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我的前世是一条狗,一条爱待在私塾外听先生讲书的卑微的狗,因为爱书,所以这一世就让我如此地热爱读书热爱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