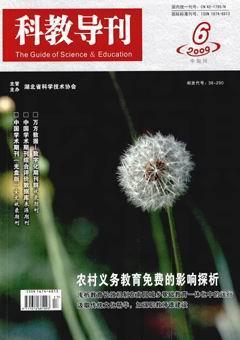天使与魔鬼
2009-01-12刘婷婷
刘婷婷
摘要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视角出发看待女性有两种形象,要么是“屋子里的天使”,要么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本文以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为文本,分析作家在书中塑造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女性形象,反映出女作家对自身女性身份的思考和困惑,以及在男权社会压力面前的屈服和无奈。
关键词《蝴蝶梦》 女性形象 女权 身份焦虑
中图分类号:I506.2 文献标识码:A
《蝴蝶梦》原名《吕蓓卡》(Rebecca),是20世纪英国非常受欢迎的悬念浪漫主义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1907-1990)的代表作,它是20世纪的第一部哥特式小说,自问世以来一直深受读者喜爱。杜穆里埃以精湛的叙事技巧使情节发展悬念迭起,在描述缠绵悱恻的爱情的同时,也塑造了神秘恐怖的气氛。
故事情节通过无名女主人公“我”对自己的梦境、回忆的叙述展开,围绕本书的同名女主人公吕蓓卡的死因紧张推进。在情节曲折发展的同时,杜穆里埃赋予这两个女性形象截然相反的性格特点和道德标准,一个是温顺、恬静、善良、真诚的“我”,一个是美丽、精明、奢侈、放荡的吕蓓卡。单纯善良的“我”作为迈克西姆·德温特的现任妻子,竭力帮助迈克西姆掩盖他杀害前妻吕蓓卡的事实,再加上吕蓓卡生前的放浪形骸、行为不端,让所有人都希望迈克西姆能逃脱谋杀的罪责,而吕蓓卡的死因最终被定论为自杀使得几乎所有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杀人者能众望所归地逃脱法律的惩罚,其原因应该在于杜穆里埃的叙事策略,让父母早亡、涉世不深的“我”作为叙述者,以“我”的纤弱、无助对比吕蓓卡的强势和独立,进而博取读者对“我”和男主人公德温特的同情和怜悯。这种叙述模式归根结底是作者的创作思路有意无意回归到主流社会道德标准的结果,具体讲就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形象根深蒂固的影响的结果。
当代女权主义批评认为,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对女性属性的界定和评价都依照男性的标准。当人们从男性的立场出发看待女性时,对女性的要求和期望无不带有男性的偏见,这种偏见在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见到。以语言为例,人们用诸如坚强、勇敢、雄伟、刚毅等都带有积极而具强势意味的词语形容男性,而用诸如温柔、体贴、理智、善解人意等消极而明显带有弱势内涵的语汇来表现女性特征。然而,在二战后席卷西方世界的妇女解放运动中,以西蒙·德·波夫瓦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首先对西方文化中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提出了挑战,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各个层面上探讨了性别歧视的社会根源,要求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她们指出,生理意义上的性(sex)和社会意义上的性(gender)其实不是一回事,把女性和“柔弱”联系起来并没有生理上的依据。
英国批评家伊利莎白·布龙芬曾在波夫瓦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女性常常被看作两个极端——不是纯洁、善良和无助的代言人,就是世故、危险而充满了诱惑力的魔鬼化身。在小说《吕蓓卡》一书中,如果说叙事者“我”似乎代表着一个极端的话,那么吕蓓卡就代表其中的另一个极端。“我”经常发出希望成熟一点的感叹,可她的丈夫拍着她的肩膀说:“要是你不会变老多好!”“我”对于这样的状态和地位是不满足的,时不时地想去翻看吕蓓卡这本“禁书”,好像关于成年女性的一些知识就写在那遥不可及的书页上。如果把吕蓓卡比作沁人心脾的杜鹃花和血红的石楠花,那么叙述者就像那些从东厢房的窗户可以看见的玫瑰花,前者浓艳逼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后者则可以和童年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给人带来幸福、平和的气氛。
《蝴蝶梦》中,作为叙述者的“我”是迈克西姆的第二任妻子,过早地失去父母亲友使“我”孤苦无依,本来就年轻、涉世不深,受雇于势利的美国人范·霍珀使“我”更加羞怯、孱弱。在多数人眼里,“我”就是一个没有多少个性可言,俯首听命、逆来顺受的弱女子,实际上却是相当坚强、独立:在家庭巨大变故的情况下没有过度悲伤且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而是积极工作积极生活;为范·霍珀工作期间丝毫不受她矫揉、势利态度的影响,也不会成为裁缝布莱兹那样的人;成为曼陀丽的女主人之后仍然不会对仆人摆什么主人的架子,依然用真诚、友善对待周围的人。“我”所具有的温柔、贤淑的品质是男性心目中贤妻良母的最佳标准,“我”的正直、善良也成为男性选择伴侣的条件,能够做迈克西姆忠实的影子和帮手,同时具备最起码的是非观念、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使“我”成为“屋子里的天使”,成为迈克西姆选择“我”作为妻子的重要原因。
相比较而言,吕蓓卡给人的感觉是仁慈、慷慨、多才多艺,她的芳名远近闻名,以至在死后,人们见到德温特的续弦夫人时谈起吕蓓卡还赞不绝口。在外人看来,吕蓓卡这个人见人爱的美人同时具备做妻子三种美德:教养、头脑和姿色。她人长得漂亮,才华出众,她那魔鬼般的鉴赏力把原本荒凉寂寥的曼陀丽变成了有口皆碑、上了照片和绘画的曼陀丽;又特别会迎合别人,老人、小孩、男人、女人,甚至狗都对她着迷;在曼陀丽大宴宾客,以她无与伦比的美貌和圆滑的处事在社交中显露风采。可在她非同凡响的魅力里,却有着令人十分憎恶东西。身边熟悉的人都对吕蓓卡讳莫如深,叙述者“我”曾以为是大家在拿自己和吕蓓卡作比较,“人们闭口不谈吕蓓卡,我总以为是出于同情和怜悯,不料真正的原因却在于耻辱和困窘。”结婚才五天就原形毕露,她的所作所为令做丈夫的迈克西姆难以启齿,怎么也不愿对第三者重复;在美丽和魅力的背后,迈克西姆深深体会到了她那可怕的一面,说她“心肠狠毒,活该下地狱,是个实足的坏女人”;她在男性面前卖弄风情,连迈克西姆姐姐的丈夫也不放过;面对丈夫指责她不该勾引庄园忠实的男管家弗兰克时,她能用她独特语言中的肮脏字眼,把人骂得狗血喷头;她扬鞭抽马,把马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满嘴白沫,不住打着哆嗦”。她生性狠毒,最厉害的是对人精神上的控制:贴身女仆丹弗斯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在她死后仍然对她忠心耿耿;结婚五天就同丈夫作“交易”,用扮演恩爱夫妻和治理曼陀丽作筹码,交换来她自己放浪形骸令人不齿的私生活,即使在身患绝症、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也要设下圈套,故意激怒迈克西姆,使他冲动之下成为杀死自己的罪犯,从而背负上一生都难以摆脱的沉重罪恶感。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一书中,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提出了女作家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即女作家在创作中的孤独感与对男性先辈的疏离感、对男性读者所持敌意的恐惧以及对表现自我的胆怯交织起来所表现的焦虑情绪。她们进一步指出,女作家们感受到父权制文化传统的压制和禁锢,往往采取了“替身”的写作策略来表达她们的痛苦与愤怒,将她们那种反叛冲动投射在作为主人公对立面的疯癫形象(疯女人或魔鬼般的女人)身上,进而表现自己的秘密欲望:“女作家通过把她们的愤怒和疾病投射在可怕的人物身上,为她们自己和女主角创造出黑暗的替身,她们便与父权制文化强加在她们身上的自我定义等同起来,同时对之又加以修正。所有19和20世纪在其小说和诗歌中创造了女性魔鬼的文学妇女都是通过与这种女性魔鬼的等同来改变其意的。从男性的观点来看,拒绝在家庭里保持顺从、沉默的妇女都被视为可怕的东西……但是从女性的观点看,魔鬼女人只是一个寻求自我表达的妇女。”吉尔伯特和格巴将此作为女性书写的策略,即在父权文化传统压制下女作家自觉采取的自我表现策略。但是,一些女作家在创造疯女人这样的对立面的时候,并未自觉地意识到魔鬼女人对她来说代表着什么,或者说,魔鬼女人只是她内心深处反抗冲动的无意识流露,这种反叛冲动也许是作者及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力图要压制的东西。当然,将这种表现视为无意识并不削弱作品本身的价值,因为正如处于历史坐标中的任何个人一样,女作家也受到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限制,从这样的文本处理中,我们恰恰可以看出女作家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和困惑。
《蝴蝶梦》中一正一反两个女性形象正是杜穆里埃内心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一方面,由于生于富贵之家,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下长大,并且作为一个出嫁前就已成名的女作家,杜穆里埃在思想、经济和社会生活上都相当独立。她不但喜欢打板球,骑马,驾船出海这些对体力要求很高的运动,甚至在21岁就由于第一本书的出版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拥有了自己的游艇。叛逆的吕蓓卡和杜穆里埃在爱好上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喜欢骑马,游艇和大海,喜欢在人际关系中占据主动。而顺服的“我”代表婚后的杜穆里埃的形象。由于丈夫的军队驻扎在国外,新婚不久的杜穆里埃毅然抛弃英国舒适的生活,追随丈夫到了埃及,她的生活和“我”一样以丈夫为中心,丈夫崇拜顺服,处处维护丈夫的形象和利益,当时的杜穆里埃对自己身为人妻有了角色认同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并努力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妻子。吕蓓卡是集美丽的外表和精明的头脑于一体的社交家和理财能手,这些智慧却和男性的头脑联系在一起。按照世俗的看法,女人只需拥有温柔的心,男人才有可以思考的头脑,杜穆里埃却把这两个方面都赋予了吕蓓卡。杜穆里埃一方面与叙述者“我”达到身份的认同,导致吕蓓卡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唾弃,彰显了男性价值观的胜利;而吕蓓卡尸体被发现,丹弗斯太太在杰克·费弗尔的猜测引领下对迈克西姆产生怀疑所带来的戏剧性变化紧扣读者心弦,直到最后求助于伦敦的贝克大夫,吕蓓卡的死因最终被认定为自杀,这一结局是杜穆里埃向男权社会做出妥协的结果,为了维护正统的女性形象而让叛逆的吕蓓卡死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吕蓓卡超凡的自信和魅力打破了传统对性别的界定,她是逾越和颠覆社会传统的红颜祸水,是使男人特权受到威胁的危险人物,是使男人优越感荡然无存的邪恶女人,因此为了保证男权统治秩序不被颠覆,吕蓓卡必须被除掉。从深层次来看,作者在潜意识里又十分欣赏吕蓓卡,与吕蓓卡也产生了身份认同感,并且使其在精神上处于优势,委婉含蓄地暗示了吕蓓卡的胜利——对迈克西姆精神上折磨的延续。以至于在英国女作家苏姗·希尔创作的续集《德温特夫人》中,吕蓓卡继续让迈克西姆因感受到她的存在而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在车祸中丧生:“我们并非因罪行被揭露而遭受惩罚,是这些罪本身在惩罚我们。我们无法一直忍受着良心的谴责至生命结束。” “我”把丽蓓卡对马克西姆的伤害称作“报复”,而马克西姆却称它为“公正”。
女性以写作的手段来实现自我讲述,以探求和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几千年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影响的根深蒂固,女性的地位以及女性看待自己的标准也都深受其影响和左右,作品中常常会流露出对自己女性身份的困惑和焦虑。随着女作家的文化性别意识的不断增强,性别价值的逐步明朗坚定,对妇女生活的思考也将更加深入,其对男权文化中心的反抗、颠覆也将更为自觉。
参考文献
[1] 达夫妮·杜穆里埃.蝴蝶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2] 王岳川.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3] 程锡麟.天使与魔鬼——谈《阁楼上的疯女人》[J]. 外国文学,2001.1.
[4] 苏姗·希尔.德温特夫人[M].郑大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 王腊宝,沈韬.重读《吕蓓卡》[J].外国文学,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