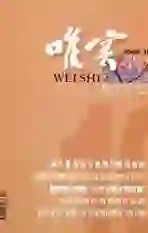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之原因分析
2009-01-06黄学胜
摘 要:通过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而真切理解这一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却在于追问马克思欲完成这一批判的真实原因。其原因并不像马克思自己交待的那般简略,而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必然,是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特性、现代批判运动的局限性以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批判的不彻底性等多种因素使然。
关键词:辩证法;现代解放;人类解放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0-0041-05
作者简介:A黄学胜(1983- ),男,江西赣州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哲学基础理论、近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突然转向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并借此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学界关于黑格尔是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其哲学“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现代形而上学之一切”,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就是批判整个近代哲学,已有统一认识。但关于马克思“为何要完成这一批判”这个值得探讨的、且涉关真切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要紧问题,目前的研究却很薄弱。本文愿对此作一专门探讨,希望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从《手稿》中马克思自己的表述来看,似乎马克思欲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的原因只在于要说明青年黑格尔派与黑格尔的关系。他说:“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特别是《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有关辩证法的叙述,以及最后对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略作说明,也许是恰当的。”[1]9其中的“现代批判运动”即指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但若停留于此,则在马克思思想内在转变的过程中,他为何要说明“现代批判运动”与黑格尔的关系?又为何要将黑格尔辩证法与整个哲学关联起来等问题就变得彰而不显了,而这些问题恰好又是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笔者研究相关文本,以为其中的真实原因至少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必然
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转变是与黑格尔哲学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的,他在《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最初是在柏林大学通过甘斯的影响接触到黑格尔哲学的,但他那时认为黑格尔哲学中的主要命题——“存在即是合理的”是对普鲁士专制的论证,他也不喜欢黑格尔哲学中“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2]。因此,并未认真研究黑格尔哲学,而是遵从父亲和未来岳父那里受到的启蒙理想引导,倾向于代表理性和自由精神的康德—费希特法权思想,要求用“应有”来规制“现有”,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康德—费希特的法学体系已过于陈旧,因此,他又欲依循康德—费希特提示的思路重建一个新的法学体系。但马克思很快发现,康德—费希特体系和任何先验论的原则一样都反映出“应有”和“现有”是对立的,“应有”总是脱离“现有”,它高尚纯洁、一尘不染,却是软弱无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再次钻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大海里,他“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物质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劳动”,但这次哲学实验还是失败了[3]141。马克思发现,他“在月光下抚育大的亲爱的孩子,它就像一个狡猾的妖女一样”将其“引入了敌人的怀抱”[3]141。此时,马克思因无法直接理解黑格尔而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危机。
1838年,马克思参加了“博士俱乐部”,在同其他成员的交往中真正了解到并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内核,即黑格尔强调精神与现实密切联系和相互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新的思想立场一旦被掌握,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反而用其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之形式主义和绝对主观主义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坚持哲学和现实的相互作用及其革命化”的世界观。自然,其中也反对了黑格尔“哲学与现实相调和”的保守观点。但黑格尔辩证法的内核却被马克思接受下来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这尤其体现在《莱茵报》时期的《第179号〈科伦日报〉》中。在那里,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4]此时,马克思既坚持黑格尔辩证法的内核,又对黑格尔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十分赞同。因此,在看待现实问题上,他始终坚持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法庭来评判和规制现存的一切,他像启蒙学者一样要求建立一个体现了普遍正义的理性国家和理性社会。但物质利益的难题却让马克思看到了理性主义的法和国家在现实生活面前的无能为力,任何像启蒙学者那样企图把国家和社会建构成理性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并以为这样就能消除现实生活的各种冲突和对立的做法都只能是一种妄想。这样一来,马克思原来所秉持的世界观又面临了严重的危机。
为弄清问题的要害,马克思接下来从事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其理论成果便是我们目前所见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通过这一批判,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法哲学的观念论本质,看到了现代解放表现为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双重抽象性,其中,现代市民社会又表现为现代国家的基础和前提。但那时由于马克思新的世界观和新的原则立场还未形成,即还没有从实践的观点来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基础本身,因此,他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克服黑格尔哲学,只是刚刚打算清算自己原来所持的世界观。其后,通过《德法年鉴》对启蒙意义现代解放的进一步批判,马克思看到了现代解放的根本局限性:它只是形式上确立了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政治解放,而不是人的解放。政治解放实现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也确立了人的市民与公民的分离和对立,这都是背离了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提出的“实现人类的普遍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的基本理想的。因此,他进而提出了消除人的原子化倾向、实现人们的实质自由和平等的人类解放思想。人类解放思想的提出表明马克思在视域和立场上已超越了现代启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是提出要对“当代现实”展开批判,要从现代世界中获得人的全面解放,即要全面超越现代世界,而这一超越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方式实现现代世界的整体变革。就马克思所指称的“当代现实”来说,马克思看到英国实现了工业革命,理论形态上表现为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地阐述了英国的“现实”;法国则实现了政治革命,即通过现实的政治运动实现了政治解放;德国虽然在社会政治状况上落后于当时的时代,却实现了哲学革命,它的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5]。德国哲学革命的最高成果就是黑格尔哲学,它是现代社会的观念论“副本”,同样可被归入马克思所要超越的现代世界之列。因此,在英法,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批判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批判,在德国就表现为黑格尔哲学批判。马克思通过政治批判要求实现的社会解放,在德国就表现为通过“扬弃哲学”的现实的运动而参与社会解放的历史进程。因此,对于德国“从现代获得解放”来说,就是展开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这一批判便是体现在《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全面清理。
二、现代形而上学是现代社会的“观念论”副本
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哲学是现代社会的“观念论”副本。黑格尔哲学与现代市民社会具有本质相生的特性,表现为现代形而上学与私有财产(货币或资本)的本质同构性。对于试图超越现代世界的马克思来说,自然也试图从根本上超越现代形而上学。
黑格尔哲学将现代形而上学发展到极致,代表了现代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它“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形而上学之一切”。本质说来,现代形而上学是对现代西方世界核心要素的形而上学说明,而现代西方世界的核心要素正是私有财产(货币或资本)。现代形而上学起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论说,表现为确立“我思”的绝对优先性。“我思”就是思维、精神、理性。我思与物质的截然二分、主体和客体的截然对立确立了现代世界的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使启蒙时代以来人们对财富(私有财产)的占有、对自然的剥夺和对人类世界的塑造获得了形而上学支撑。
在现代形而上学视野下,感性的现实生活中的人被抽象为自我意识。“我思”之“我”被确立为绝对的理性实体,表现为法权上的绝对人格,而“我”之为感性存在的本质,在法权上则表现为“占有”。绝对人格从而能够作为私有财产之所属而“占有”私有财产,实现绝对人格和私有财产的同一。在国民经济学那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1]74,而作为近代形而上学之完成的黑格尔哲学则以其“实体即主体”学说形而上学地反映了现代世界中私有财产(货币或资本)的运动。在黑格尔那里,“实体”被认为是世界运作着的精神本质,并通过如下方式实现着自身发展:精神由于自身的内部矛盾要扬弃自身成为对象,后又在对象中发现自身,从而扬弃对象回到自身。这一过程表现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精神运动。“我思”之“我”被作为“实体”的“精神”所取代,“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或者更准确些说,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1]100。现代世界中私有财产(货币或资本)的运动在黑格尔哲学中也相应地表现为精神的自身运动。马克思明确说,作为黑格尔思想本质的“扬弃”是“思想上的私有财产在道德的思想中的扬弃”[1]111,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1]98。因此,在国民经济学那里是私有财产(货币或资本)对现实世界的统治,在黑格尔那里则是“精神的货币”对现代世界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体现了启蒙精神对人的感性生活的宰制:人在国民经济学那里被认为是自私利己的个人,而在黑格尔哲学中则被抽象化为理性精神。因此,两者能够相互支撑,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加批判地加以肯定,从而最终丧失了各自的革命性。恩格斯正确指出,黑格尔的最大功绩在于他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它“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6]736-737。但黑格尔“把一切都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6]737。正是鉴于此,马克思必须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展开批判。
三、“现代批判运动”的局限性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批判运动”即青年黑格尔派运动虽然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和批判,但他们都未能从根本上清算黑格尔哲学,只是抓住了黑格尔哲学“母亲”中的某一个方面,未能从根本上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甚至还未意识到要进行这一批判。马克思则欲揭示“现代批判运动”与黑格尔的真实关系,完成青年黑格尔派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因此,马克思需要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作出自己的批判。
我们知道,在《手稿》之前,马克思已经同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同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决裂了(虽然不是彻底批判,后者体现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责备他们没有研究黑格尔辩证法,也没有克服黑格尔哲学。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批判了鲍威尔等自我意识哲学的形式主义和绝对主观主义。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更是对“自由人”展开了尖锐批判,厌弃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性”和“理论空谈”。他们脱离实际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从而最终堕落为庸俗的主观主义。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批判鲍威尔未能看到现代解放的局限性,仍停留于现代的政治解放。马克思则通过人类解放思想的提出既从立场和视域上根本上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又确立了自己批判现代世界并从中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视角和原则立场。
在《手稿》中,马克思同样也依循了这一批判。在序言中,他说,“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的神学家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这是一种必然的不彻底性,因为即使是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就是说,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出发,或者当他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产生怀疑的时候,就怯懦地和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明他对这些前提的屈从和对这种屈从的恼恨。……神学的批判——尽管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的进步因素——归根结底不外是就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的已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1]4-5不可否认,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曾经利用过黑格尔哲学作为反对普鲁士专制的斗争武器,但在马克思看来,除了费尔巴哈以外,其他人都毫不批判地对待这种哲学,并且完全受它的支配,都满足于从黑格尔哲学中抽出个别的要素,并以此作为自己学说的基础。施特劳斯把作为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作为自己哲学的原则,而鲍威尔则以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为自己的出发点。这体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又尤其体现在鲍威尔那里,甚至在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以后也是如此。马克思批评鲍威尔对于“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是多么缺乏认识”,以致始终都是黑格尔哲学的俘虏,而未能对辩证法这一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作出任何批判,而且把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进一步歪曲,把黑格尔作为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理念”偷换为不断把自己同世界对立起来并以此推动历史发展的“自我意识”。因此,鲍威尔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主观化了,也把他的辩证法主观化了。他以自我意识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辩证法的运动在他那里也不再像黑格尔那样是在现实所固有的矛盾的影响下发生的,而是通过自我意识同世界的斗争发生的。这种矛盾就是“纯粹的批判”同人民和“群众”的关系,全部历史发展都被归结为这种矛盾,而作为普遍的自我意识所体现的“批判”就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轻蔑态度冷漠地看着庸庸碌碌的人们——“群众”[7]。因此,“这种唯心主义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1]95,从而终于没有完成清算黑格尔哲学的任务。
马克思则欲完成这一未完成的工作,他试图解释青年黑格尔派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关系,揭示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运动中的非批判形式”,这同时也是进一步指证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只不过是一种“为批判而批判”的“抽象批判”,是脱离人民群众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和变革来说,最后也必然会走向保守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被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是整个“现代批判运动”的继续和完成。
四、费尔巴哈也未能完成这一任务
马克思欲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也是出于对费尔巴哈实现的黑格尔哲学批判的不满意。
我们知道,《手稿》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的理论成果。他说,“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1]4“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96这里的“真正理论革命”是指“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1]4。这主要是指费尔巴哈在1843年发表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中提出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思想。在费尔巴哈看来,“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神学”[8];宗教的本质只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上帝是人的产物,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异化的对象。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要将人异化给上帝的本质力量复归于人本身,实现人的思想上的启蒙,摆脱宗教偏见的统治,打碎那个把他束缚在天上的锁链,并到地上的真正的类的共同体中去寻求幸福。费尔巴哈将人理解为感性的具体的自然的个人,将人的自然本质中“爱”的情感力量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并以此为基础视黑格尔哲学为神学的延续,在本质上是思辨神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主客颠倒。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称费尔巴哈的发现为国民经济学批判打下了“真正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有三重功绩。首先,“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1]96。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成了上帝,因此,黑格尔哲学是一种思辨神学,应当和宗教一样受到批评。其次,“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1]96。这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高度评价。最后,“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1]96。即指费尔巴哈以其自身的唯物主义思想反对了黑格尔的观念论本质。这里,“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是指费尔巴哈主张的感性确定的东西,这便是感性的、自然的、具体的个人。而黑格尔那里作为基础的、绝对肯定的东西则是精神。黑格尔的辩证法便是精神从自身出发,扬弃无限,并设定感性的、现实的、具体的、特殊的东西,最后重新扬弃这些肯定,恢复抽象的、无限的精神,完成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一精神的自我运动。费尔巴哈以其感性的确定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观念论本质,从而实现了主客体的颠倒,恢复了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尊严。
但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批判仅止于此。在《手稿》序言中的一附释中,马克思指出,“相反,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阐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1]6。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完成的黑格尔哲学批判的不满意。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把黑格尔辩证法“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1]96。他看不到黑格尔辩证法的“非批判运动所具有的批判形式”[1]97,即费尔巴哈未能看到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运动和发展的本质。这种运动和发展,在黑格尔那里虽然是“精神”的运动和发展,但也是人类社会的运动和发展,从而能够揭示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都必然会扬弃在人类历史的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展现其“非批判运动所具有的批判形式”。正因此,关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永恒化和天然化的任何言说都将成为呓语。人类历史总会滚滚向前,费尔巴哈没有看到这一点,马克思批判他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完全脱离的。”[5]78但也不能因此高估黑格尔辩证法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尽管有这些“批判的形式”,他尽管“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出真正的和惟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惟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但他的辩证法只是阐述了一种“非批判的运动”,它“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因此,马克思说他的“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的任务就是“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说明与费尔巴哈的批判不同的,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1]97。可以说,马克思整个“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都在完成这一任务。
因此,综而观之,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真正原因并不如其自身交待的那样简略,这既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黑格尔哲学的本质特性以及这一特性与现代社会的本质相生性,还是其对现代批判运动的不满意所致。其中的理论环节涉及到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转变和其根本的理论旨趣,也涉及到马克思对当代的批判是否达到了“原则高度”。因此,对于我们切实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来说无疑有着不可否认的重大价值,值得我们重视。更为根本的是,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发动之处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具体批判,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撰文论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成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19
[3]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5:101
[8]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01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