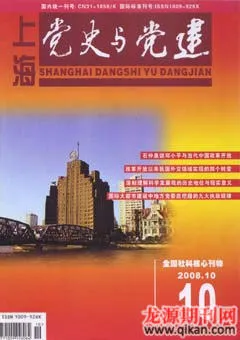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的倒退
2008-12-29陆南泉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08年10期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对经济体制改革了18年。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改革的头几年,不论在农业还是工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的来说,改革18年之后的体制,仍然是效率低、浪费大、过度集中的一种体制模式。由于改革的停滞不前,产生了一系列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这个时期,一方面消耗苏联积存的种种潜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产生种种社会经济疾病和积累大量的问题与矛盾,这是苏联走近衰亡的时期。
一、恢复并逐步加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
1.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在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日益严重。表面上政治局各委员都对自己主管的领域负责,一切决策都由政治局作出,但实际上政治局作出决策,也往往是形式上的,主要还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特别随着勃列日涅夫的地位巩固与加强之后,更是大权独揽。1977年苏共中央5月全会决定,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10月7日,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审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按新宪法增加的一些条款,勃列日涅夫同时又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样,他就总揽了党、政、军的大权。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不只反映在勃列日涅夫这个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身上,苏联党的很多领导人兼任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另外,在党政领导的组织机构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苏共中央机关设置的与政府部门相应的部门比过去更多了,如国防工业、重工业、机器制造、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等部门,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导致各级党组织往往对一些具体经济问题作决议与发指示,从而大大削弱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
勃列日涅夫坚持党政不分的政策,其理论根据来自斯大林。他在1977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上决定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讲话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他解释说:“这绝非是一个徒具形式的行动”,“这首先是共产党领导作用不断提高的表现”,“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中央政治局许多成员直接处理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换言之,因为苏共是执政党,因此苏共领导人可以处理苏联国内外所有事务。十分明显,这种观点,直接承袭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报告中的下列提法:“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
苏联长期以来未能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与斯大林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度集权,在客观上要求党统揽党政大权。对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党政不分的体制也难以改革。
2.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随着勃列日涅夫领袖地位和权力基础的巩固,个人集权日益发展。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形成的“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也不是三者之间的力量与权力处于均等状态,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权力。苏共中央1972年12月全会上对由柯西金主管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否定性评价之后,勃列日涅夫把在经济方面的决策权控制在自己手里,随后又控制了外交权,此后,使柯西金的地位大大下降。1977年解除了波德戈尔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并宣布他退休。此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大大膨胀,决策权高度集中。据不少材料披露,像1979年底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事情,只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等四人商量后作出决定的。①从这一件事就可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专权的情况。
由于个人集权的加强,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和苏共代表大会按规定举行,但并不意味着党内有真正的民主生活。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举行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讲:“让我们坦率地说,多年来,党和人民关心的许多迫切问题没有被提到全会日程上来。同志们都记得,虽不止一次地举行时间很短和形式化的中央全会,许多中央委员在其整个任期内没有可能参加讨论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全会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地方党委和党组织的工作作风。”一切重大问题不是经过认真和充分讨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更加突出。沃尔戈诺夫所著的《七个领袖》一书中说:政治局讨论问题的程式,如由谁发言,如何发言等,事先都由党中央机关秘书班子作好仔细安排。令人难以想像的是,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讨论,而是相互念自己的助手们为他们写好的2—3页讲稿。大家总是表现出“英雄所见略同”,照例不会发表同事先由起草班子起草的决议草案有多少出入的意见。②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一书中说:在那个时期政治局有些会议,开会的时间只有15—20分钟,用于集合就坐的时间往往比用于讨论工作的时间还多。即使是十分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言辞是,“同志们已作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作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③
二、个人崇拜盛行
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从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如果翻开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苏联报刊杂志,对勃列日涅夫令人作呕的颂扬言论到处可见。1976年底在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诞辰时,掀起了颂扬的高潮,为此,《真理报》开辟了7天的专栏。而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的是基里延科,他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党的领袖”,当时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④那些阿谀奉承、恭维勃列日涅夫的言论更多:“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对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⑤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恳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⑥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和泉源”。还有些报刊吹棒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而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其登峰造极之时我认为是1975—1982年”。⑦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⑧
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弊端日益严重
应该说,赫鲁晓夫执政时,他看到了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因此他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改革,目的是要废除像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腐朽的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富有活力。但他在这一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变动过于频繁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因此,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在这方面的倒退,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
1、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使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49.6%,到二十二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上升为79.4%,二十五大时上升为83.4%,二十六大为90%以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变动更小,18年中只换下12人。⑨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是苏共历史上没有过的。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死亡和正常工作调动外,没有1人被撤换。⑩由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重要干部由“一号人物”来决策,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不可能由年轻干部去担任。勃列日涅夫后来提拔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员的情况就说明这一点。如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1976年去世时为73岁,而接替他的乌斯季诺夫当时已经69岁;苏联交通部长科热夫1975年去世时为70岁,接替他的索斯诺夫为67岁;造船工业部长托马1976年去世时为69岁,接替他的叶戈罗夫当年也是69岁。勃列日涅夫兼任国家元首之后,竟选择比他大5岁的库兹涅佐夫担任自己的副手。1976年吉洪诺夫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时已72岁。{11}
二、终身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领导干部老化。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为52岁,到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1964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成员为54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党的领导层的老化,同样反映在地方党政机关。戈尔巴乔夫在1981年1月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一系列党委的书记和成员,地方、共和国和全苏一级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往往好几十年没有发生必要的干部变动,没有增添新人”。干部的普遍老化,是苏联社会死气沉沉、保守、僵化和6b713ce0fb1a9e9b1aa98fbf2b509bcf各种消极现象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个问题,从勃列日涅夫本人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于1974年12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军用飞机场刚送走美国总统福特,他感到不适,患了大脑脉粥样硬化症。第二天前往蒙古,从那里乘火车返回莫斯科时又发生了第二次中风,从此,他病得很重,病了很长时间。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从这时起,勃列日涅夫还活了八年,并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体制下,他还“统治了”八年。在这八年中,他的病情不时地有某些好转,但他一直没有能恢复到哪怕是自己正常的工作状态。他极易疲倦,无兴趣处理手头该解决的问题,说话越来越困难,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在他生命的晚期,就连起码的谈话内容和礼节性的应酬话也要别人替他写好,没有这种“小抄”他简直无法应付。{12}对此,博尔金作了以下的描述:“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作出结论并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场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13}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八年中,他已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已经无力正常执行领导者的起码职责”。{14}这在当时的苏联上层都很清楚,但在传统的集权体制下,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条件下,只有等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他才离开苏联最高领导的职位。这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现行的机制、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环境实际上排除了‘正常’接班的可能性。”{15}
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产生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不正之风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人
是否退休,并不取决于年龄与是否有才能,而是取决于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关系。正如利加乔夫指出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的关系。这种程序(确切些说是无程序)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在于主观方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那些忘我工作的书记,由于没有注意到在中央和中央委员会的个人关系,当到退休期限时便处于‘无人过问状态’。”{16}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这样,使不少干部不是把精力用于如何做好工作,而是搞投机钻营,那些吹吹拍拍、讨好上级、唯上是从、在上层寻找保护伞的干部越来越多。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勃列日涅夫还对其家属与沾亲带故的人给予“照顾”,让这些人升官、捞取私利。他女儿的最后一个丈夫丘尔巴诺夫令人头晕目眩地青云直上。在屈指可数的几年内当上中将,从一名平平常常的民警政治工作者一跃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他被选入党的高层机关,获得了奖赏、汽车和别墅。勃列日涅夫的儿子被提拔为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他的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这两个人都有酗酒的恶习。{17}
四、“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使得苏联社会早已存在的“特权阶层”进一步扩大与稳定,这一阶层的人思想更趋僵化,这也成为阻碍整个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权阶层”并不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才出现的,而在斯大林时期就逐步形成起来。像政府别墅、特殊门诊、医院、休养所和疗养院、配备司机、专用汽车等,“早在30年代所有这些已经形成完整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特别是同人民生活相比更是如此。”{18}在战后,对苏联上层领导人的配给制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特别是各种商品的购货证与票券大大发展了,逐渐成了高中级负责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在这方面越来越起带头作用。有些将军大胆妄为到这种地步,以致向来对这种腐化行为睁眼闭眼的斯大林不得不出来纠正,命令把某些人逮捕。但特权并没有消失,后来很快地扩大了,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高低,装在信袋里秘密发给。一个部长可拿到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卢布,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不纳税,这个数目相当于不久前苏联总统规定的工资的两倍。{19}
不少西方学者也都认为,苏联的特权阶层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形成。{20}他们把特权阶层的特权归结如下: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称号带来的特权,等等。对苏联上层领导来说,高薪并不是主要报酬,远为贵重得多的是上层所享有的特权。他们一切的获得主要靠特权。
至于形成这个特权阶层的原因,笔者认为,阿尔巴托夫提出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21}另外,他还指出:“社会的贫困本身实际上使特权不可避免。”{22}那种把由于斯大林时期因“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作为形不成特权阶层的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斯大林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是有区别的。首先,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干部领导职务搞任命制与终身制,干部队伍较为稳定,因此,“特权阶层”也比较稳定。而斯大林时期,虽然形成了“特权阶层”,但它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斯大林一方面给予上层人物大量的物质利益和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消灭这些人。首当其冲被消灭的便是这个“特权阶层”。其次,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各级领导机关干部数量大大膨胀,与此同时,特权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23}对特权阶层人数估计不一。“英国的默文·马修斯认为,连同家属共有一百万人左右。西德的鲍里斯·迈斯纳认为,苏联的上层人物约有四十万,如果把官僚集团和军事部门的知识分子包括进去,约七十万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利姆别尔格尔估计,今天苏联的特权阶层有四百万人,另一些人估计不少于五百万人。”{24}最后,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是使这个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
注释:
①⑦{12}{15}{16}{17}{18}{19}{21}(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79、346、267~268、267~268、341~343、341~343、341~343、312页。
②③《o176LZvDyW46u4QSlUocJkfP5+bm0ztk28nMHhnbtAY=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④(苏联)《巴库工人报》1976年11月25日。
⑤《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资料》,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1期。
⑥⑩{11}{12}《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⑧{14}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⑨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9页。
{13}(俄罗斯)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20}{22}{24}陆南泉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81~83、310、82页。
{23}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责任编辑:姜德福